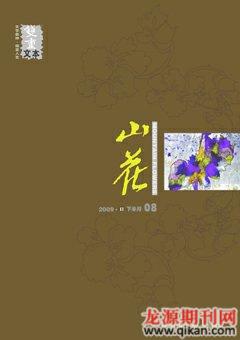声音的裂变
高玉华 张 愉
《一小时的故事》(1894)是19世纪末美国女作家凯特·肖班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小说自出版以来,由于文中所流露的明确的女性独立意识而受到文学评论界,特别是女性文学评论家的关注,也由此出现了对该作品的多种不同角度的解读。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者苏珊·兰瑟在她1981年出版的《叙事行为》一书中从女性叙事学的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分析。她通过分析人物话语、叙事视角、意识形态等因素,把这一作品阐释成一个典型的、反抗男权压迫的女性主义文本。而国内知名的叙事学家申丹教授则通过剖析文中隐含的多重反讽和深层意义,并参照肖班所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作者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及作者在创作完该作品后不久所留下的日记,认定兰瑟在分析该作品时“仅仅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文本,忽视或无视文本在意识形态立场上表现出来的矛盾性、复杂性和‘非性别政治性”(申丹),由此推出文中的意识形态所涉及的并非性别政治而是婚姻枷锁与单身自由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叙事学家都一再强调作品中叙述者的立场代表了作者肖班本人的立场,然而却就文章的主题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小说文本中,叙述声音因为是意识形态激烈对抗、冲突与激战的焦点场所而成为话语权威建构的主要文本写作策略,也历来受到评论者的关注。本文拟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有关叙事声音的理论并结合作者的生活经历,来理清文中作者、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以求对该作品做一个更为清晰的解读。
一
叙事声音与性别政治的关联是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热点之一,也是文学文本中性别政治斗争的场所和话语权威争夺的焦点所在。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创始者苏珊·兰瑟把叙事声音模式分为三种:作者的(authorial)、个人的(personal)和集体的(communal)叙述声音模式,并认为女性作家对女性权威的建构是通过叙述者来完成的,因而每一种模式不仅各自表述了一套技巧,同时还表述了一整套互相联系的权力关系和危机意识(兰瑟)。其中作者型叙述声音模式是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声音。它常常是单一的、故事外的和公众的叙述声音,因而被前所未有的权威化。在这样的文本中,叙事者往往信心十足,充满了道德和智性的优越感,是具有哲学精神和道德责任感的“现实生活”的裁决人。在十九世纪那个“男性”和“女性”生活圈子受到严格区分的时期,女性没有参与社会话语的权利,这种权威往往属于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因而这些叙事者常常是男子气十足的男性家长声音。女性虽然被鼓励进行文学创作,但作为一个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作家,面对复杂的读者群,面对来自当时的社会价值体系及群体观念的压力,要想作品被普遍接纳,必须隐藏克制自己的作者权威。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女性作家常常选择特定的叙述模式,在不脱离她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与叙事规约前提下通过套用主流叙事模式来抵制、批判男性权威,创建女性作者自己的声音。
作为19世纪末的一位美国南方女作家,肖班在她的作品中也大多采用作者型叙述声音,如短篇小说《黛西莱的婴孩》(1893),《一双丝袜》(1896),《风暴》(1898),以及她的代表作《觉醒》(1899)等, 《一小时的故事》也没有例外。在这种十九世纪普遍采用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模式中,叙述者常常如上帝般的对所发生的事件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居高临下的、不容置疑的评论,具有无上的权威,因而也常常被认为是代表了作者的观点。兰瑟也认为,第三人称叙述者在结构位置和结构功能上都与作者较为接近,可将其视为作者的代言人,因而她将这种叙述模式称为“作者型叙述声音”,并在她的《叙事行为》一书中一再强调《一小时的故事》中叙述者的立场代表了作者的立场(申丹)。值得注意的是,申丹也认为,在这篇小说中,在“这样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中,叙述评论比所述事件更有权威性,更为直接地体现叙述者(作者)的立场”。肖班所选择的这位全知叙述者真的是作者的代言人吗?他对人物的看法、评价真的代表肖班自己的观点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的深层解读。
二
在《一小时的故事》中,故事的叙述者对马拉德夫人在获知丈夫突然去世之后的外部反应和内心感受基本上作了如实的报道,除此之外,这位叙述者还时不时地对所发生的事件予以或隐晦或直白的评价。在故事的开始部分,我们了解到马拉德夫人的丈夫因为一次铁路事故意外身亡,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有心脏病,所以不得不小心翼翼、战战兢兢、遮遮掩掩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对于马拉德夫人对此噩耗的反应,叙述者说,“如果别的妇女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因过度震惊而无法接受现实。她可不是这样。她立刻倒在姐姐的怀里,突然放肆地大哭起来。”在叙述者的描述中,马拉德夫人在闻悉丈夫死亡的噩耗后所作出的反应显得虚假而做作,并没有表现出大家所预想的应有的悲伤与绝望。他对此所流露出的批评、嘲弄的语气是显而易见的。接着马拉德夫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窗外,独自遐想。在叙述者看来,此时“从她的眼光看来她不是在沉思,而是暂时停止了理智的思考”。这里叙述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马拉德夫人此后所流露出的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对终于摆脱了婚姻的束缚,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未来的向往。然而从下面的描述中我们发现正是这叙述者口中的“不理智的思考”,令她“心中感到恐惧”的向往使马拉德夫人的神情变得“强烈而明亮”,“她的脉搏加快了,快速流动的血液使她全身感到温暖、轻快。”可见正是由于马拉德夫人“停止了理智的思考”,正是由于她对自由的渴望,使她重新焕发了光彩,使她的生命再次充满了活力。如果说在这之前叙述者对女主人公的讽刺还略显隐晦,随着女主人公对自由的憧憬的越发强烈,其主体意识的日渐明显,他对她的批判也越来越直白,“她没有停下来问问,控制自己的究竟是否为一种邪恶的欢欣。一种清楚和亢奋的感知使她得以认为这一问题无关紧要,不再加以考虑。”对叙述者来说,马拉德夫人在丈夫突然去世之后,不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悲伤,反而去憧憬未来自由快乐的生活,这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绝对是有违道德的,是“邪恶”的,代表当时社会普遍道德观念的叙述者才会发出如此的质问。对于这几处叙述者对女主人公的行为所作出的评判,如果读者把叙述者直接等同于作者,那么自然会将叙述者的价值判断等同于作者的判断而得出此文是对受命运捉弄、憧憬自由独立生活的马拉德夫人的反讽的结论。
然而反观肖班的成长经历、她的其他作品和她为创建女性声音所作出的种种尝试就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肖班是十九世纪末的一位美国南方女作家。她的父亲在她不到六岁时因为一次意外事故突然去世。她自小便在母亲、外祖母和曾祖母的庇护下长大,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群精明强干、开朗健谈、独立自强的女人中间,直至出嫁。在曾祖母及同时代的各种早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肖班性格独立,具有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早在丈夫去世之前,她就喜欢抽烟,喜欢独自一个人去骑马,这些行为在当时的社会是离经叛道的,因而在所居住的小镇肖班因过于独立和举止轻浮而闻名。她所结交的朋友也大多思想自由,学识渊博,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肖班的思想和以后的文学创作。她的作品关注女性在爱情、婚姻、家庭中的独特内心体验,并涉及一些同时代的女作家不敢触及的敏感问题,如离婚、婚外恋、跨种族通婚等。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也大多拒绝传统,追求自由,渴望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肖班也因此成为当时一位饱受争议的女作家。她1889年创作的第一部小说集《过错》(At Fault),就因为把女主人公描绘成一个酒鬼,违背了那个年代对女性行为规范的要求,并且涉及离婚这一当时社会的敏感话题,被多家出版社拒之门外,直到1890年才被自费出版。《一小时的故事》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当时的《世纪》杂志的编者基尔德就曾因为这篇小说内容不道德而拒绝发表,即便在肖班把这篇小说的语气改得极为婉转隐晦之后也无济于事。为了自己的作品能够顺利出版,肖班到底采用了怎样的叙述策略呢?肖班对她所生活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压抑以及对女作家创作的压制、排斥和贬低有着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在她短暂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她不断尝试着使用一种女性语言来呈现被男权社会刻意抹杀或歪曲的女性世界。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女主人公大多沉默被动,无力表达或刻意回避自己的愿望,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克里奥尔人》(1891)中的尤福利赛和《上帝之爱》(1891)中的拉丽。而作品中那些敢于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女性,其声音往往被抹杀和掩盖,有时甚至会落得 “疯癫”或“堕落”之名,如《黛西莱的婴孩》中的黛西莱,《智胜神明》(1889)中的保拉等。根据肖班的传记作家艾米丽·托斯(Emily Toth) 的记载,肖班在1894年后曾试图在作品中更加大胆直白地呈现被长期忽略压抑的女性意识、发出女性声音,结果她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被出版商拒之门外。为了成就自己的文学梦想,使自己的作品能够顺利出版,肖班不得不采用更加隐秘的叙述策略(Poupord)。这种策略使文本的表层含义变得模糊不定并掩盖了更深层的、更不易为社会所接受的意义层次,从而成为肖班反抗男权社会压制和排斥的最有效武器,使她所要传达的那些颠覆性的信息能够避开当时严格的社会审查,成为可用来混淆男性“公众”视听的女性语言密码。在《一小时的故事》中,虽然作者所采用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以批判的口吻来描述在意外发生之后人物的一言一行及内心感受,但细读作品后,我们会发现在这篇短小的作品中,作者依然留下了种种线索让读者去了解、挖掘作品的真正主题。
三
在获知丈夫突然去世的消息后,马拉德夫人“立刻倒在姐姐的怀里,放肆地大哭起来”,这里叙述者的措辞耐人寻味,“立刻”、“放肆”这两个词一方面流露了叙述者对马拉德夫人讽刺嘲弄的口吻,另一方面也使人一看便知她并非真的悲伤。如果夫妻间感情深厚,这样的反应确实有违常理,可见在如此的噩耗面前她难以悲伤,恐怕是因为夫妻间的感情淡漠,只有对婚姻极度厌倦,才会有他人眼中如此反常的反应。读者的猜测在后面的阅读中一步步得到印证。接着,故事空间转移到马拉德夫人自己的房间,观察角度也从全知叙述者转到了马拉德夫人。接下来对窗外景物的描写看似与全篇内容不相关联,其轻松欢快的语气也与前面压抑沉闷的基调格格不入,然而事实上,整个故事的冲突都源于女主人公对窗外世界的向往,从人物眼中摇曳的树梢、雨的芬芳、小贩的吆喝、远处的人的歌声、屋檐下麻雀的叫声、天空、白云, 到“从空中爬出来的,正穿过满天空的声音、气味、色彩向她奔来”的自由,以及她“透过那扇开着的窗户”畅饮的“长生不老药”。这些意象无不表明了女性对屋子(男权社会界定的女性生活空间)外面的自然、生命和自由的渴望如同人需要窗外的空气和阳光一样难以抗拒。在叙述者的描述中,“她还年轻,美丽,沉着的面孔上出现的线条,说明了一种相当的抑制能力”。为什么她会有“相当的抑制能力”?抑制什么?年轻美丽的她如果生活美满幸福,享受着来自丈夫的爱情的滋润,她何需具有“相当的抑制能力”?由此可判断人物所处的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作者意图通过这个细节凸显现实世界中女性压抑的生存环境。
在接下来的段落中,作者巧妙地运用自由间接引语,使读者越过叙述者,直达人物的内心,与人物进行直接地对话。在《谁在这里说话》、《爱玛》、《霍华德别业》和《黛洛维夫人》中的自由间接引语、《社会性别与权威》一文中,凯西·梅齐将传统叙述权威视为父权制社会压迫女性的手段,因而更为关注第三人称“作者型”叙述模式中,女性人物与代表男性权威的第三人称叙述者之间的文本中的权威之争。在她看来,“自由间接引语”这一叙述技巧构成作者、叙述者和聚焦人物之间的文本斗争的场所(申丹)。正是自由间接引语这一有效传达双重声音(叙述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的叙述手法使读者有机会穿越作者通过叙述者设置的层层障碍,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声音这个男性家长般的声音之外,听到一个虽微弱却格外清晰的声音,路易斯的声音。
当自由向她走来时,“她内心激烈地起伏着。她开始认出那正在向她逼近,就要占有她的东西,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可是她的意志就像她那白皙纤弱的双手一样无能为力。”和其他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一样,因为长期被剥夺了自由,所以当自由真正来临时,即便是有着“相当抑制力”的她,内心也依然感到恐惧、慌乱、犹疑而无所适从。 作者刻意突出的“白皙纤弱的双手”这一意象暗示了当时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束缚,女性只不过是男性所要求的观赏对象,家中的一件精美的装饰品,“白皙”、“纤弱”、“无力”,从而再次突出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依附地位。此时的叙述者利用其全知视角的优势,直接深入人物内心,形象细腻地描述了马拉德夫人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由时的感受,然而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虽然通过叙述者的描绘得以生动再现,此时文本的话语权依然掌握在叙述者手中,人物依然处在沉默失语的状态之下。转折点出现在第11段,“自由,自由,自由!”,这是文中首次出现出自马拉德夫人的直接引语。正是在这句话之后,叙述者对人物话语的完全控制被部分打破,人物的声音和主体意识渐渐凸显,文本也从叙述者控制的单一话语层面变成了一个由叙述者话语和人物话语构成的对话体系。在文本前半部分沉默失语的女主人公终于赢得了话语权和呈现自我意识的机会。对于之前的种种反常表现,她辩解道,其实她并非如叙述者所暗示的那般铁石心肠,“等她见到死者那亲切体贴的双手交叉在胸前时,等她见到那张一向含情脉脉地望着她,如今已是僵硬、灰暗、毫无生气的脸庞时,她还是会哭的”。很多评论家以此为证,指出马拉德夫妇的婚姻是幸福的,因为她那死去的丈夫常常把那“亲切体贴的双手交叉在胸前”,“含情脉脉地望着她”。然而尽管马拉德先生“亲切体贴”、“含情脉脉”,他的身体语言却泄露了秘密,双臂交叉于胸前这一姿势在世界各地的理解几乎完全相同:消极、否定或防御,好比在与对方之间筑起了一道障碍物,将不喜欢的人或物统统挡在外边。
在这篇不足1500字的短篇小说中,肖班用女性特有的敏感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细腻地描绘了在无爱的婚姻中,当自由真正来临时,面对来自现实世界的强大压力,女性内心所经历的挣扎、矛盾和激烈的内心冲突。肖班虽然出于谨慎选择了主流叙事模式,却通过女主人公的自由间接引语建构了一个新的话语层面,以此对常规叙事声音中的男性权威的可靠性提出诘难,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男性话语权威。从表面上看男性声音控制主导着整个文本,两种声音强弱对比强烈,而事实上两种声音在激烈的对抗冲突中形成一种双重的相互抵制的力量,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冲突通过两个声音凸显出来。正是在叙述者和人物这两种声音的互动与冲突中,形成了文本意义和作者真实意图的多重解读,在有限的叙述空间内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女性复杂而艰难的生存环境,女作家艰难的创作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所谓男性权威的狭隘、专横及对女性的偏见。作者把整篇作品的故事时间安排在短短的一小时之内,人物的活动空间也局限在一间狭小的房间,凸显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局促压抑的生存空间。文章结尾医生宣布马拉德夫人死于“致命的欢欣”,对于了解了真相的读者而言,是对作为权威的医生的反讽,也是对所谓的男权社会权威的反讽,从而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地否定了叙述者所代表的权力话语。
参考文献:
[1]申丹.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对凯特·肖班《一小时的故事》的重新评价[J].外国文学评论,2004.1.
[2]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Poupord, Dannis, ed.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127. Kansas: Gale Research Company, 2003.
[4]申丹等.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皮斯等.身体语言密码[J].王甜甜,黄佼译. [EB/OL]. http://book. sina. com. Cn /nzt /live /liv /styymm /36.shtml.
[6]凯特·肖班.觉醒[M].杨瑛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高玉华,四川音乐学院基础部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与教学。
张愉,四川音乐学院基础部讲师,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