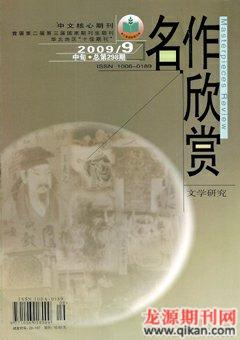从仇虎的复仇看《原野》中的基督教意识
关键词:复仇 善与恶 暴力 道德意识
摘 要:《原野》中的复仇故事与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的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试图通过对仇虎在复仇过程中善与恶之间关系的分析,来考察《原野》中的基督教意识,以及由此给作品的艺术品质所带来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现代文学从古代文学的传统中独立出来,并诞生了反叛的一代作家,但其实包括“五四”作家在内的现代作家,头脑中都含有新旧两种思想,这就造成了“现代作家在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相对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寄托方式”①。曹禺虽然不是基督教徒,但他与基督教有精神上的契合却是不可否认的,《雷雨》的序幕和尾声把背景设在基督教堂,《日出》的开头则多处引用了《圣经》中的句段,相比之下,《原野》和基督教的联系并不明显,但是剧中讲述的复仇故事与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的思想有很大的相似性,本文试图通过对仇虎在复仇过程中善与恶之间关系的分析来考察《原野》中的基督教意识:对于罪的非暴力态度、超越阶级视野的道德意识,以及由此给作品的艺术品质所带来的影响。
一、复仇中的善与恶
《原野》的核心内容讲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戏剧围绕着两个基本冲突展开:一是焦仇两家的恩怨。焦阎王抢占了仇虎家的土地,害得仇虎家破人亡,还把仇虎送进了监狱,仇虎从狱中逃出来前往焦家复仇,而当时焦阎王已死;二是仇虎在复仇过程中的心理冲突。焦阎王的罪行是暗线,但却是整个矛盾的起因和决定性因素,规定着事件的走向。焦阎王已经很富有,却由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而毁灭了仇虎一家,可是他还没有等到“报应”的来临就死去了,他是否有悔罪之心也就不得而知了,留下妻子焦氏和儿子焦大星一家来背负他所种下的罪恶。
善与恶的关系。基督教的观点认为“恶是多种的、零碎的,善是整体;恶是表面的,善是神秘的;恶在于行动,善在于非行动,等等。处于恶这个层次上,并同恶相对立。——如同对立物相对立——的那种善,是一种刑法的善”②。人物性格中的善与恶就通过矛盾冲突显现出来,焦氏作为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旧式妇女,却并不令人同情,她溺爱儿子,百般刁难儿媳,一边想通过皈依佛教来救赎焦阎王犯下的罪行,她自知焦家欠下了对仇家的血债,却毫无悔意,反而强词夺理,时刻提防着仇虎的到来,暴露了内心的冷酷残忍。她代人赎罪能否行得通暂且不论,仇虎到来后她的表现已经表现出,她信佛只是为了保持精神上的心安理得,从未抱有真诚的忏悔之心和赎罪的实际努力。焦阎王、焦氏与基督教所倡导的“自私的乃是邪恶之徒”和“不要沉醉与骄奢淫逸的生活”(《便西拉智训》)的教导背道而驰,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相当深的中国人去践行基督教的教诲。但是,我们却不禁要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犯下罪过的人如此冥顽不灵、麻木不仁呢?“人一旦作恶,恶就显现为某种责任。大多数人在作某件坏事时和做其他一些好事时怀着责任感。”③这句话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作恶者当时的心态,而内在的根源,简而言之则在于信仰天命鬼神观念的中国文化,犯罪的人和受害者都习惯于向鬼神祈祷,以此来实现精神上的解脱和复仇,而不是由受害者亲自实施报复。纵观人类历史,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一般是通过法律来惩罚犯罪的人,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在对待暴力的态度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思想有相通之处,基督教《圣经》反复强调“勿以暴力抗恶”,“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圣经》马太福音5:38论报复),可见上帝对罪行的惩罚虽然严厉,却并不想完全遗弃罪人。基督教教义的独特性在于以“原罪和救赎作为展开对人与世界,此岸与彼岸,理性与信仰的描述与阐释,它们提供的是一套如何面对和选择世界的价值意义问题”④。
《原野》中的人物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善的代表又是恶的化身,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当双方的强弱对比发生变化时,人物的身份随之发生变化。“情节的发展进程就体现在从善与作恶两条道路上痛苦抉择的过程,体现为仇虎在情感上向善而在行动上却不得不作恶的矛盾中痛苦挣扎,备受煎熬的过程。”⑤所以《原野》的基本冲突就是善与恶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当处于受害者的、代表善的一方的仇虎杀死焦大星并间接害死小黑子时,他也就由为善者转变为作恶者,进而承受焦氏的诅咒和心灵上的负罪感。“当恶发生转移时,它并没有减弱,而是在产生恶的人身上加强了,这是增殖现象。恶转移到物上也一样。那么将恶置于何处?应把它从不纯洁处转到自身的纯净处,这样,把恶转化为纯粹的受苦,自身的犯罪,应把它施于自己身上。”⑥
曹禺的情感取向是“劝恶扬善”,在价值判断和情感寄托方式上合乎基督教的精神,曹禺在《日出》跋中说:“这样我挨过许多煎熬的夜晚,于是我读《老子》,读《佛》,读《圣经》,我读多少那被认为洪水猛兽的书籍。我流着眼泪,赞美着这些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他们怀着悲哀驼负着人间的酸辛,为这些不消的子孙开辟大路。”⑦有研究者称曹禺身上有着一种保罗式的使徒精神,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阶级意识的淡化与作家的道德关照
与阶级意识直接相关的是仇虎的身份问题。仇虎的身份孤立地看是农民,但联系戏剧的内容看,他又不只是农民。早有学者对把仇虎定位为农民提出疑义,身份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会影响到仇虎形象塑造的成功与否,也涉及到对剧中矛盾斗争性质的认定。“显然,在焦、仇两家这种友好、平等的关系中,焦阎王算不上‘地主、‘恶霸,仇家人亦算不上‘农民。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⑧这样把仇虎的身份看成是破落户子弟更为恰当一些,因此焦仇两家的冲突,阶级成分已经没有意义。只有把仇虎的身份看成不只是农民,才能更切合作品的本来面目。
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把《原野》处理成农民向地主讨还血债的简单的复仇故事,而是写出了人物人性的复杂性,从而超越了狭窄的阶级性的限制,再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有更广阔的视野去批判黑暗的旧社会对人性的戕害。仇虎在杀焦大星时心理出现了动摇,毕竟他们曾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想先激怒对方,自己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杀死他。虽然作者并不赞成这种以暴易暴的行为,但对仇虎的过失还是抱有一定的谅解的。例如,作者在剧中有大段的抒情性语言赞美仇虎“在黑的原野里,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的。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⑨。
“照通俗的说法,‘罪通常意味着某种事实上的罪或者作恶的行为。然而在神学上,兴趣却在于从态度所产生的具体行为,因为正是态度才是基本的恶。”{10}仇虎在实施复仇的过程中,情感是向善的而在行动上却不得不作恶,父债子还的传统观念令他无法忘记家人的惨死,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幻觉中出现的场景:父亲、妹妹无辜被害丧命,阴间审判时他们却仍被判刑,焦阎王依然逍遥法外。基督教主张饶恕,“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圣经》马太福音6:14论饶恕)。仇虎虽然有罪,但在态度上可以谅解,并不像焦阎王那样罪无可恕。
“当曹禺将自己的灵魂与上帝的道德意识融为一体时,他自身的苦痛已转化为普遍的恶本质,他本人也是作为上帝意志的代言人从而具有了拯救人类众生的使命感。”{11}这句话道出了曹禺思想中与基督教思想相通的道德意识,但是曹禺并不是想担负上帝的职能,他无意做一个道德法官。他在信仰方面还远未达到一个基督徒的虔诚的境界,曹禺只是想通过《圣经》寻求人生问题上苦闷的暂时解脱,寻找超越现实黑暗的精神性力量,所以他想从基督教《圣经》中吸取合理的部分,指导自己的创作和生活,在作品的具体表现,就是作者的高尚的道德意识。例如,“周冲衬出《雷雨》的阴暗。……他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是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智慧的上帝做主宰。”{12}
曹禺借用西方基督教思想来透视旧社会里人性善恶相杂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可以说这种借鉴是成功的,他的前期剧作中流露出一个现代作家的高尚的道德关怀,没有说教的痕迹,《原野》淡化了阶级斗争的色彩,避免了单一的阶级视角对观照视野的限制,向观众、读者展示了人性的广阔的“原野”,从而使作品具有了长久的艺术魅力。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杨晓冬,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①④ 王本朝:《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和文体资源》,《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3月第28卷第2期。
②③⑥[法]薇依著:《重负与神恩》,顾嘉琛、杜小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68页—第69页,第69页,第71页。
⑤⑧ 董炳月:《论〈原野〉的精神内涵——兼评〈原野〉研究中的某些观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
⑦{12} 曹禺:《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32页,第14页。
⑨ 曹禺:《原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第171页。
⑩ [英]约翰·麦奎利:《基督教神学原理》,何光沪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第1版,第252页。
{11} 宋剑华:《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的结构模式》,《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