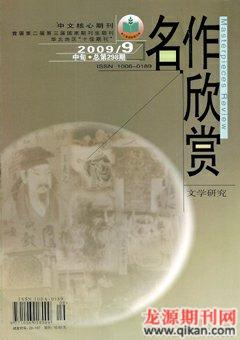正常人与疯子
关键词:鲁迅 狂人日记
摘 要:《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开创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它在穿越了近百年的时空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依然极具启发意义,发人深省,充满了思辨的力量和自我解剖的勇气。
阅读鲁迅,我总是无语;不是无话可说,而是百感交集,无从说起;忽然想起鲁迅为自己的散文诗集《野草》所作的《题词》首句:“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不觉中,这位精神界的战士已经离开我们七十寒暑了,然而我们今天的生活似乎并没有成为曾经想象的那样。如果鲁迅先生能活到今日,看到今天世界的这番模样,不知会作何感想——在世界更大的变动到来以前就匆匆离去,于他而言亦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在我看来,鲁迅是深邃的、是超越的,他看到的、想到的、发现的、挖掘的问题绝不仅是他的时代独有的,而是人类或者至少是中国人最根本、最本质、也最普遍的问题,既长久存在又根深蒂固,既难以克服更难以根除。他看得比几乎所有人更深、更远,因而他是独特的,是异于常人的。他之所以能写出《狂人日记》这样的小说,塑造了一个狂人的形象,从某种角度说是因为他有切肤之痛,感同身受。在被他称为“自言自语”的《野草》中,他流露了很多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都是写给自己看的,他不指望、也不希望更多的人去看,或者能真正地读懂。他只暴露了自己思想的一小部分,已经不能被人理解和接受了。我们常能看到他这样的自白——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时候是更无情的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
这样的文字在他的作品里实在不是少数,不仅仅是他流露最多个性思想和最隐秘声音的散文诗集《野草》,就是他的小说也颇多此类或隐或显的告白,或者说是内心深处的困惑和探寻。即使像《故乡》这样看似充满温情的乡土小说,也设计了“我”这么一个被隔绝的孤独者形象,关于童年的浪漫记忆原来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眼前的现实毫不留情地轻松地将“我”击败。于绝望中,鲁迅写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然而这句话如《狂人日记》最后的“救救孩子……”《药》中的花环一样令作者怀疑,也许只是阴冷、绝望的鲁迅给读者的一点安慰吧。
先觉者的悲哀不仅仅在于他的孤独,他的呐喊如旷野的呼喊般没有响应,也没有回声;更在于他往往被视为异类,疯子。其实世上本没有正常人与疯子的区别,所谓“正常”与“疯”都是人为的规定罢了,含有约定俗成的意思,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无约束的权威秩序”。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大家都这么说或做,这些被众人认可的语言和行为便可视为正确的、正常的,而凡是与此相对的,自然被视为错误的、不正常的。于是耳边又响起那句话:“从来如此便对吗?”真可谓振聋发聩、一语中的。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事情,或者从来都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一定都是对的,有时候甚至是完全错误的,真理却被扼杀或埋藏,这就产生了所谓多数人的暴力。
又想起了苏格拉底临终的讲话——少数服从多数便会造成多数人的专制。即当多数人认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无论这件事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管实际的效果如何,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件很有可能是错误的事情就被认定是正确的、正当的、合适的。当古希腊人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裁定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时,正是对真理最大的嘲弄,这个裁定本身即证明了苏格拉底言论的正确。真理被践踏和亵渎了。尤为可悲的是,人们往往能够识别少数人的独裁和专制,并进行反抗或斗争,却看不透另外一种其实本质相同,只是力量更为强大,也更为隐蔽的多数人的专制。狂人最后终于病愈,去某地候补了,这是庸众对独异个人的胜利,也是多数对少数、群体对个人、“正常人”对“疯子”的胜利。不仅消灭了异己,甚至将其同化为自己的一部分,绵延千年的封建礼教的威力可见一斑,从中也可窥见人类向习惯妥协和向群体的趋同感。
作家张中晓曾说:“少年时候,真理使我久久向往,真实使我深深激动。但现在,我感到真实像一只捉摸不定的萤火儿,真理如似有实无的皂泡了。”“对待异端,宗教裁判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的方法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本心的话。”这些都是作家沉静思考后的肺腑之言,体现着思辨的力量和理性的光辉。“所谓‘奸邪与‘中正,不过是美化自己和丑化他人的语言罢了。”借用到这里也是非常恰当的,所谓“正常”与“疯”、常态与变态不过也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设计罢了。
世界上一切法律、规章、制度都是人为规定的,是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为了便于管理,根据种种制约关系而制定的,它的合理性本身就值得怀疑,说得极端些,它只不过是一部分人制定的游戏规则而已,本身就有不完善的地方。而我们大多数人却以此为标准和准绳,衡量一切也制约一切,超出这一范畴的,自然被认定是非常态的、不合理的或者错误的。于是,那些先觉者,那些真正掌握真理的英雄,不是被视为疯子,就是被视为狂人,不仅被他们所反对的人排挤着,也被他们要拯救的人打击着。如果说来自反对者的攻击因为在意料之中还能够抵御的话,来自后者哪怕是轻微的质疑、非难都是难以承受的。
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对他的这一观点作了很形象的诠释,在这篇文章中,真正有行动的人是个傻子,他是真的傻吗,还是大家都认为他傻?进一步追问,大家都认为傻的人,他就一定是傻子,就真的傻了吗?在《灯下漫笔》一文中,鲁迅曾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两种:一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样的概括实在太精辟、太透彻了,连奴才都做不了的时候,当然渴望做稳奴隶的日子,于是一旦有人要破坏、反抗现状,自然被认为是傻子或是疯子。只有将异己的行为归类为痴傻或疯癫,排斥出正常的人类行为圈子,自己才是安全的。人类排斥异端、清除异类、划分类别,甚至种族屠杀等行为背后正是有着这样的动机和考虑吧。
说到这里忽然发现其实很难对“正常”和“疯”下准确的定义的,尤其当这一概念出现在非医学领域的时候,有人在研究京派文人沈从文先生时曾提出过:“疯”是指思想争斗不休、茫然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而“狂”则是思想意识十分清醒状态下采取的带有极端性的言行。用英国小说家切斯特顿的话来说,狂人并非是失去理性的人,而是失去除理性以外所有的一切的人。汪曾祺也说:“沈先生在精神崩溃的时候,脑子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来还很准确。”这就是狂人超凡的地方,狂人具有不同凡俗的眼睛,鲁迅笔下的狂人就是从常人看了几千年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
“正常”与“疯”实在只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正如荒诞派戏剧大师尤涅斯库的剧作《犀牛》表现得那样,当人类全体异化为犀牛的时候,少数尚未异化的人类在已经变成犀牛的人类眼中却变成了异类。换言之,在当今异化的社会中,坚持真理、坚守信仰的人往往不被理解,被视为异端或不正常的,并最终被时代和社会所抛弃。就像《犀牛》中的女主人公最终也放弃理想和真理,加入到犀牛的大军中去了,可谓与《狂人日记》有异曲同工之妙——先觉者,或曰“狂人”,被庸众同化,向世俗妥协,并最终成为“正常人”中的一员,何其悲哀。剩下孤独的男主人公独自飘零于天地之间,荷戟彷徨的战士也是一样。
英雄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社会前进的车轮有时候是靠少数人推动的。真理不会以多数人的标准为标准,更不会以少数人的规定为标准。如果掌握真理的是疯子,那么我希望疯子能多一些——毕竟命名只是个符号而已。
(责任编辑:张晴)
作者简介:黄昕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