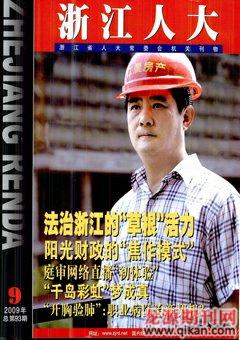人性与法
刘 刚
在星光灿烂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的司法文化盛极一时,光彩夺目。虽然西方现代司法文化的传入导致了中国本土司法文化的断流,但“以史为鉴、可以见兴替”。从古代文献中的点点滴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司法文明大观,亦可更全面地总结出法律天生的缺陷。
据《初刻拍案惊奇》记载:“明朝年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有一王生,一日踏春饮酒归来,见一卖姜老翁与家丁争执,便上前一探究竟。言语几句后,王生怒将老翁推倒在地。老翁痰火攻心昏将过去。王生顿时酒醒,将老翁救活后,连称不是,讨些酒饭与老翁吃后,又拿出白绢一匹相赠。老翁自渡船回家,王生以为相安无事。该夜一船家找到王生,言老翁于船中发病死去,老翁死前央其告官索命,并以竹篮和白绢为凭。王生顿时慌乱,欲以金银止祸端,船家得重金后与王生家丁连夜将尸首掩埋于偏僻之所。过了一年光景,王生一家丁胡阿虎由于误事被王生重打,怀恨在心,于官府告发王生年前杀人掩尸一事。官府挖出腐尸并取言于街坊,加以刑讯使王生招供入狱。年过半载,老翁故地重游,上门拜访。王生家人始知此乃冤案一桩。官府最终查明此乃船家借死尸设计诈银。王生无罪出狱,免成冤魂。船家被重杖至死,人财两空。”
这则传奇的民间司法故事涉及了一个历史性的话题——“人性与法”。所谓人性,即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法因人而立,依人而行,故法难逃人性的影响。船家是本案的罪魁祸首,他利欲熏心,借用一具浮尸,将老翁手中的竹篮和白绢买过来,利用天黑的时机,实施了这桩诈骗案件。这些只是船家计谋的硬件条件,但此案的软件条件在于法律的威慑力和人趋利避害的本能。法是用来惩恶扬善的,法是人们寻求正义最重要、最有力的武器。而此时此处法律的威严被船家肮脏的不良动机所利用,法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的工具,这不是与法的初衷背道而驰吗?
这种歪曲利用的根源便是人性。家丁胡阿虎虽然有举报犯罪的义务,但他却是在遭到王生毒打后才上报官府,我们可明显看出胡阿虎公报私仇的丑恶目的,法律成了其泄私恨的工具。虽然法律并不关注原告的报案动机,但法律尊严却因此大打折扣。既然人为了牟利、为了私恨而利用法律,那么人们也可以由于其他层出不穷的欲望和私念去恶意用法。
在中国古代,人们的正义观念是相当朴素的,而且具有宿命论特点。人们相信公平、正义是上天注定。“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我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上天必定会秉公执法,从而维系人间稳定的社会秩序。在本则故事中,卖姜老翁的再次突然出现便被看成是上天维系公正的努力。
有意思的是,如果王生真的含冤而去,人们只会将此看作命运使然,是对前世罪孽的弥补,或是为了来生后世积蓄阴德。王生后来考中进士,苦尽甘来,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似乎从轮回转世的长远视角去看,上天也一定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正是这种“天持正义”的文化观念使古代中国的人们很少利用法去伸张正义。
古代中国产生厌讼文化的一个原因在于,古代法制的严峻和人们对司法认识的不正确。在保守的农耕文明中,人们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里,错综复杂的亲情、家族、近邻、乡里关系使人们彼此之间十分熟悉,使人们不自觉地联合起来回避司法的过多干预,从而更好地维护原来的人脉关系。王生为了劝说船家帮他逃脱关系,便说道:“你我同是温州人,也须有些乡里之情,何苦为着外人报仇。”胡阿虎在向官府告状时也说:“这尸首实是一年前打死的,因为主仆之情,有所不忍。”而知晓王生与船家达成协议埋尸逃罪的还有其他家丁,他们一起隐藏事实便是熟人文化使然。
“三纲五常”的传统和男权社会的特征使王生之妻刘氏不可能去揭发丈夫的“罪行”,这点也被“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所肯定。因此,司法更多的被古代中国文化排斥在日常生活之外。
刑讯在封建时期是获得口供的重要方法,但知县却将其作为唯一的方法,先后对王生、胡阿虎、船家进行了刑讯。虽然刑讯并没有导致屈打成招,但有滥用刑罚、草菅人命之嫌。在对船家的处置上重杖至死过于严厉,船家本是诈骗钱财的罪行,而知县却言之凿凿地说:“你这没天理的狠贼,你自己贪他银子,便几乎害得他家破人亡。似此诡计凶谋,不知陷害过多少人?我今日也为永嘉县除了一害。”岂不知,知县自己也是酿成冤案的因素之一。如果我们戏剧性地将知县换作狄仁杰、包拯等公正智慧的官吏,或许就不会导致故事中的结果。不管多么完美的法制也需要人去执行,优秀的执法者才能让法制发挥光芒,达到法律预期的功能。
日月交替、沧海桑田,当代中国的法制已经比古代先进完善了许多。但法律与人性本能、社会文化、科学技术、执法主体等诸多要素的争斗和互动仍然要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