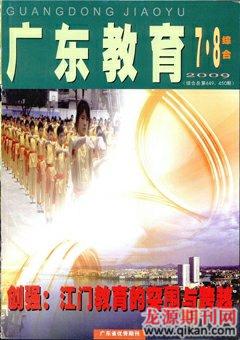远远地望见我的学校
嘉 禾
九十年代:希望工程、普教、高教、职教、普师、单亲家庭、单亲子女、新东方、西部支教、贵族学校、互联网、新概念作文大赛……
普教·普师
1990年春天,那是我师范毕业分到新街小学教书的第三个年头。
学校还是老样子。一条沙石乡村公路通往不远的小镇,从那公路拐下来,走上一条长满青草的机耕道,两里多地,看见一个四周被农田包围着的小村子,只有五六户人家,被绿树掩映着。前边两排长长的整齐的民房,布瓦粉墙,连围墙也无,两排房中间,横着两间更小的房子,是厨房,靠山墙码着枝枝丫丫的木柴。有两个攲斜的乒乓球台,是唯一的娱乐设施。报到那天是老校长领着我从学区过来的,她一路走在前边,满是皱纹的脸上堆着笑,客气里仿佛带着点歉意,推开办公室的厚重的木板门,迈过门槛的时候,她还在重复着说,马上要区划变更了,新街小学会成为新成立的法龙乡的中心小学。正在伏案办公的几个老师也一起抬头冲我点头,客气又带着几分好奇的笑,打量我。那天我的情绪一直不高,还沉浸在一种深深的失败感中不能自拔。当时我是全乡第一个师范生毕业“下”到小学的,同一届的同学,有的留城了,回乡的也全都分在中学。
其实到1990年的时候,乡中心小学的牌子也还没挂出来。过去两年里又有新的师范学校毕业生分下来,小学中学都有。听说乡中学也有了历史上第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乡教育管理委员会一开始借用乡中学的几间房子办公,后来有了新的楼房,人员配备相当齐整了。基础教育陆续有了一些新的动向。天气好的时候,乡里的教研员会骑着单车远远地从机耕道过来,听听课什么的。“六一”也会有全乡的文艺汇演,就在学校的土台上,二胡、唢呐、锣鼓、电子琴都搬上长着青草的舞台,虽则简陋,但台上台下,每个人的表情,是认真、严肃而热切的。
我的第一次全乡公开课被安排在这一年的四月份。由于教室太小,听课的老师又多,只好转到中学去讲。我夹着书、备课本,学生帮忙抬着两块小黑板,排着队,浩浩荡荡地往中学进发。行进在麦苗、菜花的香气里,看见乡村公路两旁的白杨都长出了好看的新叶,有淡红,有嫩绿,鲜得很。我讲的课题就是袁鹰的散文《白杨》,连着讲了两节,据说是得到了一些好评。但当时自己对教学理论仿佛还很茫然,只记得小黑板上应该是按规矩写了一些关于目标教学和学法指导的东西,这也是县教研室那几年里一直在推的。
县教研室多了一个活动课的教研员,偶然听到我的课,就鼓动我在全县讲一次活动课的公开课。这个难度更大,因为不光没有现成的课例可以借鉴,甚至连教材都没有,能够讲下来,多数恐怕还是凭了自己的大胆和随机应变,感觉自己更像一个不太合格的游戏主持人。倒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外乡镇年轻人,在听完课后聚到我住的房间,谈得很投机,后来成了一直交往的朋友。教研员着实费了一些心思开展农村学校活动课,她说哪怕一所学校只抓一个项目也好啊,比如跳绳、象棋、球类等。我喜欢在自己班上踢足球,也带动其他班开展起来。校长好不容易批准买了一个足球,很快踢破了,我也不好意思再求着校长买,就每个孩子捐几角钱,花23块在镇上供销社里买了一个小一些的黑白相间的足球,风里、雨里、雪里都没断过,甚至在学校运动会上还把足球列为其中一个比赛项目呢。
再往后,我带的头几届学生当中,有的也师范毕业陆续分到小学来。一直到2000年8月的那届中师生毕业,在当时的湖北省内,作为一个时代教育标志的中师生已经成为历史。原来的县市级师范学校,或者升格成为更宽泛的职业学院,或者改办了高中。
贵族学校·外面的世界
大概是1995年左右,还在乡下小学的时候,我在一个同事宿舍里品红茶。这茶在以前闻所未闻,说是来自在海南工作的亲友。后来就聊到了那边的私立学校(当时是一律称之为“贵族学校”的),以及在当时看来颇为不菲的工资,感慨一番,有些动心,但还是搁了下来。
不久后,镇上终归还是有人去了南方教书,断断续续地传回来的信息似乎还不错。于是我也寄了些简历出去。是1998年冬天吧,有了一个到浙江乐清面试的机会。那天起得很早,孩子还在熟睡。镇上的街道也还在冬日寒冷阴沉的薄雾里静默着。一个人瑟缩在破旧中巴车阴暗的角落。客车从家的窗下街道上驶过时,不觉眼泪就出来了。
真正走出去是在次年元宵后,一个风和日暖的天。学校是在被称为“才子之乡”的江西临川境内,远离市镇的一处非常荒僻的所在,规模颇大,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有,据说公司所属的私立大学也正在筹划之中。校园里颇多榕树,这榕树显然并不是江西的“土著”,有人说老板是福建人,榕树也都是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可能兼有乡土和文化的双重意味。
春天时,满山的映山红开得如火如荼,极有气势。但学校是全封闭管理的,除了每月一次的假期,学生平时绝不可以出校门。老师们晚饭后出去散步时,老有女孩子在校门内央求:“老师,给我们带束花回来吧。”我们尽量多带些映山红的花枝,供在教室里。但心底里酸酸的感受却挥之不去。除了月假,平时周末学生也在校,安排相对宽松一些,也会定期放两场露天电影什么的。出于纪律和安全的考虑,排路队几乎成了私立学校的一景,尤其是在小学。从教学区到饭堂、宿舍有几百米的距离,都是一列列的路队,唱着歌儿。特别记得晚修结束后从教学楼回来,有一处明亮的路灯,夏天的灯光总会吸引许多飞虫,地上也落一层。孩子们总是在走到路灯下的时候就不动了,围着看,叽叽喳喳地,显出活泼的天性来。这时我也常抬头望望星空和暗夜里静默的起伏的丘陵,想自己的心事。
生活的轨迹就像是一条河,曲曲弯弯地,终于汇到珠三角这片热土上来。香蕉林,椰子树,众多免费的公园、博物馆、美术馆,同时,学校的塑胶跑道,教室里联通世界的电脑平台,孩子们的礼貌与活跃,家长的事业心与教子经,常常使我感慨。一个因为调皮从别班转到我班上来的孩子,运动会上他憋着劲要拿成绩,特地买了一双金色的专业跑鞋,跑完100米后觉得不够劲,跑200米时执意脱了跑鞋,赤脚冲刺,没想到脚皮都被磨破了一大块。我问他疼吗,他只是咬着牙摇头。不久这孩子全家移民去了檀香山。后来我偶然试着赤脚在塑胶跑道上走走,很扎脚,都不大敢落地,真不敢想那孩子是怎么赤着脚冲下来的。
在私立学校做事,压力自然是有的。但学校大多会有一些细致体贴的安排,体现出人文的理念来。譬如定期提供水果牛奶凉茶,教师生日聚会,节日里每人送一束鲜花,等等。
当然也免不了辗转。我落脚于现在的学校,是因为面试时被一位长者的话所打动:“你在底层啃过草根的,有一些积累,应该有一个发挥的地方。”当时举家从一百多里外的另一个城市过来,一辆小型货车,载着不多的家当,晚上快十点了才到这个全新的城市。司机路不熟,好不容易找到学校安排的住地,打开宿舍门,房间里却是空空如也,又赶紧想办法找新的临时住所,解决一夕之安。纵然如此,但对教育理想的坚持,对生活的执着,却不曾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