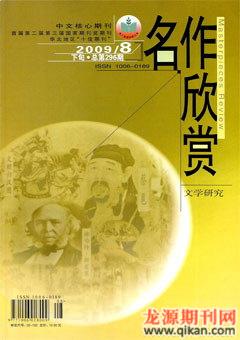流放地上的权力狂欢
路 杨
关键词:卡夫卡 《在流放地》 刑罚 权力狂欢 “局外人”
摘 要: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以其独特的叙事为我们呈现了一场权力的狂欢。小说以“刑罚”作为中心意象,以摇摆的“局外人”立场,表达了卡夫卡在面对人类生存处境中的“权力”以及“权力膜拜”的思考和绝望。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卡夫卡都称得上是现代主义小说家中第一位重要人物。正如英国大诗人奥登所言:“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困境。”①作为最早感受到20世纪时代精神特征的一位作家,卡夫卡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独特而深刻的审美世界。
一直以来,小说《在流放地》都吸引着无数的读者和评论家。故事本身并不复杂:流放地的一名军官向一位来考察的外国旅行者详细介绍了一件罕见的刑具和奇异的行刑过程;军官料想新指挥官会借机废止这一制度,当他获知旅行者不肯站在自己这边时,他自己接受了刑罚并最终与机器一同毁灭;旅行者参观了前指挥官的墓碑后,匆匆离开了流放地。
然而,“它效果强烈,因为它完全不是一篇具体的幻想作品:小说通过它的写作方法提供的是一种对事实的感觉,你可以解释它,自由创造它”②,其主题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卡夫卡曾表示过希望在“惩罚”的题名之下把该作品和《审判》、《变形记》合集出版,故有研究者认为作品表现的是“罪恶与惩罚”等具有普世意义的命题;另一类评论家或认为作品表现了人类历史在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的矛盾,或看到了其中的“政治预言性”;还有评论者将作品看作一种宗教寓言,大多谈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救赎思想或“原罪”意识;甚至有人将《在流放地》与精神分析学说结合,认为作品表现了一种“口头施虐狂”③。
纵观各类观点,虽然各自都能自圆其说,但多少有脱离文本之嫌。从文本出发,行刑机器无疑是小说的一个中心象征。本文就旨在从“刑罚”的直接意义出发,通过小说涉及的三方面形象来透视“流放地”背后的“权力”主题。
一、军官:刑罚与权力的共谋
《在流放地》中,“刑罚”的意象以行刑机器的庞大形体和军官受刑的残酷场面出现在旅行者面前。“军官”的形象则贯穿在他对行刑机器的详细讲解、对行刑过程的巨大热忱以及对前指挥官的顶礼膜拜中。而这二者所展示的正是一场“权力的狂欢”。
先从被判决者所触犯的戒律谈起:“尊敬你的上级!”德国学者赫伯特·克拉夫特谈到,“这句话,是一个戒律,但并非上帝的戒律,它要求大家承认社会等级制度,从而把统治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④。“戒律”,是权力机构制定的,本身就是统治阶级权力意志的反映。“戒律”被打破就意味着权力受到了挑衅,统治者必然需要一个程序来证明自己对权力的掌握是不可侵犯的。此时,由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刑罚”就起到了重振权力的作用。
流放地的刑罚一直是以公开处决的方式进行的。当刑罚被公开,“重振权力”的意图就得以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得到昭示。“我们不能把公开处决仅仅理解为一种司法仪式。它也是一种政治仪式。即使是在小案件中,它也属于展示权力的仪式。”⑤刑罚最终是要使处决人的权力得到彰显,暴力则因此得到了其合法性地位。在这层意义上,刑罚完全和权力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
《在流放地》中,军官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权力膜拜者。“军官干将很起劲,不知是因为他对于这台机器推崇备至,还是出于别的原因,他不能把这份工作托付给别人”;他抱怨着“前指挥官在任时,我可以随意支配一笔专用于此的款项”,而“如今,机器的维修费用被大大削减了”,“他们正在密谋撤销我的审判权”, “老指挥官的说服力我具备一点,他的权力我却一点也没有”——军官渴望的正是“处决”象征的权力,恐惧的也正是权力的流失。
军官对机器和判决形式不厌其烦的介绍以及对往昔行刑场面的狂热追忆,则是通过一种语言狂欢的形式来达到对“权力”的假想式占有。然而当“讲解判决形式”这种过去使军官“深感荣幸”的“审判长的职责”而现在却成为了“随便哪个士兵都可以做的事”时,他愤怒了,因为“讲解”背后的权力意味开始被消解,他不能再由此来实现对于权力的掌控。
处在“自以为拥有权力”和“权力的实际被剥夺”这样一个不平衡的状态之中,军官只能选择“语言狂欢”来实现自己假想中的权力占有,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疯子式的执拗和审慎。讲解已经成为一种完全仪式化的、带有浓重的“献祭”色彩的行为:他“身穿紧绷绷、挂满肩章绶带、仪仗队式的军服”,三次“洗手”,“兴趣盎然”。军官往往会陷入一种“自说自话”式的迷狂状态之中,以至于“忘了站在他面前的是谁”,其表述总是从有对象的回答逐步滑向无意识、无对象的独白,内容则集中在机器构造、犯人罪行、行刑过程和老指挥官在任时的行刑场面以及对旅行者的请求这五部分内容上。军官所完成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旅行者的交流,而是通过在语言上对行刑机器进行无限夸大和推崇,对前任指挥官及其统治进行完美化、神圣化言说以及对新统治机构的蔑视与侮辱来完成一场“强迫症式”的语言狂欢,从而在假想中来满足内心对权力的渴望。
无论是鲁迅笔下擅长“精神胜利法”的阿Q还是当代作家刘恒笔下的贫嘴张大民,语言狂欢,向来是人们调整自己社会地位的一种惯常策略。正如巴赫金所说,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等级关系恰恰相反”⑥。只有在这种语言的狂欢中,军官内心不平衡的权力关系才能够得到调整,以使自己相信,刑罚与权力的共谋不会被任何人消解,自己仍是唯一有资格持有“刑罚权力”的人。
而另一方面,对整个流放地而言,这种权力膜拜其实早就有其狂欢化的所在:“山谷里已人山人海;都是为了亲眼目睹处决”;“在数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观众都踮着脚站着,那边的斜坡上站得满满的”;“数百人苍蝇似的簇拥在土坑周围”。
这种盛大的观刑具有的全民性、仪式性正是一种狂欢化的体现。这种行刑方式得到的绝不仅仅是来自军官一个人的拥护。“刑罚”作为暴力的合法化形式,使围观的人们从中得到了释放和发泄阴暗人性的快感。这样的公开处决不仅重振了统治者的权威,还制造了一个将权力“下放”的假象:仿佛人人都可以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对犯人进行宣判,正所谓“公开的酷刑和死刑应该是引人注目的,应该让所有的人把它看成几乎是一场凯旋仪式”⑦。统治者需要在民众中得到支持和帮助,来使集权统治得到拥护和认可;而对围观者而言,他们在非狂欢式生活中所经历的强大的等级关系正是在狂欢中得到了变更与调整。民众之所以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不过是因为那虚假的权力下放;行刑结束时让人感到不无遗憾的并不是“正义的光辉”的消逝,而是那短暂的“权力持有”将脱离狂欢回到非狂欢化的生活常态,他们也将重新跌落回没有权力的普通人。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得出的结论:“真理”不过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谁掌握权力就掌握着“正义”和“公理”。“罪行总是毋庸置疑的”,是因为没有人会对“权力”置疑。
由此可见,无论是民众观刑时的狂欢还是军官的语言狂欢,其背后的动力机制都在于刑罚与权力的共谋。正是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和信仰,才造就了流放地永远被放逐的悲剧。
二、指挥官:守旧与革新的对峙
《在流放地》中,除军官和旅行者之外,还存在另一对隐性的对峙关系,即代表着专制政权的老指挥官和代表着新温和派的新指挥官。有的评论家由此将小说主题的矛头对准了传统专制文化。但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新旧对峙可信吗?我们能否简单地将其归为一个传统专制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对立?流放地是否能随着军官和机器的毁灭走向新生?面对这些问题,卡夫卡书写了他的绝望。
首先,无论老指挥官还是新指挥官,都是被军官叙述出来的,我们无法看清他们的真正形象。前者已经死去,后者语焉不详,其对峙在文本中并没有直接的呈现,可见二者其实是不在场的。这种对峙双方的同时缺席让我们开始怀疑这种叙述的真实性。
“不在场”的老指挥官也许只是军官用语言狂欢完成的一种“精神支撑”式的假想。其存在已远远超越了一个具象的个体存在而上升为一种旧有权力机制甚至价值体系的强大象征。军官一切具有献祭色彩行为的最终指向是这个符号的象征而非其实体,是一种存在于军官精神深处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记忆和精神实质。观刑的盛况和被判决者的麻木无知充分说明了这种精神传统并不会因为“老指挥官”或“行刑机器”的毁灭而毁灭,而其实质就是一种对“权力”信仰的膜拜。
同时,“不在场”的新指挥官恐怕也只是军官的一个假想:他甚至将那个莫须有的“所有高级官员的大会”上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指挥官将要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反应都作了精心细致的设计,仿佛是在导演一出必将发生的戏剧。这种强迫症式的假想充分说明:“新指挥官”不过只是他内心恐惧的化身,军官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抓住旅行者,就是希望通过反对“新指挥官”来取得旧有制度的维系。在这里,“新指挥官”也同样成为了一个符号,象征着迫使旧权力体系走向崩溃的力量。
但事实上,“新指挥官”并不具有这种使旧体系崩溃的绝对力量。旅行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到的是:新指挥官想要废除行刑机器的愿望并不像军官口中那么明确——“他对这种程序的看法如果真如您所认为的那么明确,那么,这种程序的末日恐怕无需我的绵薄之力就来临了。”这道出了“新指挥官”所代表的“新温和派”的实质:变革的不彻底性。新权力机制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历史继承性,充其量只是发生在旧有体系内部的一个动摇,而非根本性的革命。这种动摇既体现在守旧一方(军官)外强中干的“脆弱性”上,又体现在革新一方(新指挥官)的“不彻底性”上。卡夫卡利用新、老指挥官的“缺席”将这场新与旧的对峙叙述成了军官一个人孤独的坚守与抗争,在他一个人身上同时反映出了在权力信仰控制下他所坚守的历史魅影和他所抗拒的未来幻象,这正说明:无论“守旧”还是“革新”,权力膜拜正是二者同构的群众心理基础。
在流放地,对“权力”的膜拜几乎已成定局,从历史中带来,并将带入历史中去。虽然卡夫卡设置了“旅行者”这样一个旁观者的形象,但旅行者从来就没有感到自己真的具有阻止这种刑罚或改变这种状况的责任和能力。卡夫卡在文本中告诉我们的是:人们并没有像某些评论者所言由于旅行者引进了另一种生活视角而“产生出痛苦或受难的生存体验”;相反,在“流放地”的“铁屋子”里,连“叫嚷”都已经无法使人们醒来。这从那个被释放了的“被判决者”对军官的报复和对刑罚机器的迷恋上就可见一斑。流放地上的人们还在深受着历史记忆和传统思维的控制,导致他们看待新文明时所使用的仍旧是旧的眼光。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后被判决者和士兵“逼迫旅行者把他们带走”绝不是出于什么对生存困境的觉醒和抗争,而是因为他们从自己命运的巨大逆转中发现了:现在旅行者才是真正的权力占有者。现实主义的鲁迅在《风波》、《阿Q正传》中告诉我们:人们心中的所谓“革命”也不过是想通过暴力霸占别人的家产、妻女,成为新的权力阶级;现代主义的卡夫卡则告诉我们:这种无始无终的“权力膜拜”决定了旅行者不带走他们,也带不走他们,因为他们从精神深处已经没有了觉醒的可能,无论走到哪里也将永远属于这片流放地。
这才是卡夫卡真正的绝望:“守旧”已成为历史,“革新”却无法创造未来,“外来者”无能为力,在权力信仰的缠绕下,没有人能够拯救甚至唤醒流放地。
三、旅行者:摇摆的“局外人”
德国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曾说:“没有一部德国中篇小说能像《在流放地》的作者那样,以如此自觉的力量抑制自己任何内心感情的参与……作者以极其大胆和非常冷漠的态度讲述整个故事。”⑧而旅行者这个与流放地没有任何关系的“局外人”身份为这种冷漠叙事提供了便利。然而,“局外人”本身其实很难置身事外,旅行者一直在内心进行着一场“介入/不介入”、“理性/非理性”的思想交锋,并一步步被牵扯进事态之中,成为了一个摇摆的“局外人”。
随着“刑罚”意象的展开,旅行者从开始时的“难以集中注意力”、“兴趣并不大”到“更觉得这军官值得钦佩了”到“想问这问那”,逐渐露出了一个窥视者的兴趣。其心理过程包括了两个“自我”的对话:一个“自我”出于民族观念在告诫旅行者保持作为一个“局外人/旁观者”所需要的必要的距离;而另一个“自我”则出于人道感在说服旅行者介入并阻止这次处决。更关键的是,旅行者渐渐反映出对这一惩罚体系的尊重和承认:“他对军官所讲的审判程序不满意,却只能提醒自己,这里是流放地,特殊的惩处是必要的,彻底的军事化做法是必须的”,后来甚至对军官的权力信仰产生了“敬佩”、“感动”等积极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旅行者是出于一种“认同”才终于选择了“不介入”。
正如旅行者对军官所说:“我既害不了您,也帮不了您。”在这里,他最终选择了双重的“不介入”:出于理性原则的判断和人道感,旅行者不会协同军官维护该制度的存在;但他也不会出于同样的原因出面去阻止这次处决。这种对权力信仰的“默认”随着军官走上行刑机器而愈加强烈,旅行者甚至觉得若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会这样做的”,并为军官之死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此时的旅行者已经摆向了权力信仰的一端。
旅行者“摇摆”着,并一步步地从理性旁观堕入了非理性旁观。在街边茶馆,流放地一方面用潜伏着的精神传统感染着他,一方面又用“老指挥官”墓碑上预言的强大力量威胁着他,这使旅行者意识到了“光复流放地”的强大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虽然他最终逃出了流放地,却已经在这种双重夹击之下和流放地建立了某种非理性的精神联结,默认了流放地的权力信仰,其出走不过是一场无奈的遁逃。
不仅如此,小说的叙述者其实也是一个在两个“端点”间摇摆的“局外人”。“这部作品非同寻常的一面是,通常和他的主人公相认同的卡夫卡,在这个故事中他却在两个主人公之间摇摆不停。‘困难在于卡夫卡的写作,尤其是《在流放地》,给读者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卡夫卡自己所采取的立场既像是军官又像是旅行家。”⑨
事实上,军官和旅行者之间本来就存在一个相互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军官恐惧旅行者强大的人道理性,但旅行者也深受军官权力信仰的影响——叙述者正是在这二者的关系中间“摇摆”不定。最终军官为了他的信仰死去了,旅行家逃回了自己的文明家园,叙述者还是没能在这二者之间停下来,他找不到可以供他回归的地方。
格非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卡夫卡的故事是一个不发展的故事,从起点回到起点,或者说在被各种因素的纠缠中陷入了泥沼,剩下的就是一只秋千的摆动……如果对幅度加以严格限定,它更像是一只钟摆。”⑩在《在流放地》中,叙述者或者卡夫卡本人的立场也可以以此来概括:他绝不认同“军官”非理性的权力膜拜,却又无法抵抗这种精神传统的引诱;他表现出了对“旅行者”所代表的理性原则的不信任,但又不能指出一个更可信的方向——他在这两端中找不到平衡点,只能任由它们在发展中停滞和错位;没有人能够拯救流放地,卡夫卡是绝望的。
然而这种叙事背后也许还存在着更大的隐喻。米歇尔·福柯对人类刑罚历史的考察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参照。如果以“现代”作为一个模糊的分界,那么在历史进入“现代”之前,“酷刑”从来都与“肉体痛苦”和“公开仪式”密不可分,那些真实案例中的行刑方式无一不是“用精心计算的间歇和连续的伤残来拖延死亡和加剧死亡的痛苦”,这与“流放地”又何其相似。现代刑罚虽然已经有了“示众场面的消失和痛苦的消除”这样的变化,却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福柯称之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惩罚景观的旧伙伴——肉体和鲜血——隐退了。一个新角色戴着面具登上舞台”,但“在现代刑事司法体系中存留着‘酷刑的痕迹。这种痕迹从未完全抹掉,而是逐渐被非肉体刑法体系包裹起来”{11}。可以想象,“新角色”如旅行者之流,即使是作为现代理性文化的代表,他们所谓的人道、理性和正义,不过也只是换了一层外衣的“权力工具”罢了,其中刑罚与权力的共谋仍旧没有消解。肉体痛苦不过是被代之以话语权的剥夺甚至精神上的暴虐,真正发生的只是“惩罚运作对象的置换”,而刑罚背后的“权力经济体制”仍旧无处不在。旅行者之所以最终和流放地建立了某种非理性的精神联结,也许正是因为在潜意识中他已经发现自己的文明国度和流放地在本质上的同构。卡夫卡用旅行者的“摇摆”向我们泄露了旅行者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社会的“权力实质”,同时又用叙述者的“摇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如果说流放地是走入现代之前的历史,那么旅行者就是一个窥探历史的现代人,然而在时间的坐标之上,无论历史还是现代,权力和“权力膜拜”的精神传统都贯穿始终。军官和旅行者不过是一丘之貉,与其说卡夫卡的立场是在摇摆,不如说全部都放弃;卡夫卡之所以在二者之间停不下来,是因为二者都不值得他停留。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说:“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12}卡夫卡用他的荒诞隐喻书写了福柯的这一兴趣所在,同时也书写了他自己的绝望。
卡夫卡在每一个路口摇摆并徘徊,却终究找不到一个足够可信的方向。《在流放地》所写的绝非是某个具体的专制社会,在人类永恒的生存处境中,“权力”的膜拜与狂欢无处不在。
福柯认为,“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它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我们可以通过讨论或历史来质疑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或通过艺术创造向它挑战。
然而,仅仅是“挑战”。我们能否找到某种努力的方式彻底将“权力”驱逐出去,或是永远逃出“权力”的放逐?卡夫卡没有告诉我们,也无法告诉我们。但他和他的文字至少点燃了人类思考自身生存处境的自觉,在这一点上,卡夫卡无疑是伟大的。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路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① 转引自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② 转引自叶廷芳主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121页。
③ 以上关于《在流放地》的主题的各种探讨,参考了学者胡志明的研究成果,详见于胡志明:《卡夫卡现象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3月版。
④ [德]赫伯特·克拉夫特:《卡夫卡小说论》,唐文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87页。
⑤⑩{11}{12} [法国]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第51页,第38页,第17页,第33页。
⑥ [苏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6页。
⑦ 转引自[德]扎东斯基:《卡夫卡与现代主义》,洪天富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⑧ [捷]伊凡克里玛:《卡夫卡灵感的源泉》,崔卫平、崔建军译,《天涯》。
⑨ 格非:《卡夫卡的钟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