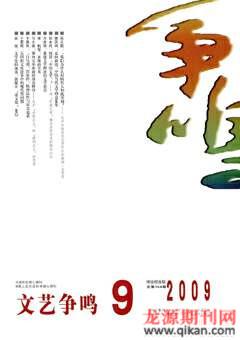《尘埃落定》的象征性分析
寇旭华
阿来,《尘埃落定》是一部充满寓言性和象征性意义的长篇小说。小说主干,即统治阶层关于权力的攫取和争斗,具有显而易见的寓言性。阿来曾谈到:“有批评家看出了小说中的寓言性质。寓言可以让读者会心一笑,原来一个土司,跟一个国王皇帝争斗起来是一样的。我在写作时也经常有会心的联想。”《尘埃落定》总体上可说是一部权力寓言,其政治意味很是明显。但同时,小说文本带有藏文化独特的魅力和光彩,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识,在描述与其他文化互动的部分充满独特的象征性意味,笔者认为这也是小说最有个性、最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本文试图从小说的象征性意义入手,对其背后所隐含的特定时代民族文化心理加以解析和研究,找出小说真正所欲表达的意蕴所在。
一、理性反思:弱势文化的宿命
藏族文化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高原文化,有史可考的历史至今也有1500年。宗教在藏文化中一直具有意识形态统治地位。藏传佛教凭借各地方割据政治势力的支持,在广大藏区传播,影响着藏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意识,并逐步渗透到了藏族社会的方方面面。相对于中原文化来说,藏族文化相对地缺乏主动性和创造力。在《尘埃落定》中,藏族土司制那种封闭性农奴社会体制下,这种文化的衰落就是必然的宿命。在《尘埃落定》一书中这种宿命却表现为一个命运的怪圈。
《尘埃落定》的主人公是一个傻子,这个傻子身为土司的二儿子,表面上不知世事实际却大智若愚。年纪渐长,这个本来为土司家族所轻视的傻儿子出人意料地对权力象征——也就是土司的继任者位置产生了觊觎之心。而他那富有远见的判断力在家族议事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显露出来。比如建议土司父亲要少重罂粟,多种粮食。结果在其他土司因少种粮食而闹饥荒时大赚了一笔,巩固了麦其土司的政权;免除百姓的一年贡赋,使土司更受拥戴,等等。哥哥死于非命后,他终于成为麦其土司的未来继承者,土司家的仇人对他评价“他是土司们的土司!”这无疑是土司制时代一个优秀人物的象征性化身。
然而,土司制度还是不能被智慧的傻子少爷挽救,他眼睁睁地看着父母的官寨在汉人大炮的攻击下轰然倒塌,变为烟尘从此灰飞烟灭。他的成功的人生命运被历史车轮无情碾过,就此幻灭。作为生命个体,傻子少爷象征了弱势文化的自我改良和完善,其轨迹是上扬的,而外界力量的强大,又将这上扬的轨迹拉回终点,构成一个宿命的怪圈。就是说,无论是弱势文化中的个体生命多么辉煌,在历史潮流冲击下,也逃脱不掉如微尘般迸散落下的命运。相比于某种内在力量造成的毁灭性命运,这种宿命具有更深刻的悲剧感觉。
就像古希腊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一样,俄狄浦斯为逃避弑父娶母的可怕命运,越是积极行动扭转命运越是陷入被动,最后刺瞎双眼而自我放逐。人的自由意志与盲目命运的冲突在此得到充分展现。《尘埃落定》中也有诸多对于土司制度将要灭亡这一结局用超现实手法描述的种种预言与暗示,如引种罂粟做鸦片生意以及傻子二少爷的妻子与大少爷通奸所引起的先后两次地震,傻子常做的那个“明明是下坠,却又非常像是在飞翔的梦”,种种征象都造成一种类似于索福克勒斯悲剧的神秘的宿命感。但事实上造成《尘埃落定》傻子少爷命运悲剧的外在原因并不神秘或盲目。现代社会,弱势文化落后、保守、不合时代要求的硬壳势必要被先进文明所打破。土司制度土崩瓦解的宿命无疑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尘埃落定》渲染了原始神秘宿命氛围的同时,也并未否定这一点,却加深了弱势文化身处其中却并不自知造形成的悲剧感。在土司制行将崩溃的前夕,书中饶有寓意地设置了一个细节:土司们从汉人妓女身上染上了致命的梅毒,身体开始腐烂、发臭。从外在到精神,土司制都已近于朽烂。
所以,《尘埃落定》中,土司制所象征的弱势文化的衰落宿命,是由其文化特性所决定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发展进步的原动力、内驱力的先进与落后、自主与被动之别。
二、二律背反:当弱势文化遭遇强势文化
阿来比作家马原和扎西达娃笔下的西藏更进了一步,阿来并不是在写异乡异闻,而是在写一种原始状态的人和魂,他灵魂的根系深植在藏文化的土壤深处,他的精神始终在那片神奇的光芒之中。因此,按照形象学的提法,阿来的笔下的藏文化可以理直气壮地相对于文本中的异族文化而言,称为”本我”,即文本中的本土文化,也是叙事者;而与”本我”相对应,发生关联的、被描述的异族文化则可视为“他者”。”本我”描述“他者”的方式似乎往往出于潜意识,正如法国形象学(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专家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所说:“这个‘我想说他者(最常见到的是出于诸多迫切、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
就《尘埃落定》的文本而言,对于“他者”即强势文化的形象表述,就颇耐人寻味。
首先是“两毒意象”。先是鸦片之毒。小说前半部分写到,前来调节土司之间的纷争的国民党特派员以回报高额财富为诱饵让土司们用大部分土地种了罂粟,制成鸦片向内地贩卖,结果引起不祥之兆,“当麦其土司在大片领地上初种罂粟那一年,大地确实摇晃了” ,富有寓意的一笔隐喻着土司政权被强势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动摇了。罂粟在书中被描得很美,“罂粟开花了。硕大的红色花朵令麦其土司的领地灿烂而壮观。我们都让这种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土地上的植物迷住了” 。就是这种金玉其外的植物似乎隐喻着“他者”文化给”本我”文化带来的异质因子有些是有毒化作用的,或说是负面影响的,并不因“他者”的强势地位而一定带有进步因素。“梅毒”意象更说明了这一点。傻子少爷无意中给边界小镇引进来一个打着戏班子旗号的妓院,“我要说这是一个古怪的戏班,这个戏班不是藏族的,也不是汉人的”。土司们光顾了妓院,染上了梅毒。这种疾病是以前从未在这块土地上出现过的,无疑也是强势的外族文化传播而来。相形之下,弱势文化的土地是那样圣洁,却被“他者”文化中的腐坏因子毒化了。“鸦片”和“梅毒”这两毒意象反衬出弱势文化的原始性的纯洁和无辜。正如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所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
再如《尘埃落定》中的汉人形象。比较典型的、具有前后发展连续性的两个人物分别是土司太太和黄师爷。这是两个具有复杂意义的人物,他们是融入”本我”的“他者”。土司太太是个出身低微的汉族女子,作为藏族土司太太之后,“他者”文化特性在她身上仍时有体现。傻子少爷在婴儿时期就似有所觉:“奶娘把我从母亲手中接过去。我立即就找到了饱满的乳房。她的奶水像涌泉一样,而且是那样的甘甜。我还尝到了痛苦的味道,和原野上那些花啊草啊的味道。而我母亲的奶水更多的是五颜六色的想法,把我的小脑袋涨得嗡嗡作响”。相形之下,藏族奶妈更具有大自然的淳朴天性,而汉人母亲(土司太太)却是颇多思虑、工于心计的。土司太太习惯叫人知道她处于痛苦之中,用她的怀乡病,用她的偏头痛,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不受欢迎的辛辣气息。如果说,小说中的妇女形象还只是更多具有原始主义“原始快感”的本真形象,只反映了“他者”的表层部分,那么小说中汉人黄特派员就更具有“他者”文化的深层文化特质,即政治心理部分。文本对此的描述颇多讽刺、幽默笔调。他的形象是“瘦削”、“黄脸”“一口黄牙”、“手掌很小,手指却很长”,观赏歌舞前先要闭着眼睛作诗。对于土司来说,他的想法、心计简直不可理喻,让藏人土司手足无措。而继任者姜团长的形象也很有意思,与黄特派员相反,他是一个健康的汉人形象,“壮实“、”喜欢肥羊和好酒“,而且对那种病态的“写诗”十分反感,这似乎是一个汉族的“真”人形象,外表与心理都健康,引得土司和儿子高兴地大叫:“姜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姜的朋友!”令他们料想不到的是“这人不光是黄特派员的对头,也是麦其家的对头。黄主张只使一个土司强大,来控制别的土司。姜的意思则是让所有土司都有那个东西,叫他们都得到银子和机关枪,自相残杀” 。
“他者”的心理是这样难以捉摸,甚至多有可怕之处,对于作为“本我”的弱势文化而言,这个问题恐怕总要问下去:“汉人的脑壳里究竟在想什么?”(11)
如果说,《尘埃落定》对“他者”文化形象有某种批判性意味的话,那么这种批判的尺度是十分复杂的。作者为母亲和黄特派员这两位“他者”文化人物选择的命运结局,即其“故事情节的书写”,与土司制时期汉藏文化的正面、积极的交流这方面的“状态保持着关系”。这一点是不容忽略的。土司太太是”本我”的代表人物即傻子少爷的母亲,土司除了短暂艳遇,始终爱着这个汉族女子,象征意义上讲“他者”文化的血液通过此人物而融入了”本我”文化体系之中;她临终对儿子表白:“她叹了口气,说:‘在今天要死去的人里面,我这一辈子是最值得的。她说自己先是一个汉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藏人了。闻闻自己身上,从头到脚,散发的都是藏人的味道了。当然,她感到最满意的还是从一个下等人变成了上等人。”(12)
这一段表白举重若轻,寓意非常深刻。无论土司太太这个“他者”文化人物的“他者”成份多强烈,还是被”本我”所同化直至深深爱上”本我”文化,而且甘愿为之自杀殉葬。这时的”本我”文化从狭义讲是土司制时期的藏文化,土司太太随土司制灭亡也不算突兀;但从广义象征意义讲,则是“他者”文化对”本我”文化的最大的肯定,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相异性此时由于文化互动,文化互融关系而转成同一性。
正如巴柔所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在个人(一个作家)、集体(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关集体(一种思想流派、意见、文学)的层面上,他者形象都无可避免的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13)这就形成一个奇特的现象:尽管弱势文化因为迟滞、落后而陷入受强势文化掌控并随社会发展而衰落的宿命,但在强势文化面前仍有其尊严和价值,并与强势文化形成二律背反,成了强势文化的反面观照:那里没有理性,却有激情、神奇和本真的残破,没有进步或现代化,却象一个远去的田园或重新发现的圣洁之地。换言之,强势文化有其丑陋,弱势文化亦有其美丽和尊严。小说在反思弱势文化宿命的同时对此似乎有着深深叹惋和失落。因为“千百年形成的民族文化观念、文化心理是根深蒂固的,远非一朝一儿夕便可以改变和谈化得了的。相反,越是现代化,越是处于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巨大反差之下,那潜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意识,民族归属感,民族风俗习惯反倒由于这种反差的刺激而变得更加强烈。”(14)而这一切都源于对本民族文化深挚的热爱。《尘埃落定》结局主人公死去之时,有这样一段描述:“上天啊,如果灵魂真有轮回,叫我下一生再回到这个地方,我爱这个美丽的地方!”(15)这种民族乡土之爱正是一切失落和悲怆产生的根源,它不为理性反思所拘,象孩子对母亲的爱那样从性灵中喷发而出,超越了时间、超越了死亡。《尘埃落定》结局也便自然而然由此落定。
在《尘埃落定》的寓言性描述中,中土司制无疑是落后、腐朽的,但作为其所象征的文化基石仍不失其绚烂与神秘之美;另一方面,它也引起我们对文化“他者”意义的思索,作为民族的整体自我意识是在与“他者”的交往、接触、碰撞或冲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成熟的。在民族文化碰撞中“他者”文化的积极因素不容忽视,因而,在保持民族文化记忆和接受具有他者性的多元文化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一方面使民族文化抛弃非现代性的文化因子,尽快使民族文化心理实现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结构性转换,一方面又要十分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使它不致被市场化、商业化和科技化的浪潮所吞没,依然保有原生态文化的魅力,这或许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健康方面。这也可看作《尘埃落定》给我们留下的延伸性思考。
注释:
(1)《<尘埃落定>:一本神秘的书》亚辰访谈阿来 ,人民网,2000年10月27日。
(2)(3)(5)(6)(7)(9)(10)(11)(12)(15)阿来: 《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392页,第165页,第61页,第42页,第364页第6页,第159页,第35页,第398页,第407页。
(4)(8)(13)[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摘自《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主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第157页,《尘埃落定》阿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
(14)李子贤:《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
(作者单位: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