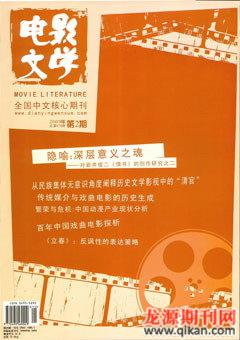浅谈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白宝善
[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个奇异的亮点。在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传奇的书写与建构中,女性主义是她们笔下最能体现女性社会与市民意识的载体。张爱玲与王安忆的作品将女性作为立文的视角,时刻关注着女性的命运,从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对女性加以观照,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凸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关键词]女性主义;张爱玲;王安忆;人文关怀
一、引言
在张爱玲与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小说中,情感与婚姻是其贴近小说主题、描写女性生存状态的切入点,写得最多,颇为得心应手。不同的是,在关照女性的生存境遇时,张爱玲始终用冷静的目光自发审视女性的寄生心理和奴性病疾,王安忆则采用热切的眼光自觉地关注着女性的独立、坚韧与成熟,张爱玲的作品重在揭示,王安忆的作品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赞赏的态度。
二、奴仆到女人的回归
1,依附寄生的女性
张爱玲集中揭示了男权话语社会里女性精神奴役的创伤及其对男性的依赖。在漫长的封建男权社会话语中,“天道阳尊阴卑,人事男尊女卑”,女性作为被放逐于男性权力文化之边缘人与失语者。“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们,都先后对男性的中心话语表达了强烈的反抗。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伤痕累累的心灵及其对平等、自由、独立精神的渴求,在冰心、丁玲、萧红等的作品中被屡屡展示。然而,这些作品中少有对女性自身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逐渐形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进行审视,而把女性的深重灾难完全归之于男权中心社会。“张爱玲对女性群体的心理病疾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在她的笔下出现了女性的自我观照、自我审判、自我解构的新气象,并且她把笔力集中在揭示女性的负面”。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的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挣扎在百孔千疮的感情世界里。身为女性,张爱玲冷眼静观,她对女性群体的不幸遭遇和心理瘤疾有着清醒的认识。她认为,造成女性卑下地位和不幸命运的原因,固然是由于男权话语社会及其意识形态,但女性自身的愚昧麻木和驯顺奴性,则是其解放自身的重要障碍。
2,坚韧成熟的心灵
在王安忆所处的年代,时代的发展与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使女性逐步摆脱了服从男性统治的地位,大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因此王安忆笔下,女人的情感婚姻大都可列为“谋生”之外的“谋爱”。这些女人执著地追求着爱情,在感情的漩涡中苦苦挣扎,甚至在爱情的寻找中迷失了自我。《逐鹿中街》中的女教师陈传青,因担心丈夫古子铭有外遇而不辞劳苦,日日跟踪着丈夫,与古子铭作着心智的较量。《米尼》中的米尼,偶然与阿康相识相爱,阿康因偷窃被捕后,米尼竟也靠偷窃养活自己与阿康的孩子,后来又在阿康的诱引下堕落成了妓女并参与了卖淫组织,坠入一个肮脏、丑陋的罪恶世界。米尼的自甘堕落是为了“情”,最终迷失于情网而为男人所出卖。如果说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一定程度上尚处于自发状态,王安忆则是以自觉的姿态来正视女性的。当女性摆脱了男权意识的控制,她们逐渐变得独立、成熟而坚强,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中相继投入到社会生活中,饰演自己的角色,展现自己的风采。王安忆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成长,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
三、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承传与拓新
张爱玲可以说是现代女性主义小说的第一人。张爱玲将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正如她在《传奇》的扉页上所写:“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王安忆作为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中成就最大,对海派精髓领会最深的一位,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拓展着自张爱玲以来建构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新天地,并对“张派”一脉作最富有创造力的延伸。对上海这个多面体,王安忆有着理性的认识,在她的上海书写中,没有对时尚的炫耀与展览,她聚焦的是城市的日常生活。她紧紧依偎着多姿多彩、新鲜润泽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貌似风花雪月的故事演绎中,渗透着包括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文化意蕴、市民情趣在内的民间写作立场。“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投缘,那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
我们在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小说中实实在在地读出了历史的沧桑,看到了人性的善恶,可以说,王安忆是在一步步地向坚韧的人生态度靠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小说创作是承接了张爱玲透视世俗人生的衣钵,但她对女性主义人生的体会更带有主动性和自主性。在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上,王安忆也表现了她独特的人生态度和鲜明的个人立场。作品在展现女性主义生活世俗的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现人性,不是知识分子的某一群体而是大众的人性。如果说张爱玲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关于苍凉和凄美的追忆,王安忆更多的带给人们的是关于人生的感悟和一种临危不乱、处事不惊的人生哲学宣言。
四、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价值
张爱玲与王安忆分别以其女性意识和人文关怀,从女性日常的生命流程人手,就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描写女性的生存境遇,反映以女性为代表的市民精神状况。张爱玲的作品从历史场景中的女性人手,侧重表现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自发地审视女性依附寄生、自甘卑下的心理痛疾,揭示女性悲剧的深层内因,对女性的“原罪意识”进行展露和鞭挞,目光犀利,悲天悯人。作为新时期的女性作家,王安忆以平实的格调,注重描写女性主义生活场景中女性外在生存价值与内心体验,自觉致力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权力的争取,表达女性生存的韧性,赞赏其蓬勃的生命力,以热切亲近的目光倾心关注女性思想和精神的成熟,在社会变革中寻找女性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具有更深厚的社会内涵。她们的作品对于丰富小说与女性写作,具有积极的意义。张爱玲与王安忆对女性主义生存状态的刻画展示着女性生活的精髓,“这种对以女性为代表的市民精神的描绘渗透了作家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观照,也使得上海这个都市更富有迷人的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