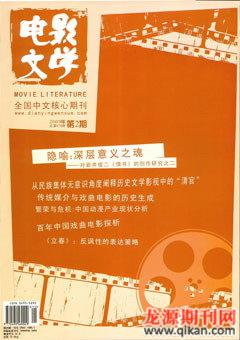挣脱不出的生存困境
张晓艳
[摘要]尤金·奥尼尔是美国现代戏剧史上最杰出的剧作家,他十分关心美国的社会问题,力图通过戏剧形式加以反映,因而他的剧作总是弥漫着悲情意味和对人类困境的悲剧性发掘。本文拟通过分析奥尼尔晚期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玛丽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进一步揭示其戏剧的艺术魅力。并试图通过这一形象,透视尤金·奥尼尔时代的精神危机,感受现代入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生存困境;困扰;纠结
尤金·奥尼尔是一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剧作家,也是美国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不但在美国影响深远,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被认为是美国戏剧的奠基人,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许多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将他列为20世纪最杰出的剧作家之一。在他的戏剧作品中,奥尼尔创造出了许多倍受瞩目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从多方面反映了这位伟大剧作家的妇女观,其晚期作品《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玛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一女性形象身上奥尼尔展示了人类心灵价值的缺失,并由此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1956年在瑞典首次上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ALongDaysJourneyintoNight)是尤金·奥尼尔后期以自己家庭为素材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剧本,也是最受评论家称誉的一部作品。罗伯特·斯比勒评论说,这部剧是美国二战以后发生的最伟大的文学事件。迈克尔·曼海姆甚至说这是一部可以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相媲美的伟大悲剧。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是一出四幕剧,讲述了一个由失败者组成的家庭在避暑别墅的冲突。整个剧作围绕着一天当中蒂龙夫妻二人和两个儿子的对话展开,每个人物都与奥尼尔的家庭相对应(小儿子爱德蒙的原型就是作者本人),甚至连时间都是一致的——1912年。虽然一开头亲昵的蒂龙夫妻对话和餐厅里兄弟俩轻松的笑话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情节剧,但随之而来的激烈对白却揭示了这个失败者之家的可怕真相:丈夫杰姆斯是一个不得志的莎剧演员,走南闯北到处奔波,但常年只能演出一个角色,事业上的失意渐渐也磨灭了他的才气,成为一个碌碌无为、吝啬小气的中产阶级地产商;妻子玛丽原本是一位“大家闺秀”,爱好音乐,从小在修道院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立志做一个修女,却因为嫁给了杰姆斯而跟随他四处颠簸,居无定所,并因为生育小儿子爱德蒙时找廉价的庸医为她止痛从而让她沾上吸毒的瘾,成为一个靠注射吗啡过活的瘾君子,大儿子杰米是个不折不扣的潦倒之人,靠着父亲的推荐找到工作,根本没有花过力气去找别的工作,整天什么事都不想干,在父母那儿吃白食,却又时时刻刻嘲讽父亲的吝啬。他痛恨母亲吸毒上瘾,并出于嫉妒而贬低弟弟在报社取得的成绩,而自己却“从来就不知道一元钱的价值,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终日只知道喝酒嫖妓,“每星期一拿到工资就扔给酒馆和妓院”,一辈子没有奋斗目标,“一辈子就从来没有存过一元钱,一年到头是个穷光蛋”,小儿子爱德蒙原本是一个热爱诗歌的船员,认为母亲之所以染上毒瘾都是由于父亲的吝啬,因而常常埋怨责备父亲。对哥哥杰米的放荡行为爱德蒙很不以为然,却也受到哥哥的影响,养成了吃喝嫖赌的习惯,并不幸感染上了在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纠结在失败和痛苦的深渊之中,不能自拔。他们每个人的不幸都不是孤立产生的,都和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紧密相关,纠缠在一起,从而成为他们之间激烈争吵和互相埋怨指责的理由。而处于风暴中心的母亲——玛丽更是心力交瘁,无力挣扎出面临的困境。
玛丽刚一出场的时候,虽然已经五十四岁了,但“体态依然年轻、优美”,让人不禁想到她“以前一定绝顶漂亮,即使现在,仍然楚楚动人”;“她衣着朴素,但天生地懂得挑选合适的服装”,“说起话来声音柔和动人”;“她个性中最动人之处还在于那种从小在修道院里养成、始终没有从她身上消失的质朴自然、毫不做作的妩媚——种内在的、超凡脱俗的天真”。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了解到少女时代的玛丽充满幻想,她的理想就是做修女和成为钢琴家。但实际上她的这两个理想却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方向的未来之路——远离俗世去追求自我灵魂的升华(做修女)或走世俗的道路(成为钢琴家)。在她还懵懵懂懂,并未真正对未来的道路作出选择的时候,她爱上了比她大11岁的杰姆斯·蒂龙,并和他结了婚,准备做个贤妻良母,为丈夫生儿育女,过着温馨的家庭生活。这种生活是玛丽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为女人规定的角色。但随后的生活并不如玛丽先前所想,她在婚后得成年累月地随着作为巡回演出的演员的丈夫“一晚要跑一个地方,住蹩脚的旅馆,火车脏得要命,生孩子,连个家都没有……”丈夫杰姆斯还爱去俱乐部和酒吧间,总觉得把钱用来给家庭盖房屋是很大的浪费。这一切使玛丽十分苦恼,孤独压抑,甚至想到了自杀。尤其在产后误信庸医的话注射吗啡,从而染上毒瘾后,更产生了变态心理,常常沉溺在自责和悔恨的纠结之中,难于自拔,不但自己痛苦异常,也给家人带来了困扰,使整个家庭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综观全剧,我们可以发现,玛丽的精神生存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源于她心中爱的困扰和对过去的纠结。
正是出于对丈夫杰姆斯真挚的爱,玛丽放弃了结婚前的理想和追求、她所希望实现的个人成就——做修女或成为钢琴家。嫁给了杰姆斯后,为了使心爱的丈夫不感到孤独,玛丽抛下了正在出麻疹的杰米和还是婴儿的尤金,到她所不喜欢的旅馆去照顾杰姆斯,结果造成了尤金的死亡,给自己带来了永远无法摆脱的内疚和悔恨。她不想再生孩子,也认为自己“不配再生孩子”,可她又顺从丈夫的劝告怀上了爱德蒙,导致新的更大的痛苦——产后病重时误信庸医而从此染上毒瘾。玛丽在遭到种种不幸后,虽然指责过丈夫给了自己一个“从来就不是个家”的家;也曾指责丈夫为了省钱请了一个“出卖灵魂”的庸医,害自己染上毒瘾,指责丈夫以酒当药“把杰米培养成酒鬼”,毁了前程。但是当儿子嘲笑父亲的吝啬时,玛丽柔情地讲述起丈夫穷困的过去,斥责儿子不尊重父亲叫他“老头几”,维护着丈夫在孩子心目中的尊严,当爱德蒙也责备父亲灌他酒喝时,玛丽又为蒂龙辩护,说丈夫遵照的是爱尔兰人给孩子压惊的传统办法,袒护他,处心积虑地为他遮掩。婚后的玛丽只知道如何给丈夫自己的爱,只知道一味地去服从,到头来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甚至她那以前是很美丽的一双手都变得“从来没有安定的时候。关节炎症使手指变弯、骨节粗硬,给人一种残缺的感觉,看上去十分难看”。这样的一双手当然不能再弹钢琴了,少女时期的梦想早已在婚后颠簸的生活中破灭了。如果我们从玛丽的角度来看待她所遭遇的一切,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的悲剧实际上是从结婚开始的,她并没有背叛当时的社会给她规定的角色——生儿育女做贤妻良母,相反她对丈夫某种程度上的言听计从才是她种种痛苦的根
源。
对往昔的纠结是玛丽精神困扰的另一源泉。她曾经说过“我们当中谁能忘记过去?它困扰着我们大家”,她当然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玛丽甚至是个在往事中寻找幻象的幻想家。她自己承认,她沉溺于毒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药能带你往回走——回到很远很远的往昔。直到再也不觉得痛苦为止。只有过去那些快乐的日子才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但那些她所认为是快乐的过往是真实地存在过,还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她的幻想呢,后者的成分要更多一些,所以实际上玛丽是靠着幻想在过日子。
年少时的玛丽有理想,有追求,希望实现个人的成就,婚后的玛丽就像当时的传统妇女一样,相信“孩子只有生在家里才能长成大人,女人要想当好妈妈,得有个家才行”,但残酷的现实让她永远也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孤单无助的玛丽只好到吗啡里寻求安慰,在毒品中湮没,缩回到自己的梦幻世界中去,靠回忆来支撑自己,使自己暂时从痛苦的现实中摆脱出来,在幻梦中找到一块逃避现实、放松自在的处所。玛丽就这样沦陷在对年轻时代的回忆中,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少女年华和短暂的恋爱时光,她在全剧的最后一句话“我跟杰姆斯好上了,有一段时间过得很快活”里只字不提他们的婚姻,这也正好说明玛丽放弃自己的追求以后所得到的幸福只是短暂的,但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去改变去征服自己的命运,永远也不能正确地面对自我,最后被过去的阴影所淹没,沦回在精神生存困境之中。
女性都不可避免地在敌对的世界里备感孤寂和痛苦,对命运深感恐惧。玛丽说“我们谁也摆脱不了命运的摆布。……直到最后你永远失去自己。”沉溺在往昔岁月里的玛丽希望自己“能找到失去的信仰,能再像过去那样向上帝祈祷就好了。”但最终,她痛苦地意识到“我丢失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有了这件东西,我就不会感到寂寞,也不会感到害怕。我永远不能丢失它……因为失去它,我失去了希望。”剧中玛丽的精神生存困境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道德精神的沦落和人的社会生存困境,用哲学人类学开创者马克斯·舍勒的话来说,就是“人不再知道他是什么并且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由于自己有疑问,他以无比的忧虑研究自己的意义和世界,研究自己来自何方,走向何方”,也就意味着自我观照和自我定位的错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