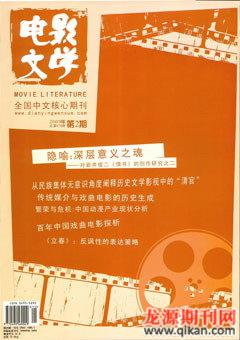《立春》:反讽性的表达策略
葛 娟
[摘要]《立春》表现了人物内在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冲突。更具写实性和戏剧性,这正得益于它的反讽性手段的运用。对《立春》而言,反讽首先是一种艺术技巧,通过对比性的镜头展示传达其强烈的反讽意味。再者,反讽的意义价值体现在反讽本身包含的批判精神上;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说,反讽作为一种表达策略,是编导对影片中主人公人生命运和现实处境所作的艺术化处理。显示了反讽者的睿智和幽默,表现了反讽者对反讽对象的超脱感和距离感。
[关键词]立春;反讽,表达策略
《立春》是顾长卫继《孔雀》之后推出的又一新作,这部片子以深度的题材开掘和独具的艺术风格获得了业内人士和众多观众的好评。虽然票房不够理想,但此片所传达比较丰赡的主题意蕴以及在镜头语言的运用等方面所作的艺术追求,成功地确立了它在当下国产艺术片中醒目而独特的地位。
如果单从剧情来看,这部影片表现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使我们不禁想起《孔雀》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以及她骑着单车拉着降落伞飞奔的镜头。但两部影片在主旨表达以及艺术表现方面多有不同,如果说,《孔雀》是一种全景式的展示人物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的冲突,凸现了时代因素的作用,那么《立春》则更多地表现人物内在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冲突。与《孔雀》写意性、抒情性风格相比,《立春》更具写实性和戏剧性,而在这一点上,《立春》正得益于它的反讽性手段的运用。可以说,反讽是《立春》借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并表达比较深厚的主体内涵的重要策略。
一、反讽,作为一种艺术技巧
反讽作为艺术表达的技巧和手段,似乎很难用明确的语言来陈述它的性质,或者说,人们对认识和把握反讽还存在一定的难度。正如英国的D,C·米克所说,“反讽很难理解”,他认为:“即使在英语国家,也存在‘广义界定与‘狭义界定两种倾向,前者扩充反讽概念,直至使其成为想象性文学的基本性质或特殊性质,后者则把这一概念仅仅用于这种那种‘纯粹的反讽。”所谓的“广义”似乎把反讽当作一种类似于批判性或否定性的内在精神,或把它当作一切作品产生复杂的审美意味和丰富的主题意蕴的一种必要因素,而“狭义”的反讽则是构成“语境对于一个陈述明显的歪曲”的种种手段,“有时是一种用语上的技巧,有时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有时是一种富有效力的策略,有时又是这样一种情景,在其中,未被命名的‘命运,作为相反力量的‘代理人”。显然,这两种倾向共同存在于《立春》之中,即反讽不仅作为一种技巧手段,运用于某些场景、片断或镜头语言中,而是在整体上已内化为本片特有的审美意蕴和独特的批判精神。
反讽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是两极对立因素的相互对比,没有这种对比,就只不过是单一因素,就不能产生多重因素条件下才会形成的反讽意味,亦即反讽常常是通过对比而实现的。对比性的呈现在影片中随处可见。如影片中最先出场的周瑜,一个音乐爱好者,在听了王彩玲的歌剧演唱后,执意要拜她为师。而这个人物身上所具的反讽意味来自于编导对人物的设计,编导旨在突出身份、外形、言行教养与人物的情趣爱好之间的距离,造成粗鄙和高雅的反差。再且,周瑜追求王彩玲,这两者实际上又构成热情和冷漠的对比,周瑜在王彩玲面前无比投入地朗诵诗歌,而王彩玲则非常漠然地望着窗外。因此当周瑜真诚地向王彩玲表达爱情时,却招来了王彩玲“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的拒绝。再就舞蹈教师胡金泉来说,编导将他设计为芭蕾舞爱好者,一个小城市中的大男人,整天踮起脚尖跳芭蕾,难怪被人看成是“怪物”,最具讽刺意味的场景是演出队在街头宣传表演,镜头对比切换,一面是胡金泉兴奋地跳着他挚爱的芭蕾,一面是围观人怪异的目光,继而是讪笑、嘲弄、离开。这里,影片将芭蕾与男人、芭蕾演出与街头场地、演员与观众等都作了对比性的展示,其反讽意蕴也是令人回味的。
当然,影片最具反讽意味的对比是王彩玲的所处现实状况与她自身梦想的对立并存。这种二元对立凸显了本片的主旨,之所以用梦想指称王彩玲所谓的理想,那是因为王彩玲常常处在半幻觉中,她时常对人说:“我马上就要调到北京了”,“中央歌剧院要调我了”,可事实是,王彩玲毫无能力和条件进北京进歌剧院。电影的反讽性主要是将王彩玲“在罗马歌剧院演唱”的梦想建立在与之有极大距离的现实基础上。现实中的王彩玲只是小城市一个普通音乐教师,尤其是长相丑陋,衣着过时,发音土气,除了唱歌本身的天赋外,没有其他任何资质。因而当王彩玲找到北京音乐学院人事处自我介绍时,遭到了断然拒绝,她失去了控制,就像找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不顾一切地唱起歌来企图证明自己的实力。这时一个近镜头是王彩玲有点吊起的上衣下面过时的裤子,显示了她的卑微。整个场景中隐含的反讽是不言而喻的。
严格来讲,反讽并不是独立意义上的艺术技巧。尤其是在电影这种影像造型艺术中,编导是通过镜头、画面、场景、声音等众多电影语言的运用来表达反讽意味的。以声音为例,《立春》中人物对自全部采用方言,这在国产片中并不乏见,但方言的运用对于《立春》而言有着特殊的反讽效果。影片一开始就是壬彩玲的一段旁白:“立春一过,……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一夜间变得潮湿温润起来,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段本富有诗意的话,却用非常浓重且听起来特别土的方言说出,这对于一个酷爱歌剧的音乐教师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讽刺。方言于他们不仅是地域的符号,更是身份的印记,王彩玲、周瑜们离不开这个城市,恰如他们摆脱刁掉自己的方言一样。
二、反讽,作为一种批判性精神
反讽,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是隐含和委婉的。正因为反讽采用婉曲的否定形式,故加强了反讽的内在张力,使其表达意义更加丰富而复杂。
《立春》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强调了王彩玲在屡遭挫败之后内心的痛苦和无奈。王彩玲坐在行驶的货车上,车上是相挤着的绵羊,王彩玲双手紧紧抓住车栏杆。电影先给王彩玲面部一个近乎特写的镜头,粗糙有些浮肿的脸上布满了大小疙瘩,凸起的嘴唇露出龅牙,眼神呆滞。接着,是横竖在王彩玲面前的栏杆,身后的绵羊。再后,是远去的货车,不知驶向何方,最后消逝在荒漠的山野中。其_中一个画面,呈现的是紧贴在栏杆后的王彩玲困苦的脸部表情,有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和特别的影像意义。当我们将这一画面与王彩玲多次乘火车上北京的镜头联系起来时,那奔驰的火车恰如王彩玲乘着歌声的翅膀,在理想的天空飞翔。而眼下破旧的货车,围绕的栏杆就是困住王彩玲精神的囚牢,是王彩玲现实境遇的拟写。前后对照,反讽意味非常明显,有着美丽梦想,心高气傲,一心要离开她生活的地方的王彩玲,如今的境遇何其悲惨!同时,画面刻意突出王彩玲那布满疙瘩的脸和呆滞的表情,使人不难意识到构成王彩玲悲剧的自身因素。而这组镜头所包含的否定意识和批判精神应该说是贯穿于整部影片的。
如果说,《立春》是以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为主旨展开情节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王彩玲、黄四宝、周瑜、胡金泉、高贝贝们应不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努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当影片中的胡金泉在街头投入地跳起他心中挚爱的芭蕾时,那些围观者的不解、讪笑的镜头又在表明什么呢?是在指责观者的无知和狭隘,还是诉说舞者的孤独和悲哀,或者二者兼有?这组切换的镜头(包括接下来王彩玲上场演唱观众相继而去的情形)所造成的反讽效果是非常强烈的。高大的男人与柔美的芭蕾,高雅的艺术与杂乱的街头,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反讽就是在这两极并置的对比情境中生成的。反讽一旦产生,我们就能明白造成胡金泉、王彩玲尴尬境遇的原因了,这时,我们只能对胡金泉王彩玲的眼前境遇给予一点怜悯,而不会再指责那些围观者,到这里,我们或许已洞晓镜头的意图了。表面上,是在客观地呈现一种不和谐的场景,实际上镜头与那些观者构成了“同谋”。胡金泉、王彩玲的“角色”已完全成了被戏弄的对象,而其他所有人都成了看客。但是这一结论正与上述的假设前提形成悖论。如果再引申一下,那就是坚守自己就意味着与现实的对立,与社会的对抗,那只能头破血流,所以胡金泉最后只能采用非常的手段来调解自我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代价是牺牲自我进监狱,“终于拔掉扎在人们喉咙上的刺”。
有人认为,胡金泉这个人物在影片第二个叙事段落出现并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改变了影片的叙事视点,王彩玲与胡金泉形成了看与被看的关系。其实不然,影片中的胡金泉与王彩玲属于“互文见义”,在胡金泉身上,我们能找到同样也属于王彩玲的悲剧性命运的答案,但对于王彩玲来说,其命运悲剧性的因素更加复杂。影片在展示王彩玲理想与现实的二者距离时,更加夸大两者的对立性。这种对立恰恰构成了更深意义上的反讽。探究其反讽意义,是解读影片意旨的最直接的途径和方法。影片一开始,高音喇叭里播放了王彩玲演唱的优美的歌曲,周瑜便是被这歌声吸引去找王彩玲拜师的。当他和黄四宝看到王彩玲从远处走来时,黄四宝说了句:“我就不明白,这么丑的人竟然唱出这么美的声音!”另一镜头,黄四宝在临摹王彩玲背部形体时,王彩玲突然转过头来,镜头中光浩的:背部与长满疙瘩的脸庞反衬特别鲜明,无须多言,我们便能明白王彩玲理想和爱情破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是其相貌丑陋,而相貌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一点来说,王彩玲的不幸或许是命中注定的。显然,这是一种宿命。但事实上宿命论的观点是一直潜伏在《立春》整个叙事过程中,无论是王彩玲,还是黄四宝、周瑜,对于他们来说,生在这个小城市,本身就意味着很大的缺憾,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立春》中有两个属于不同场景的王彩玲在天安门前的镜头,联系起来饶有意味。一个是电影的开头部分,王彩玲夜晚站在天安门广场观望着天安门,画面中的王彩玲是近景,前身靠着栏杆,背向摄影镜头,远处的天安门,本应该是背景,这里无疑又成为画面的主体,却采用了模焦处理,金色光晕模糊闪烁,可望而不可及,似乎有一种不真实感。而电影结尾部分,王彩玲带着女儿来到天安门广场,摄影机采用的是深焦镜头,阔大的广场上,王彩玲和女儿对唱儿歌,远处的天安门清晰可见,王彩玲若有所思地望着它。这两个镜头前后对比,其意旨不言而喻。对王彩玲而言,也许压根就不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命中注定她应该安分守己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或者更进一步地说,老天爷给她的那副好嗓子注定了她此生的不幸。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立春》与其说是展示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不如说是在呈现王彩玲、胡金泉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苦痛,在追问他们人生的价值意义何在?当他们的理想与追求被否定,是否意味着他们生来就应该认命,就应该像周围人一样地生活和生存下去?
三、反讽,作为一种表达策略
从更高层面上来说,反讽有着极大的艺术魅力,它显示了反讽者的睿智和幽默,表现了反讽者的超脱感和距离感。正如米克所说:“观察者在反讽情境面前所产生的典型的感觉,可用三个语词来概括:居高临下感、超脱感和愉悦感。歌德说,反讽可以使人‘凌驾于幸运或不幸、善与恶以及生或死之上。”可以说,反讽的魅力之一,正在于它能把人从对反讽对象的厌恶,同情、仇恨、伤痛、绝望等消极的感受和体验中超脱出来,使观众与之保持一种心理上的距离,从而获得比较轻松、愉悦的精神享受。反讽的这种艺术魅力同样体现在《立春》中。
《立春》正面展示的是王彩玲、胡金泉等的悲剧性命运,但在具体情节的安排、场景的设置乃至演员的表演等方面或多或少地传达出反讽意味,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故事的悲剧性。比如影片一方面在多次陈述王彩玲的梦想,一方面又在突出她的种种不可能实现梦想的现实性因素,尤其是王彩玲将调北京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不明身份的北京老头的帮助上,不免让人感觉荒唐好笑。胡金泉是片中最不幸的人,但他走路时端起的架子,抬头挺胸的姿态,他舞蹈跳得好,被称赞比泰国人表演的还要好看。因此,当王彩玲、胡金泉各自演绎了自身的悲剧时,我们只能对他们寄予同情。悲剧只属于他们个人。对观众而言,没有大悲大痛。尽管影片中王彩玲多次唱起歌剧中片断:“我常把珠宝缀满圣母的衣襟,把我的歌声献给上帝和天上灿烂群星,为何,为何,上帝啊,为何对我这样残酷无情?”这段歌词应该说是对王彩玲境遇最贴切的写照了,应该说是王彩玲出自肺腑的表达,但却无法引起观众深切的共鸣。这就是《立春》的一种表达策略。
当然,消解故事的悲剧性,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愉悦需求,也不是为了回避矛盾。反讽,作为一种表达策略,是编导已超越于个体的人生悲剧,他把摄影镜头放在更高的层面上,居高临下,俯瞰人生,透视社会百态,从而使影片获得更为丰富的主题内涵。比如《立春》中高贝贝欺骗成功与王彩玲的奋斗失败可谓“相映成趣”。高贝贝的成功,在于她年轻漂亮,更在于她采用特殊的手段——剃着光头。假说是癌症患者、走后门等。而王彩玲只能活在她的梦想中。
在《立春》中,编导借反讽对王彩玲们的人生命运和现实处境作了艺术化处理,体现了编导深邃的目光、彰显现实的力度和批判的态度,但必须强调指出,反讽本质上是轻松幽默的艺术表达策略。“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好的礼品,是我们关于我们称之为人生的那桩复杂而又可疑的事物的最深刻的知识。上帝既然把它赐给人类,人类那张严肃可怖的面孔,也许会被迫挂上一层微笑。”读到这里,我们会对影片中胡金泉即使在监狱里也要踮起脚尖跳芭蕾、结尾处王彩玲幻想在歌剧院舞台演唱歌剧的情境报以会心一笑,尽管这笑是酸楚的。我们更会对“立春”二字获得更深一层的语义理解。正如王彩玲对高贝贝所言:“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我的心总是蠢蠢欲动,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可整个春天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好像错过了什么……”这段话也应该是对《立春》之以“立春”为题最好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