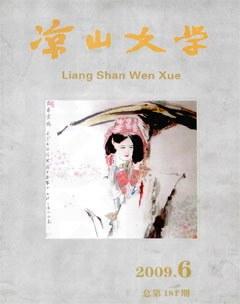川乌草乌没娘疼
蔡应律
到现在我才知道,没娘疼是一种野生食用菌。
此物正式名称为猪苓或猪屎苓,俗称野猪粪,表面呈棕黑色,皱缩而有瘤状突起,状如猪粪,故名。
这东西的怪异之处在于,它深埋在林中的某一处土里,体轻,却质硬,且断面略呈颗粒状。家乡人早先不晓得它是菌类,还以为是某种植物的块根,便努力地去找它的植株,比如茎啦藤啦甚至叶啦什么的,却没找到。没找到便去想象,说它的“果”结在山这面,它的“藤”却长在山那面;还说有经验的山民正是在山那面发现它的“藤”了,翻过山梁来,才于某个神秘的对应点上找到它的“果”的。我曾经长久相信此说法。还将没娘疼三个字理解为“没梁藤”——隐没于山梁背后的藤。当然,至今没有人告诉我这理解有什么错,是我于某一天的某一个时辰,猛然觉得,这名字,有可能不是“没梁藤”,而应当是“没娘疼”。你想,猪屎样一堆东西黑不溜秋地埋没于土里头,没根没杆,没枝没叶,没头没脑,没依没靠,没来没由,岂不可怜!我想这是山民们好不容易找到它时,惊讶、庆幸之余,生出来的怜悯感情吧。那么,找到了的,可怜;没被人找到的,就更加可怜了——它们将永埋于土里难见天日,并终老一世而自行烂掉。
关于没娘疼,我很小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传闻。说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因生吃没娘疼而被闹倒过。“闹倒”是会东家乡土语,意即“毒翻”,也就是严重中毒。家乡人认为没娘疼“生打熟补”,意思是生食可以打劳伤,熟吃则能滋补身子。
“打劳伤”即治疗劳伤。底层人命苦,稍有一点年纪,便劳伤满身,天阴下雨,便一身疼痛。好好说着话的几个人中,但凡有人提起,便人人背了手去,擂腰捶背,脸上的皱纹,也一下子扭成了纂纂。这都是劳伤。这劳伤隐藏在身上,这里那里,捉拿不到,需要药“打”。药必是毒药,以毒攻毒,且毒性愈大,效果愈好。是生活教会了人们对付劳伤的办法。
最简捷之法,便是喝剧毒药酒。这药酒家家屋里泡有一罐,里面黑不溜秋,虫虫蛇蛇,块根须根,面目狰狞,令人生畏。它是草根家庭中。一个可怕而又必须的存在:生疮长疖,跌着扭着,倒点出来搽;累得不行了抿上一小口,既打劳伤,又解乏气。这药酒便成了当家人心目中的宝贝疙瘩,由当家人藏在床脚某个阴暗处,既避免孩子误喝,更避免某个家庭成员一时想不开去打它的主意。尤其是两口子赌气的时候,倘听说一方寻短见了,另一方最本能的反应是,一把抓起酒罐来,看里面的酒是不是蚀了。蚀了多少。倘那药酒并没有蚀,便立即放下心来,算是虚惊一场;倘发现蚀了,并且蚀得多,则免不了“天哪!”发一声绝望的嗥叫,人也就瘫坐到地上,或干脆仰脖喝下所剩半罐,以求一死……
当然,更多的时候,家乡人是拿这药酒打劳伤,一身骨头骨节实在痛得很了,便去喝上一小口。
难在掌握分寸,家乡人因打劳伤而把自己闹死的事时有发生。
我的这位远房亲戚被闹倒后,始而大喊大叫。“一跳八丈高”,继而遍地打滚,央求家人使木棒捶打他,浑身上下,哪处都在喊打,且要重重地打,狠狠地打,轻了不行——地上的人在杀爷宰娘地嚎啊。家中亲人,始是愕然,悚然,待找来木棒,左掂右掂,却又哪里下得了手!不过后来就顾不得了,于是别了脸挥棒打去,且泪如雨下汗如雨下,一棒比一棒重,还忍不住跟被捶打者一道声嘶力竭,哭天喊地,直到筋疲力尽,并眼睁睁看着那个人扳命而亡……
我不知道这故事的真实性如何,我甚至不知道没娘疼生食是不是真的有毒。事实上,到提笔写此文时经网上查证,我至今没见到没娘疼有毒的说法,因此,更大的可能是,我的这位远房亲戚是吃了别的什么剧毒药物,譬如川乌、草乌、生丁子或者雪上一支蒿之类,而把帐误记在了没娘疼的身上——谁让它叫没娘疼又这般诡异神秘呢。
没娘疼切片炖肉,鲜炖、或者晒干了来炖,均可,食之没味,闻着却香。然而炖不烂,这又是没娘疼的怪异之处,文火厉火,无论怎样炖,也不改当初模样。可谓定力十足,你拿它没办法。
既是药,当然要讲功效。“生打熟补”是民间说法,典籍上却讲利尿,抗肿瘤,提高免疫力。这就了不得。人类发展到今天,能耐大得很却也日益脆弱了,各类肿瘤找上门来,躲不胜躲,逃无处逃,没娘疼能抗肿瘤,宝贝呀。于是,有食没娘疼传统的家乡人大受鼓舞,首先就是县城里拿退休金的前公职人员们,这些号称“吃饭挣钱”——只要还能吃饭,活着,就有钱拿的无所事事的一群,一天到晚背剪了双手在农贸市场和街口上转,见没娘疼就买,直把这绰号叫野猪粪的东西驴打滚般哄抬到天价上去。
但事实上,没娘疼在我的记忆里,远没有川乌草乌深刻。
原因在于,没娘疼和川乌草乌我都吃过,没娘疼淡而无味,川乌草乌却又苦又毒。
苦是巨苦。毒是剧毒。
川乌和草乌,是两种药,同属毛莨科植物,药用其块根。区别是,川乌表面比较光滑,而草乌表面皱纹较多。因二者性味相同,性热,味辛、苦,有大毒,且同具祛风湿、散寒、止痛的功效而常将它们并列并用。现在已经知道,川乌草乌里含多种毒性很强的双酯类生物碱。据传,东汉末年关羽中毒箭,华佗为他刮骨疗毒,其毒即为乌头毒。川乌又名“五毒”,草乌又名“百步草”。我不知道“五毒俱全”这个成语,是否是从川乌这个别名来的;也不知道误食了草乌,是不是走不出百步就会倒地。不过川乌草乌之毒,亦由此可见一斑了。
在我的家乡,吃川乌草乌被闹死的,代不乏人。最令人惋叹的,是我初中时代的一位梅姓数学老师。梅老师命硬,历经三次劫难,最后死在川乌草乌上。第一次是遭雷殛,一个炸雷,将他从老式电话机旁的躺椅上扯到地下,却未危及性命。第二次是饥饿年头,下乡支农,夜里起夜,头晕眼花从楼上掼下来,大难不死。第三次,为强身壮体而吃川乌草乌,竟不幸中毒身亡。
吃川乌草乌非常冒险,全家人被闹翻的事情也曾发生过。既是剧毒,却有人吃它,全部原因就在于,吃了川乌草乌,不生疮不害病。试想,穷苦山区,缺医少药,物质极度匮乏,要活命,你得不停地做;做不怕,怕的就是生病。那么,有这一条,再毒的药,也都值得冒险尝试了。至于是否真的有效,人们只能从实际感受上看。比方说吃过川乌草乌睡眠好,不起夜。而不起夜,从来被民间认为是“内体好”的一大标志。
我本人多年来都不起夜,往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是不是跟我小的时候大吃特吃川乌草乌有关呢?老实说,这问题到今天我仍是没法回答。倒是某些中药、草药,毒与不毒,既生死之隔,势不两立,又可以通过人类的智慧之手,将它们之间的那一条界线轻轻抹去这一事实本身,令我既惊讶不已,又深深着迷。当然,这都是由人类的勇敢和固执,还有无奈达成的——倘有路走,谁又甘愿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呢?
这就需要说到褚表耶了。
褚表耶即褚姓表叔。唤表叔为表耶,是会理、会东一带的习俗。褚表耶胖而块头很大,络腮胡。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年轻的父母殁
于席卷家乡小镇的那场伤寒流行病后,家住会理西街的褚表耶拖家带口来抚养我们。褚表耶家人丁兴旺,分一半到会东,加上我哥、我姐和我,有十来口人。这十来口人,甚至加上留守会理的半个家,全靠褚表耶开馆子维持生计,可见比较艰难。怕的就是家人生病。现在回想起来,褚表耶带我们的那些年中,除他年迈的母亲患有老年性支气管炎而外,全家长幼,竟没有谁患过什么病,更没有谁上医院打针吃药什么的。这不能不算个奇迹。
细究起来,恐怕就在于吃了褚表耶炖的川乌草乌。
褚表耶差不多每年要炖一次川乌草乌给全家十来口人吃。每炖一次,他都如临大敌一般,先在内心里积攒着足够的勇气和蛮力,并不动声色地于暗中做着各种准备。假如我没有猜错的话,在这一难熬的过程当中,全家人被一屋子毒翻在地的可怕局面,肯定说不止一次地在他的意识里反复出现过,尽管他是那样地不愿意往这方面想。
终于到了这一天。
褚表耶天麻麻亮就起来,在火塘里烧燃火,支好三脚铁架,坐上砂锅,将川乌草乌,估计还有别的什么药物,加巴掌大四四方方一块刀头肉,放进砂锅里,掺上水,然后,他就寸步不离地守在火塘边,开始炖。
这里头有两个关键。其一是,火塘里同时得坐一把茶壶,烧一壶开水,以便随时补充砂锅里炖蚀下去的汤。也就是说,砂锅里的汤炖蚀下去了不能补充生水、冷水,只能补充滚水。其二是,这整个炖的过程当中,不能“闪火”。意思是,一旦烧开,砂锅里自始至终必须保持滚沸状态。故而砂锅下面,必须保证及时添柴,万不能让火小下去或者时大时小。褚表耶之所以寸步不离,守的就是这两点。柴是他头天就备好的,全是一尺来长、凳腿粗细的老松木块子柴,足量、整齐地码在火塘边上。为了炖这一砂锅药,褚表耶让馆子歇业一天。在这一天里,褚表耶脾气极好,耐心极佳,一脸的和颜悦色,跟生意不好时一脸的愁容和焦躁判若两人,看上去像极了产后的表婶,安静又宁谧(表婶在会东曾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小冬,意思是既生于冬天又生在会东,只可惜在后来的全国性大饥馑中被饿死了)。
总之,在这一天里,褚表耶就心无旁骛地守着那砂锅。经佑那砂锅,既不让我们靠近,他本人更须臾也不离开。我现在特别能理解褚表耶在这一天里的好脾气。我甚至能回想起褚表耶在这一天里的悲悯目光。
他当然相信自己是炖川乌草乌方面的老手。但是,万一,万一有个闪失呢?毕竟,这太冒险了,稍有不慎,便万劫不复。
现在回想起来,街坊上的人是何其惊讶又羡慕这一大家十来口人平平安安,从不生病,且都知道得益于吃川乌草乌。然而,没有哪个人家敢冒这个险也赌上一把,他们宁肯瞅住褚表耶炖川乌草乌这天晚上,死皮赖脸地守在我家堂屋里,天南地北没话找话地海吹,或者搜肠刮肚用尽种种伎俩跟褚表耶套近乎,目的就是守得半碗汤喝。上隔壁的徐老奶奶没好意思来家里守,却早早地在后门口朝我表婶说,哪怕涮砂锅的水能让她喝一碗,也好。
然而,褚表耶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铁石心肠。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褚表耶在处理别的事情时一向大方又得体,很得街坊上各色人等的敬重,唯独在这件事情上不近人情。不是褚表耶悭吝,实在是因为人命关天。你要守,守就是,他不会撵你。他甚至可以兴致勃勃地听你瞎吹,陪你神侃,直至深夜。
砂锅里的川乌草乌早已炖好,火塘里早就不再添柴,红红的火炭在暗淡下去,并一层层变为淡而无味的疏松的灰粉。
夜,在深下去。定定的油灯下面,大的小的,我们一个二个困得东倒西歪,却不敢去睡,褚表耶拿眼角瞅着我们,允许我们趴在桌上或者歪在什么地方打盹,但不允许谁离开,必须要喝了药才准去睡。这是褚表耶的规矩。褚表耶年年炖药,便形成了这规矩。
褚表耶巨大的身躯就舒服地仰躺在火塘边的靠椅上。褚表耶谈笑自如,客人说什么他丝毫也不显出来不耐烦。但客人不走,他不会去揭那砂锅。这个时候,尽管客人们仍在有一搭没一搭地搜牙巴缝缝找话说,事实上已经守不下去了。
歇业时分能到我家堂屋里来闲坐的,皆街坊上有点头脸的人物,要不就是个什么挂角亲戚。眼见得守碗汤喝的奢望难以实现,只好悻悻然打算抽身,却又不便站起来一拍屁股就走。
,
终于有人夸张地伸一个懒腰,且大大地挤出个哈欠又一拍大腿说,嗨!咋就这一大晚上了呢?
于是尽皆一拍大腿,且嗨了一声,站起身来,老大不甘地相跟着出了门。
我们一个个睡眼朦胧,看着一下子空出来许多的屋子,大的忙着顺椅凳,小的则一缩脖颈,感觉那苦药晃然吃进了嘴里一般,脸也皱成了一砣。
首先是表婶将一把长柄大铁勺递到褚表耶手里,然后转身去灶房里抱来一大摞碗,当然还有筷子,放在大八仙桌上,再用帕子,逐一地将碗底上残存的水气擦干。
这步骤非常重要,吃川乌草乌不能沾生水,之前之后的一天里都不能沾,连褚表耶手里的大铁勺,伸入砂锅前也须在火上正反两面烘烤一番。
备好碗筷,褚表耶开始舀药汁,一人一碗,表婶则给我们发冰糖,一人一块,捏在手心里,待喝完药后“过嘴”。
药汁乌黑,浓稠,面上漂着亮亮一层油。
其实,一年一次,我辈已训练出喝药的自觉和技巧。药肯定得喝,赖不脱的,便无人去赖;而喝的要诀是,等那药冷热适中时,埋下头,闭住气,不松口,不呼吸,不换嘴,更不咀嚼地,一口气,将它喝下去!
紧接着将手中冰糖一下塞进嘴里。
毕竟馋肉,在大人的一再鼓励下,也曾试试探探地动过筷子,夹肉吃,却因为实在苦得没法,而浅尝辄止,而后悔不迭。事实上,那肉差不多已经不能叫肉,它被炖得太绒、太烂,似有若无,而只剩点纤维状的丝丝了。而大人,居然不怕苦,不仅敢吃那肉,更敢于嚼那些叉八五爪的药根根。这一点尤其令人佩服。
那药到底有好苦?
只说一点:吃药三天后偶尔伸舌头出来舔嘴唇,尤苦得不行!
说来不好意思,我们那时的卫生习惯实在太成问题。脸当然每天都洗,牙却是只有褚表耶一人在刷。而当年家乡小镇上的原住民,知道每天需要把牙齿刷一遍的人,几乎没有。褚表耶属外来者,且来自繁华的“会理州”,自是不同一般。褚表耶刷牙还颇为讲究,非“白玉”牌牙膏不用,什么“黑人牙膏”、“固齿龄”、“坚尔齿”一概不予考虑。褚表耶洗漱的次序是,先洗脸,再刷牙,刷过牙还要用一块指头长、筷头宽的专用篾片使劲刮舌苔,刮完舌苔,才从这大半盆洗脸水加漱口水中捞出事先温在里面的一个生鸡蛋来,将大头于盆沿上轻轻一磕,用指甲抠出一小孔,既而举到嘴上,并异常惬意又享受地仰脖吸下肚去。褚表耶是全家人的衣食保障,老老小小全家人的心都是褚表耶一个人在操。他是家中太阳,照耀会理会东两个家。褚表耶的健康顶顶要紧。我们虽不懂事,却能够把褚表耶的这一点点特殊享受视为全家人的幸福之源。可惜后来,公私合营,倏忽间褚表耶成了县城经济食堂一名月薪二十元的小伙计,紧跟着便是全民大饥荒,鸡飞蛋打中,褚表耶的这一点点享受,也戛然而止了……
扯远了,仍回到川乌草乌上来。不过关于川乌草乌的话题也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只是记得,有一次,某街坊就炖川乌草乌方面的程序和诸种忌讳、讲究向褚表耶请教。那街坊问得很详细,褚表耶讲得很认真。
到了最后,褚表耶问:你炖川乌草乌的砂锅,盖不盖盖子?
街坊说没盖。
褚表耶立即身子后仰,大显惊讶。并且反复强调,要盖,必须要盖。要不,老房子天棚上的尘灰掉到里面,就吃不成了,就只有连砂锅一起扔掉了。
褚表耶强调这一点时很注意措辞。他绕山转水说半天,也不会去触动那两个不吉利的字、词:“毒”和“闹人”,尽管他需要明确指出,一旦有尘灰掉进砂锅里去,那整锅药就恢复了毒性,就会闹人。他只是一再地且明白无误地说,这样一来,那药就不能吃了,就只能毫不痛惜地倒掉了。由此可以看出,命悬一线中,人们对“毒”和“闹”这两个字,是何等地心存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