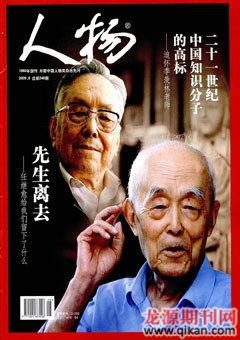说爱莲者
周和平
诗人画家写景状物都是有所寓意的。陆放翁痴情于梅,总想着化身亿千:一枝梅前一放翁。当年徐文长画葡萄,题款就泄露了他的心情:“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心中的怨愤和无奈,让一挂挂丰硕的果实抹上了凄凉的色彩。板桥写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于竹影摇动中写出的是一腔赤诚。及至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黄胄的驴,都让这些不谙世事的动物担起了作者的向往和追求。人物最重传神,即使画山绣水,或青山妩媚,或秋山不老,或寂寞沙洲,许多的技巧只是写出作者心中的丘壑,人生悲欢都付与了远山近水、花影渺渺中。
萧平
别署平之、戈父。室名爱莲居。1942年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江苏扬州。1963年毕业于江苏省国画院。曾任书画鉴定之职于南京博物院19年,1981年调江苏省国画院。合书法、国画、鉴赏、史论、收藏于一体。
40多年的创作、研究、实践,在诸多方面均有不凡的造诣和建树。作品不拘一格,借古开今,清新放逸。1983年以来,多次应邀赴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地讲学、考察,出席国际艺术史高层论坛,发表论文和见解。在国内外举办个人书画展16次,参加各类联展60余次,作品被故宫博物院等国内外10多家博物馆收藏。出版有《萧平书画集》、《笔墨春秋——萧平书画集》、 墨缘——萧平书画集》、《爱莲——萧平六十华诞画荷精品集》、《萧平书法集》、《中国水墨——萧平卷》、《当代中国山水画坛十名家——萧平作品》、《山水画传统技法解析》、《人物画传统技法解析》、《花鸟画传统技法解析》、《龚贤研究》、《倪云林研究》、《娄东画派》、《陈淳》、《龚贤》、《中国画》、《鉴识傅抱石》等书画册和专著。参与编著的书有:《中华文物鉴赏》、《珍宝鉴别指南》、《六朝艺术》,《国宝大典》等。现任江苏省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兼任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资源美术学院、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教授,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美术馆鉴定顾问、南京博物院鉴定顾问、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名誉会长、龚贤纪念馆名誉馆长、江苏省海外联谊会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江苏省政协书画室副主任、江苏省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

萧平爱莲,虽未成癖,却也痴迷。在他40岁时,将清溪路上的画室朝华馆改成了爱莲居,可见他心中是藏着对莲的敬意和向往的。在经过了20年后,他说道:“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成了我的偶像。淡于功利,不倚不傍,唯真善美是求。”直白的宣言中有着高妙的境界。
因此,当他不疾不徐地在宣纸上濡出第一片荷叶时,他便在精神上完成了与这花中君子的契合。后来,当他一次次举办展览、出版图集并广受好评时,他显然已经远离“十莲九俗”的陷阱,莲花于他,已经具有图腾般的意义。
他作过多幅“爱莲居”图:一方池塘,荷叶田田,几架茅舍,绿树匝地,鸡豕逐食,小犬嬉戏,主人或读书,或招饮,或鼓琴,或偕友赏画,清风徐来,香远溢清。他为之题日:余无斯庐,而心中常存之也。对于厌倦了俗世纷扰的士人,有如此境界,岂不快哉?
萧平画荷,或工或写,皆见精神。但我独爱他的写意:横涂竖抹,呼风唤雨,痛快淋漓。他是喜欢青藤、白阳、八大、石涛一路的,这些不遇文人身上所沁出的萧瑟心绪和不愧不怍的姿态,应该是比技巧更能影响他的。他曾宣称更爱秋风中的池荷:“荷叶斑驳破损,在风中飒飒作响”。我想,其中折射的是凝重的心路历程。
夏赏新荷,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之妙;秋得佳实,有“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之趣。萧平的荷花并不尽是文人墨客的清玩,而倒常常成为他以亲和步人民间的写照。在他的散文名篇《爱莲》中,既表达了对莲花高尚的气节、缠绵的情意的倾慕,也注意到了莲藕是清补的食品,甘嫩可口,叶及莲心可入药,更联想到了在莲乡金湖见到的“被尘灰拂面的莲,堆积如山的藕”,感叹这“紧紧维系着老百姓的生活”。这也正应了周公敦颐的“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意思,让人感到了一股透明的纯净。
“莲之爱,同予者何人?”不知萧平愿问否?

1961年8月的一天,萧平走进了位于总统府的江苏省国画院。这天,阳光明媚而有些哺懒,让萧平的心头多了些温暖。在这个非常的岁月里,没能进入大学校门而成为国画院的学员,他心中是欣欣然的:能向享有盛誉的老师学习自己钟爱的书画艺术,这是多么难得啊!想到这些,外表冷峻的萧平的眉头出现了少有的舒展之色。
上世纪60年代的江苏美术界,正是热闹的时候,以傅抱石为代表的一批画家,以“时代变了,笔墨也要变”为宣言,壮行二万三千里,完成了“新金陵派”崛起的最后蜕变。每个大师都是一部传奇:傅抱石用他潇洒淋漓的笔墨,将“抽象和具体完美结合”(黄永玉语);钱松岩以其写实的新题材,用颤笔为绚丽婉约的江南山水开辟了新境界;亚明则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胆魄和出色艺术家的恣肆,引领着“新金陵画派”的崛起;宋文治、魏紫熙、余彤甫、张晋……新时代、新生活、新题材、新笔法,映照着画史上一个新的流派的诞生。
与大师为友为伴,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幸运,也是人生一次奢侈的盛筵。多少年后,躬逢其盛的萧平,不管是在研究新金陵画派的著述中,还是静夜追忆、友人絮语中,都透出对大师们的崇敬和对逝去岁月的怀念。
虽然只是短暂的两年光景,但给了萧平非同一般的人生意义。他不仅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并以之为终身的职业,更在于他从老艺术家身上汲取的营养,他们对国画艺术深邃的认识、开放的姿态、相互间的砥砺和宽容,时至今日,仍然在精神上导引和愉悦着他。
从省国画院出来,萧平走进了南京博物馆。这是他的恩师亚明先生推荐的。这座有着深深庭院的安静院落,依稀残存着不愿离去的昨日风景。走进去的萧平是一个带着探询目光的俊秀青年,19年后走出来时,已经成为了一个经历了许多人生况味,同时有着诸如知名鉴定家、书画家头衔的中年人。
在寂寥而又飘着旧时书香的库房里,在徐法秋先生等前辈指引下,萧平走进了中国书画千百年的长长隧道。一卷卷书画珍品,隐藏着古人的身世和故事,名字是念叨过千百遍的,今天见到许多真迹,矜持的萧平内心奔涌着难以自制的激情。
鉴赏之学,是最为无际无涯的学问。“作画难,而识画尤难”
(龚贤语)。中国书画由于自身的特点,加上战火兵燹之灾不绝,记载著录不全,少有流传有序之作。所以,如何借得一双慧眼,穿透世事风云,剥去层层迷幛,鉴古今,识真假,还其本来面目,历来被视为畏途。学问是鉴赏的基础,作品的时代风格、个人风格如何,题款、印章、纸绢、题跋、著录、装裱,样样都见学问,这一切又都在变化之中。画家书家以千万计,要能鉴能识,又谈何容易?萧平认为,这实在是难以取巧的,一日熟悉。多看真迹原作,则如晤老
友,面貌亲切,有欢笑矣。二日研究。抓住主要流派及代表者,读书研究,久之,则成挚友畏友也。三日实践。古人有“鉴者不画”之说,萧平不以为然。他认为,要在创作中体味古人笔墨功夫,见识高下。所以,在南博开头三年,他便临摹原作近百件。
当然,在南博,萧平收获的也不仅是艺术上的硕果,做学问也不全是寂寞的。随着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美丽的江南女子邹正玉的出现,他的单调生活中又多了红袖添香的雅趣。及至后来,邹正玉爱上青花瓷鉴定并有所成就时,有作家将其二人誉为“水墨青花两相和”。
日积月累,厚积薄发,及至一个新时代到来时,萧平蕴藉于胸的才华喷涌而出。
在当今画坛,萧平是以其广博和精深闻名的。他精于鉴赏,长于史论,而又善书法,其画作涵盖山水花鸟人物,书法也诸体皆备,这也许应该看做一道难得的文化风景吧!
萧平的画,都是能窥其本源的。除了傅抱石、亚明等金陵前辈所给予他的直接影响,他的山水远溯宋元,近接明清,尤其注重王蒙、石涛、龚贤、董其昌诸家。王蒙的“苍”、石涛的“润”,让他的山水丰润中含洒脱,深远中透灵动。他人物笔法中汲取了梁楷、罗两峰的画风,墨色淋漓,取神为上。花鸟画中,他有工有写,既有如“万类霜天竞自由”这样的鸿幅巨制,更多的是八大、吴昌硕的影子,而他们则是萧平崇敬和效法的。萧平的书法是有家学传承的,筑基于汉隶和孙过庭书谱,又取黄山谷及今人高二适、林散之等笔意,自成一格。

这种师法先人的行迹,正是萧平的优势所在。“真迹鉴千卷,英光罗一胸”(吴白语)。这是其他画家少有的经历和机缘,难得的是他走了进去,又走了出来,没有因袭师古不化的老套。他曾以石涛语录:“万点恶墨,恼杀米癫;几丝柔痕,笑倒北苑”,批评当下那种皮相之作。他是将师古人和师造化结合,抒写自己的心灵性情。他对大自然充满敬畏和热爱。“我见青山多妩媚”,面对名山巨川,他常常神思飞跃,视接千载:想着沧海桑田的变化,想着古今名贤的形状,想着这山、这峰、这石,该用王蒙的“牛毛皴”,抑或是石涛的“渴笔”,还是龚贤的积墨法……?这光、这色、这景,又可以从凡·高、莫奈中做哪些借鉴呢?种种想法,杂糅着、纠缠着、撞击着,创新的火花也就进发了。这种古人与今人、国画与西画、心灵与自然的结合,让他进入了一个化境。
早在50年代,还在南师附中上学的萧平就接触了后期印象派的作品印本,并为之目眩神迷,以至80年代他在国外看到许多真迹时,感到的是亲切而不是陌生。他认为,印象派、后期印象派与中国画的意象艺术是相通的,其本身就受到中国画的些许启示。某次,徐邦达先生曾购得王原祁去世前两年画的作品,当时就惊呼:这是中国的点彩派。所以,中西艺术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他的代表作《乐山大佛》,造型上借鉴了西画的透视法,使之更具立体,突出了形象的庄严。在用光上,采用侧逆光;在用色上,使了泼彩。《早春之泸沽湖》,以褚黄为主基调,明亮而温暖,让人想起凡·高、莫奈笔下的19世纪的欧洲乡村。《丽江金水寨》则明显受到米勒《拾穗者》的启示,洋溢着人性的浑厚与神圣,但细细看,这些画从点、线、皴到笔法气韵全是中国画的。近年来,他画得最多的荷花,在构图和用色上也明显汲取了后期印象派的技法,尤其随着丙烯的加入,色彩更加明快灿烂,令人耳目一新。
在具象和抽象之间行走的意象艺术,是中国画的一大表征,也与后期印象派线条粗犷、形式夸张的特点有合。意象的实现得力于它的书写性。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种类,在传统文人中,它是作为必备的要素出现的。萧平的汉简和行草,存在于稚拙和灵动之间,古人有言“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这是将绘画与书法的相通相融作为文人画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作为一名书法名家,萧平对书法艺术主观写意的特点是有充分把握,并自如地体现于绘画中:表现静穆凝重,多用汉简、隶书,而大写意则参入草书、行书笔意。正是运用了书法的体势结构以及用笔用墨或徐或疾、或枯或润的表现形式,使自己的心灵能得到更多的表现和阐释。
这些年来,萧平创作了一批有着强烈地域性和扎实写实功底的作品,显示了他不凡的创新能力。在这组以新疆、云南、甘肃为对象的系列中,他畅快地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城市旅行者对西域淳朴自然风光的新奇和惊喜,这甚至是被俘虏和被征服。作为观赏者和画者,“凝神遐想,妙悟自然”后是拿起勤奋而倔强的画笔,调动起几乎所有的艺术积累,包括自少年而始的多种尝试,作为对大自然馈赠的报答,我们几乎难以界定这些热烈而安静的画面的构建所在:题材的新颖、造型的准确、色彩光影的多变、笔法的松秀,都与其以往的作品有极大差别,然而中国画书写性特色依然鲜明夺目,这种形式上的巨大反差,是萧平作为一个优秀艺术家所具有的超越他人超越自己的特质,而其内在的大统一,则显示民族文化已成为他的魂魄之不可夺也。也正是因为心中激荡着无可遏制的创造激情,才使他的笔端不断开出艺术新花。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们见到的萧平,大多时候是举止得体,一派儒雅,这正是长期传统文化的浸润使其具有“文人之素养,文人之识见”的结果。但他内心,是有他的世界的,不遇与不平,不合与不屑,使他不自觉地流露出矜持和孤傲,许多时候还有常人不易理解或觉察的孤独。
这种孤独是具有文化意识的一种境界,也能成为催化艺术激情的力量。他所具有的学养,让他充满理性的思辨和开阔的视野,他用精神的高贵来实现对凡俗的超越,让自己不羁的艺术翅膀自由翱翔。于是,他心地澄澈,心中盛满了艺术创造的快乐。
他用他的笔在创造着美,用他的心在守护和延续民族文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多元带来了观念的多元,仅以国画论,“穷途末路论”、“废纸论”到“笔墨等于零”等等,萧平都是关注的。有时候他会出奇的愤怒,指斥种种的无知和狂妄,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冷静的,用艺术的规律和艺术的语言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有时,儒雅的萧平也会直抒胸臆,大胆直言,某次在政协讲到纪念吕凤子的意义时,激动处更哽咽失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多年来,萧平在文化传承责任感催逼下所做的点点滴滴,见证了他的赤子之心。
萧平在努力构筑着他的美学理想,书写着自然之美、人性之美、意象之美,追求清新俊逸而不失大气的艺术风格。在他的国画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寄寓着他所追求的深邃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直接意义在于:要将国画从简单的图式中解放出来,而赋予其“写我心、悦性情、传神韵”的国画特质。他在研究石涛、倪云林、袭杼、八大、青藤、白阳时,是在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交合中,在社会变革和文化嬗变的背景下,去熟悉和发现他们的意
义。他画的历史文化名人,如张大千、齐白石、鲁迅,均以工笔写之,神态之酷肖,神情之生动,令人叹为观止。如无精神的敬畏和向往,如无精神的相通相接,何来如此摄人心魄的绝妙手笔?
萧平的史论,尤其是他写的大量的序跋,文史结合,文笔优美,堪称美文,不管是老一辈的吕凤子、傅抱石、陶白、亚明、宋文治,还是同辈的小石、玉麟、伯乐、唐滔,每一篇都是笔力沉雄而又文采飞扬。作文于他,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每一篇都是苦心经营,字斟句酌。他的成功在于他有着深厚的史学、美学和文学功底,更在于他在构思时独出机杼,他是将写人和写艺结合起来,写活了人物,也写活了艺术。他力避一些艰涩生硬的术语和故弄玄虚的概念,让读者从优美的文字中领略传主的美丽人生和美的艺术。萧平在文章中显露的才情,使他更容易找到艺术上的知音。
挚爱着传统文化的萧平,是开放以后较早将书画艺术在海外传播的人。1983年,他即应邀赴美讲学,以后,他十几次前往欧美、日本、新加坡、港澳讲学展览。作为一位优秀的文化使者,他往往受到不同寻常的欢迎。他作为一位鉴赏家的背景和中西文化交融的素养,使彼此间更容易沟通交流,而他展出或示范的书法和绘画,更是直观地传递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妙。
萧平以及其他文化精英是有理由过上精致优雅的生活的,但作为一位有人文思想和悲悯情怀的艺术家,萧平对处于弱势和困厄的群体所表现出的爱心,是常人难以企及的。1998年夏季的大洪灾中,萧平忧心如焚,曾作诗记之:“眼中江如带,心为楚水忧,拙艺堪挥洒,风雨共一舟”。他精心创作了10幅书画作品并将拍卖所得3,7万元悉数捐赠。近年,他为家乡扬州聋哑学校(他是名誉校长)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的事。也许正因为这样,作为名流的萧平被爱和友谊包围着,也享受着爱和友谊的温馨。他,累并快乐着。
2000年9月的一个夜晚,我与萧平有过一次长谈,地点在香港中环附近的一个小酒馆。
三四个小时之前,萧平刚刚经历了一次生死之劫。在游览维多利亚港湾上岸时,由于组织者的粗疏,没将船固定住。在萧平上岸时,船被海浪托起,致使他一脚踩空,掉人海中。不会游泳的萧平夹在游船和码头中间,旁边还有在水下急速旋转的螺旋桨……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萧平,沉浸在回忆之中。我知道,刚刚离去的劫难,触动了他心中最为柔软的部分。他讲起了贤惠的妻子,一双聪慧的儿女,但讲得最多的是自己已经去世的父母。
萧平的父亲是一位文化人,他爱好文学,尤其喜爱鲁迅。他热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往往是父亲写字,萧平拉纸,看父亲笔走龙蛇,心中升腾起对艺术的爱好。自小生活在一种文化的气息和氛围里,文化素养就是这样传承下来。
小酒馆暖暖的灯光和安静的气氛是适宜怀旧的。那一刻,萧平讲起了自己的艺术之路,提到了自己的恩师,这自然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他提得最多的是亚明和徐邦达。他说,亚明当时要他去南博,他心里并不乐意,在经历了许多以后,才真正明白了老师的苦心。某次他去苏州东山看亚明,看到先生不顾高龄爬上爬下创作巨幅壁画,一刹那,他深深地感到老师是为艺术而生的!
徐邦达,于萧平不仅仅是知遇之恩,还有他的学识、他身上保留着的传统文人的气息,都曾强烈地影响着萧平。他说,先生大家风范,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某年,在浙江博物馆鉴赏古画,徐老只肯从差的看起。旁人不明白,徐老说,等“老太爷”来再看,众人不解,第二天,萧平急匆匆赶到,徐老笑指:“老太爷”来了,众人莞尔……
香港之夜转瞬已经过去了6年。这期间,我们多次谈及这次遇险,只是在事件的解构上,危险的因子越来越小,基调也已经从沉郁到带点浪漫甚至还有些调侃,这其实也是大家所冀望的:让记忆成为一次精神的涅磐。
是的,“曾经沧海”的萧平,正用他从容而优美的姿态,在他的艺术天空飞翔。艺术之于他,早已超越了职业的成分,成为了他生命中的主要意义。他创造艺术,艺术也创造了他。艺术照亮了他的人生之路,使他的生命更加丰厚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