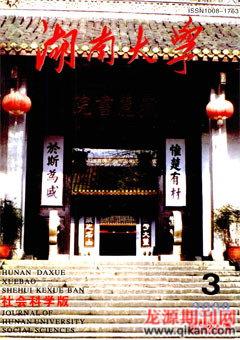论廖平1880年并未转向今文经学
吴仰湘
[摘要]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学思两变,自称第二变是“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学术界据此认为廖平自1880年开始,在王意意闿运影响下,厌弃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但细检相关史料后发现,研究者推证廖平学思二变的契机发自王闿运入主尊经讲席的证据虚空不实。廖平从1881年至1886年间一直从事文字训诂之业,并且始终强调“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真正意蕴,是主张跳出琐碎的名物考订,着力推寻经书条例、解证经典大义,由勤学变为深思会悟,但他的经学立场和治经方法并无明显变化,直到经学二变后才一度转向今文经学。廖平治学在庚辰以后得入新境,既要归功于他对专治小学训诂弊端的自省,又是他不喜记诵、长于悟思的个体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刚到尊经书院的王闿运没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廖平;王闿运;古文经学;今文经学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12009)03—0043—05
关于廖平入读尊经书院后为学与思想的变化,他本人追述说:“予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丙子,从事训诂文字之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滑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于此一变矣。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子》、《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研究者大多以此为据,评析廖平经学初变以前数年间治学与思想的变化。关于从笃嗜“唐宋人文”、用心宋学,到“博览考据诸书”、转治汉学的转变,廖平也有回忆说:“丙子科试时,未见《说文》,正场题‘狂字。余文用‘狮犬之义,得第一,乃购《说文》读之。逾四五日复试,题‘不以文害辞,注云‘文作《说文》之‘文解。乃摭拾《说文》、《诗》句为之,大蒙矜赏,牌调尊经书院。文不足言,特由此得专心古学,其功有不可没者。”廖平因应试偶用《说文》而大获学政张之洞赏识,由此得以调入尊经书院,开始究心文字训诂之业。廖平“聪明心思”的第一变及其变因,恰如廖氏自陈,殆无疑义。备受关注的是廖平“心思聪明”的“又一变”。关于此次转变的契机、内容及对廖平日后学术生涯的影响等,学界虽屡有论及,但仍有重加探讨的必要。
迄今为止,学界对廖平早年学思演变所作的探讨,当推黄开国先生的研究和分析最为详尽。他先后发表过《廖平经学第一变的思想准备》(1985)、《王闿运与廖平的经学——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重要一环》(1989)、《廖平经学六变的变因》(1989)、《廖平早年思想变化及其对经学六变的意义》(1993)等论文。《廖平评传》(1993)第一章第二、三节也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综观上述论著,黄先生关于廖平早年思想第二次转变的要点有二:其一,廖平从博览考据转为专求大义的契机与变因来自王闿运。黄先生始终认为,“治《公羊春秋》,喜言公羊微言大义”的王闿运来主尊经讲席,引起书院学风的极大变化,“这个变化反映在廖平身上,是从博览考据转入专求大义。1879年,廖平经常向王闿运请教到深夜。在王的影响下,他开始钻研《公羊春秋》”。在另一个地方,黄先生更明确地说:“王闿运执教后,廖平勤于请业。他在老师的今文经学影响下,感到名物训诂的破碎,遂改而信从专讲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经学初程》说:‘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从此,廖平的经学就沿着今文经学的方向发展了。”其二,廖平此次思想转变的实质,是否定文字训诂的汉学,接受今文经学,探寻微言大义。对廖平所谓“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云云,黄先生作了如下诠释:“廖平又受公羊学者王闿运之教,感到文字训诂只是经学的枝叶和糟粕,今文经学讲的微言大义才是经学的根本和精华,转而笃信今文经学,从而又深入地研讨了汉代的今文经学。”黄先生进而提出,廖平在厌弃考据后,有一个“专求大义的时期”,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是“以探索《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持论大体相同的还有不少人,例如陈其泰先生就认为,廖平“专事求大义”后阐发今文经学是受老师王闿运的影响,并论证说:“王闿运来蜀前一年,刚刚完成《公羊春秋笺》初稿,以后又在光绪九年、十年从事改定工作。故在主讲书院期间,《春秋公羊传》正是他头脑中的兴奋点。这就直接影响了廖平。据《年谱》记载,是时廖平与好友张祥龄均有志于《公羊春秋》,常就王闿运请业,每至深夜。”台湾的陈文豪先生也曾根据同样的资料,得出相同的结论。此外,赵伯雄先生在论及廖平时,也说王闿运在尊经书院提倡今文经学,使廖平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廖平自述‘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就是向今文经学的方向转化。此后他的思想虽屡有变化,但基本上没有超越今文经学的范围”。
事实上,在经学上兼采今、古的王闿运,在入川之前,并未专门研治《公羊》微言大义之学,主讲尊经书院期间,也没有专以今文经学诱启院生。所以,廖平因王氏入主尊经讲席而厌弃考据、转而专求大义并走向今文之学的说法,很有必要再作检验。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此加以辨析。
首先,检视研究者所凭借的论据,不过是《廖季平年谱》光绪五年条下所言二事:一是根据《湘绮楼日记》,谓“是时先生与张祥龄均有志于《公羊春秋》。先生初见王闿运,王询知有志习《春秋》”;二是“三月一日,与张祥龄迁入内院,常就王闿运请业,每至深夜”。按《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二月十七日记:“廖生登庭来,久坐,有志习《公羊春秋》,然拙于言,未知其学如何。”细绎此处文字,可知王氏入尊经后尚未施教,而廖平第一次来见即表示“有志习《公羊春秋》”,则廖平对于《公羊春秋》的兴趣,有可能是蓄志已久,这当然与王氏入主尊经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廖平一时心血来潮,藉以投师门所好,引起王氏对自己的重视。但因廖平“拙于言”,虽久坐而王氏“未知其学如何”,当然无法就研习《公羊春秋》一事给予廖平任何指导。《廖季平年谱》记载他第二年起专治《毂梁春秋》,直到光绪十年始以余力撰成《公羊何氏解诂十论》,可见王、廖的第一次见面对于廖平走向今文经学的影响,实是微乎其微。又《湘绮楼日记》三月三日说:“张、廖二生于朔日已移入内院,同话诗文,至亥正散。”《廖季平年谱》三月一日条下所云迁入内院及请业至夜深,与王氏此处日记所载正相契合,“至亥正散”自属深夜,但师生所谈并非今文之学或公羊大义,而是“同话诗文”。但有论者竟把《廖季平年谱》所载请业至深夜,转述成廖平“常就王闿运问《公羊》义,每至夜深”,实属失考。可见,研究者援引《廖季平年谱》所载两事,推证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契机发自王闿运的入主尊经讲席,证据如此虚空,立说当然不稳。另《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有曰:“终日为诸生讲说,多
发明《公羊春秋》之义例。张生子绂、廖生旭陔皆有志于《春秋》。子绂云欲移入院,并要张生监荪同来。此邦人欣欣向学,可喜也。”这条记载表面上较前述两条似乎更能说明王闿运在尊经书院宣讲公羊之学,却未见研究者引用。但细究王闿运所发明的“《公羊春秋》之义例”,多指《公羊传》中的书法条例,与何休以来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并不是一回事,虽间及“张三世”之说,却很少发挥“通三统”、“素王改制”等微言大义,与常州公羊学派不可相提并论。
其次,对于廖平所说“庚辰以后,厌弃破碎”,研究者大多解读成廖平从1880年开始厌弃文字训诂之学,批判乃至否定汉学考据,事实是否如此呢?根据《廖季平年谱》和其它相关资料,廖平在庚辰(1880年)以后有以下数事值得注意:1881年,作《释字小笺》,讨论《说文》中的虚字问题,“尽取《说文》虚字而求其本义,均作实字解,将近二三百字”,后来还准备将其补缀成书,一为《六书说》,二为《四书分类》,三为《绪论》;又应尊经院课,“考酒齐所用,题最繁难,精思旬日,大得条理”,王闿运阅卷后大加称赏,“以为勾心斗角,考出祭主仪节,足补《礼经》之阙”;同时著《转注说》,“旬月专精,五花八门,头头是道”。1881至1882年,“与华阳赵浚(孔昭)以小学相切磋”。1885年,为同学范熔《篆书说文》作跋。1886年,成《六书旧义》一卷,两年后由尊经书局刊刻行世。《六书旧义》是廖平入读尊经书院以来小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他在自序中回忆研治《说文》之学的历程,说:“予丙子为《说文》之学者数月,后遂泛滥无专功。辛巳冬,作《转注假借考》,颇与时论不同。丙戌春间,乃知形、事之分,援因旧稿,补为此编。”显然,廖平虽称“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但从1881年至1886年间,他自1876以来一直大力从事的文字训诂和汉学考据之业,不仅没有中断,相反日益有成。根据现有资料,廖平对小学训诂的批评,是在1883年,他在会试后赴太原谒见张之洞,张以“风疾马良相诫,并以治小学相勖”;廖平意不苟同,“欲作《语上篇》,以矫时流株守小学之弊”。另1896年廖平编撰《经话甲篇》时,存录同窗好友张祥龄责斥小学末流的一段话,指责“末流之弊,小学未通,年已衰晚,叩其经义,茫乎未闻”,并加注说:“此为株守小学者发,切中时弊,故取之。癸丑在晋阳,欲作《语上篇》以矫其弊,匆匆未暇。此编所言,颇多曩旨。”考察廖平1881至1886年间的小学研究,再寻绎“叩其经义,茫乎未闻”的沉痛之言,可知廖平斥责的“破碎支离,最为大害”,原是鉴于考据末流毕生株守小学、未能发明经义的弊端,要求以小学之功钻研经书义蕴,并非否定汉学考据。事实上,廖平1886年编撰《经学初程》指示治学途径时,相当重视小学,指出“小学为经学梯航”,强调“夫治经之道,不能离声音、训诂,学虽二名,实本一事”,并盛赞《说文》“为古学之渊海,最为有用,其有功古学,不在贾、马之下”。1896年编撰的《经话甲篇》,仍告诫士子说:“不通音训,罔识古义,非也。”廖平对待小学的真实态度,是“经学自小学始,不当以小学止”,视文字训诂、名物考订为通经之具,藉以探索、发明经书大义。不明了这一点,就会误解廖平“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本意。
第三,对于廖平所谓的“专事求大义”,论者认为他在1880年以后的数年间,专门探索《春秋》的微言大义。然而细加考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廖平自述说“庚辰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子》、《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可知他是因为考据书中缺乏精深之义,遂弃置不再殚精研读,但取而代之的并非蕴含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典,而是《庄》、《管》、《列》、《墨》等诸子论著;从“喜其义实”一语中,也可窥知廖平此时接受“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可能性应该极小。揆诸当时的情形,廖平此时的厌弃破碎、探求大义,实是察觉到沉迷于小学训诂的弊病,以为“若沉浸其中,则终身以小道自域,殊嫌狭隘”,因而跳出琐碎的名物考订,着力探索经典中蕴含的书例、义理或整体上的大义要旨,舍枝叶而图其根本,弃糟粕而撷其精华,寻求“大道”,由先前的学而少思变为深思会悟。这是廖平治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的开始,因此自称“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心思聪明”一语正可见此次转变的实质是指治学精神与为学方法。事实上,《经学初程》原文在叙述“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说:“初学看考据书,当以自验。倘未变移性情,其功犹甚浅也。”这句话未被《廖季平年谱》转引,也未见有研究者引用,其实对于正确理解廖平叙述早年的学思两变极为关键。将廖平所述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可见他此处述说自己读书治学的变化和进步,乃是现身说法,启示学子应由小学人手治经,但不能终止于琐碎的考据,应进而“变移性情”,寻求大道。
考察廖平1880年以后的治学实践,可见他治经喜欢推寻条例、解证大义,以及先撰诸经凡例再作经书研究。这些正是廖平“专事求大义”的具体呈现。1881年他始注《毂梁传》,即从其遗说中“间就传例推比解之”。1883年他在赴京应试的舟车劳顿中,曾“冥心潜索,得素王、二伯诸大义”。1884年他明确提出“三传之学,唯求内理,不务旁攻”,强调《春秋》三传研究重在寻求各自的“内理”,以求其会通,不能纠缠于枝叶细节而彼此攻击。当年所成《起起穀梁废疾》、《释范》,正是通过“条例”何、郑、范三家之说,各加纠匡。1885年编定的《穀梁春秋内外编目录》中,就有《穀梁大义考证》、《穀梁传例疏证》两种。1884至1886年间相继完成的《公羊何氏解诂三十论》,同样不专执于何休注解的繁文碎义,而是高屋建瓴,总括大纲,论述《公羊》学的要义大旨,如“主素王不王鲁论”、“曲存时事论”、“《王制》为《春秋》旧传礼论”等,均属精深之论。最为突出的事例,是他忽视经传文字少数细节性的差异,从《穀梁》、《王制》的研读中寻出“古与古同,今与今同”的规律,对数千年纠纷难解的今、古文经学从礼制上加以判分。《今古学考》曾追述其因探求大义而豁然开悟的情形:“乙酉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觳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钞《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为晚年说,弟子多主此义,推以遍说群经。汉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说,乃定《王制》为今学之祖。”其中所谓“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就是舍弃枝叶,寻获今、古异制的根本,再执之“推以遍说群经”,使纷乱纠杂的
今、古两家从此门户瞭然可睹。
论者还以为,廖平在“专求大义”时期通过先后研究《穀梁》、《公羊》,找到了借助发挥微言大义以建立其理论的今文经学形式,形成了以“素王改制”说为核心的尊孔崇经观念,因此“对廖平后来的经学发展起着决定基本方向的作用”。但事实是,廖平在其经学一变之前,无论研讨《穀梁》、《公羊》,还是评析何休《公羊解诂》,虽一再论及今文微言大义之学,甚至推证过“素王改制”之说,但其主观目的并非宣扬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他的《公羊解诂三十论》还一再驳斥何休以来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是企图通过对古说遗义的探寻,找到判分今、古家法的客观依据。他这一时期经学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是从《穀梁》、《王制》与《五经异义》的比对中发现“古与古同,今与今同”的奥秘,再执以遍考群经,确立了以《王制》统今学、以《周礼》统古学的平分今、古之论。此外,廖平此时虽有“素王”诸论,但实无尊今黜古的观念,直到经学二变才提出尊今抑古之说。因此,即便承认廖平“专求大义”时期的思想以探索《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也不能将他这一时期探索微言大义的行为,与他经学二变时期及其以后利用这些微言大义宣扬尊今抑古、尊孔崇经相提并论。廖平经学一变、二变时期的经学立场判然两异,他本人对此有过清楚的说明,例如《知圣续编》自序称“初用东汉旧法,作《今古学考》”,《四益馆经学四变记》中的廖平自序也说:“初以《王制》、《周礼》同洽中国,分周、孔同异,袭用东汉法也。继以《周礼》与《王制》不两立,归狱刘歆,用西汉法。”另光绪《井研志》所收《今古学提要》,也说廖平“于乙酉用东汉许、郑法为此编”。既然廖平经学一变所用为“东汉旧法”、“许、郑法”,直到经学二变才用“西汉法”,那么他在所谓“专事求大义”时期的经学立场和治学方法,已是不言自喻。研究者指称廖平1880年就由汉学考据转向今文经学或公羊之学,显然与史实有违。
还应指出的是,廖平庚辰以后渐弃破碎大道之学,“专事求大义”,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学思境界,其实是他早年以来不喜记诵、独擅悟思的回返与发展。他曾回忆说:“予素无记性,幼读五经未终,而皆不能记诵。每读生书,必以己意串讲一过,然后能记。……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不以记诵为事。心既通其理,则文字皆可弃。”通解其理意而文字皆可弃,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正如出一辙。廖平日后还将此法教示给尊经书院的士子,《经学初程》开篇即指出:
经学须耐烦苦思,方能有得。若资性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则但能略窥门户,不能深入妙境。
经学要有内心,看考据书,一见能解,非解人心也。必须沉静思索,推比考订,自然心中贯通。若徒口头记诵,道听涂说,小遇盘错,即便败绩。惟心知其意,则百变不穷。前人云读书贵沉思,不贵敏悟,信哉!
廖平赞同前贤所说读书贵沉思而不贵敏悟,正可见他教人学思并重,由学致思,才能登堂入室,渐臻妙境。《经话甲编》卷一开篇所立治经规条,第一条“戒不得本原,务循支派”,也是这种主张,他说:
凡经皆有大纲巨领,为其本根,而后支流余裔,因缘而生。立说须得大主脑,探骊得珠,以下迎刃而解。如不得要领,纵极寻枝节,终归无用。今之治经者,多沿细碎,不寻根原,所以破碎支离,少所成就。
舍枝叶而取其本原,略琐碎而寻其纲领,廖平在治经大有所成后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之谈,实是“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的最佳注解。
因此,廖平所说的“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并非治学对象、经学立场的转移,如同研究者所称从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而是他学力日进后为学精神、治学方法的提升。他不再沉潜于经书中具体、细碎的名物考订,由先前“泛滥于声音训诂”的勤学,变成“专事求大义”的重思,通过苦思冥索,每多创获神解。而廖平治学在庚辰以后得入新境,既要归功于他对专治小学训诂弊端的自我反省,又是他求学以来不喜记诵、长于悟思的个体特性自然发展的结果,与初到尊经书院的王闿运实无直接关系。不过有趣的是,廖平的这一次变化,在时间上与王闿运入主尊经书院恰好合拍,后人遂将二者牵扯到一起,误以为王闿运在尊经书院宣讲今文经学而直接促成了廖平的厌弃考据、改习今文。
[参考文献]
[1]黄开国.廖平经学第一变的思想准备[J].重庆师院学报,1985,(3):93.
[2]黄开国,王闿运与廖平的经学——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重要一环[J].船山学报,1989,(2).
[3]陈德述.廖平学术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18.
[4]黄开国.廖平经学六变的变因[J].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2):108.
[5]陈其泰.清代公羊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273.
[6]陈文豪.廖平经学思想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19.
[7]赵伯雄.春秋学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740.
[8]廖幼平.廖季平年谱[M].
[9]王闿运.湘绮楼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7.
[10]廖平.经话甲编(卷一)[A].李耀仙.廖平选集(上册)[C].成都:巴蜀书社,1998.
[11]廖平,吴之英.经学初程[M].
[12]廖平.穀梁古义疏·序[M]
[13]黄开国.廖平早年思想变化及其对经学六变的意义[J].天府新论,1993,(5):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