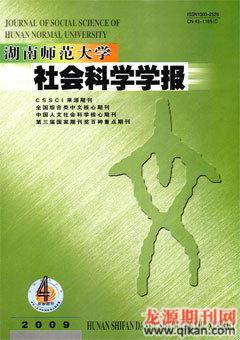论儒家自我调节及其内在机制
赵彩花
摘要:儒家有丰富的自我调节理论和实践,具体体现在个体一生对行为、情绪、事业进退和人我关系等的调节,儒家自我调节内在机制可从认知和目标层面子以分析,认知层面上,儒家通过修正认知方式和树立认知源以调节;目标层面上,儒家以每天检查反思目标施行和用终极目标来指导实践,从而使人从认知、行为上超越困境,达到不忧、不惧和无怨的境界,成为身心和谐、人我和谐、天人和谐的个体。
关键词:儒家;自我调节;认知;目标,和谐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4-0017-05
人生多难,仕途多舛,充满逆境。提倡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儒家,面对诸多的人生遭遇与仕途逆境,凭借何方进行自我调节?其自我调节的内在机制如何?这是本文要着力探讨的主要论题。
自我调节,指的是“个人努力去化解逆境、去阻止它的主观影响、或者去适应逆境带来的新的生活情境,这些就是应对的本质——也是心理调节的本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逆境无处不在,自我调节也随时在起作用。同时,自我调节具有文化属性,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自我调节方法及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中国文化中儒家具有浓郁的人世情怀又常不得其位,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乐观应对中包含丰富的自我调节理论和实践,其“修齐治平”的基石“正心”即调节心理状态:“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宋代学者程颐更明白指出:“学本是治心。”研究儒家自我调节及内在调节机制既可丰富自我调节理论,更可以直接为当今塑造健全人格和建立和谐社会提供参考,可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儒家自我调节的具体表现
儒家“治心”并不是通过玄思冥想,而是“要做得心主定,惟是止于事”,通过“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的实践,考察并体验万事万物的原理,从而使心如明镜,毫无“忿嚏”、“恐惧”、“好乐”、“忧息”等闭塞滞碍之病。下面我们从不同的生活情境来具体剖析儒家如何调节自我。
1,不同年龄阶段爱欲及行为调节
儒家的自我调节具有时段性,根据各个不同的年龄段的生理特点与心理机制,采用不同的调节方法。孔子把人生分为三个阶段:少年、壮年和老年,认为不同年龄段上的自我调节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其自身的气血各异所致,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年少之时,气血日渐旺盛,身体各方面都在成长变化,内心的爱欲日渐增多增强,而个人的意志力却跟不上身体的成长,所以这一时期需要警觉不要沉溺于各种爱好欲望之中;中年之时,血气充盈,精力旺盛,个人的品质、毅力都已经成熟,此时容易走极端的爱好是自恃力气,与人争斗;老年之时,由于气血衰弱,戒斗已不成为问题,但随着年龄增长,老人容易出现因经验丰富而自得,只相信自己的经验而不能以开放的心态体会和接受新事物。所以要在不同生理时期,警惕容易蹈袭的弱点,进行合理的自我调节,从而顺利度过不同的人生阶段。
孔子所论是针对普遍人性而言,宋代程颐谈论自己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特点及养生调节,于此可以管窥儒家个体的自我调节方法:
先生(程颐)谓张绎曰:“吾受气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后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于盛年无损也。”绎因请曰:“先生受气之薄而厚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为深耻。”
宋代理学家认为“在天日命,在人日性”,“气便是命”,便是性,人的寿命长短在于最初禀得之气性,“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赢窳”,程颐所谓“受气甚薄”也就是初禀之气不丰厚,先天身体素质不强壮,直到30岁气血才开始变盛,到40至50岁才筋强骨健。与张绎谈话之时,程颐已经72岁高龄,仍然体健身轻,与四五十岁时没有区别。程颐认为他以菲薄的初禀之气却能到老年仍然身体强壮,原因是他一直颐养天和,精神专一,不放纵爱欲,而以“忘生徇欲”为深戒:“某气本不盛,然而能不病、无倦怠者,只是一个慎,生不恣意,其于外事,思虑尽皆悠悠。”
儒家的自我调节,往往因各个时段而异,不同时段,采用不同的自我调节方法。孔子着眼于谆谆告诫世人要警惕不同人生阶段容易沉溺的偏嗜,而程颐则以自己的践行从正面立论,两者实质都在强调人整个一生要调节和控制好自己的爱欲和行为,不能让它伤生害性。
2,一生情绪的自我调节
人的情绪,最容易因外界的刺激与干扰而波动,因而最需要自我调节。儒家经典对人的情绪的表达,使用频率最高的分别是“乐”、“忧”、“耻”、“怨”。儒者追求的情绪以否定式表达是“不忧”、“不惑”、“不惧”、“无怨”,以肯定式陈述即“乐”及“有耻”。快乐可分为感官满足之乐和精神快乐,孔子批评世俗追求“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的感官快乐,认为它使人无所用心,对成德进业有损害。儒家之“乐”,孔子认为是“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孟子认为是“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孔孟表述不同,实质都是乐善乐道,以仁义礼智信为宗旨和目的实践和行为,才是儒家“乐”的发源和归宿处,终身依仁蹈义,所以有终身之乐。儒家特别强调自我调节,需要保持“乐”的情绪,因为情绪如“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乐道”,行道,才是个人心理幸福感的源泉,才是真正长久地被履践和体悟。
但是在求道乐善的漫长过程中,人们还有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负性情绪来动摇和浸蚀“乐”,其中主要的负性情绪是“忧”、“怨”、“耻”、“惧”。儒家反复提到如何对待“耻”、“忧”和“怨”。就一般人情而言,“贫而无怨难”,但君子面对贫困,要以目的来调节自己,“求仁得仁,亦何怨”,君子以求仁为目的,达到了目的就乐在其中,至于物质、名誉并非所求,所以没有这些也应该心安理得,毫无怨言。儒家对各种情绪的调节,程颢有言:“怨只是一个怨,但其用处不同。舜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学须是通,不得如此执泥。如言‘仁者不忧,又却言‘作《易》者其有忧患,须要知用处各别也。天下只有一个忧字,一个怨字。既有此二字;圣人安得无之?……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君子与常人一样,每天要面对忧怨疑惧,不同处在于他以“道”为提契,恰当的调节好情绪,从而能做到常“乐”而无忧无怨并“行己有耻”。
情绪表达并不是孤立的行为,它的展示规则包含着个
人目标和社会认可标准。纵观儒家经典所使用的情绪表达词,“怒”、“喜”、“好”、“哀”、“戚”、“悲”与君子成德的帮助或阻碍关联不大,所以儒家对它们的关注和叙述不多;“乐”、“忧”、“耻”、“怨”、“惧”这些正性或负性的情绪与个体成德密切相关,所以儒家格外注意调节这类情绪,并反复强调君子要保持“乐”、“不忧”、“无怨”和“有耻”。
3,一生事业进退的自我调节
儒家之所谓事业,包括于内的自身修为和于外的外在事功。人生无常,进退难料。儒家要求人们在事业进退之中加强自我调节。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对个人一生修身进德事业的极好总结。孔子对自我人生的总结概括,不啻是一种人生模式,而程颐又指出:年少时“须激昂自进”,努力进取,中年以后,循序渐进至于“自至成德”,“事方可自安”。他着重标识“自进”、“自成”、“白安”,在成德过程中的主体性与主动自求的重要性。
儒家认为外在的事功是个体对社会及君王之“义”,“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内在修为和外在为社会服务的事功,是生命个体终身不懈的事业,而儒家自我调节一生事业进退穷达的总方针,乃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兼济天下不能实现时,儒家在“穷”中安顿自我的具体调节方法首先是调整对“爵禄”的认识:“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个体体行仁义忠信即是“天爵”,“人爵”应该因“天爵”而来,不应当为“人爵”背弃“天爵”,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既使不能为世所用,行“天爵”的个体也能“内省不疚”,知道不是自己的过错,从而安之若素,心理能平衡和畅。另外,即使不能为统治者所用,个体修身行道,能和睦邻居朋友,醇美远近风俗,影响一乡人乃至于一国人,这种影响力实际就是俸禄。当子张向孔子问“干禄”时,孔子回答“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当他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的时候,孔子回答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行为能给社会以好的影响,这就是“为政”,所以君子在道不能行,无法通过仕途造福天下的时候,既要安之若素,同时又要积极修身行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无能也”。君子在进退穷达之际,以“道”为最高境界,修身以乐“道”,而不是乐“物”,始终与道同在,与义谐行,在道义中安顿自我。
4,人我关系的自我调节
儒家着眼于宗法制度与宗法文化,把人我关系分为五类:“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陈寅恪总结说:“中国文化之要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就是“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儒家对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的交往原则和调节方法各有阐述,个体待人的总原则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遇事要责己以严,待人以宽。具体分方法是“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换位思考,身体力行,要求对方做到的事情,先自己亲身实践,这样就能在与人关系中不苛责他人,同时又能亲善力仁,提升自我道德境界,以“正己”与“无怨”为原则来调节自己,因而当孔子遇到公孙寮的谗言,孟子遭到臧仓氏的诋毁,孔子称之为“命”,孟子归之于“天”,不怨天,不尤人,反思自身,假如反省而“内心不疚”,则泰然处之。
同时,儒家把人分为两类,一君子,二小人。要求君子与人相处,注重君子之交,以心换心,以诚相待,以仁义为本。还要积极认识自我优长,以保持积极心态。比如对方以富贵权势骄人时,孟子提供的调节方法是:“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驰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不要被对方的物质富有所吓倒,而要看到这些享乐并不是己之所求,自己的追求是对方所无法达到的,这样,“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以慊之哉”,从而调整好自我,更加坚定求道之心。
二、儒家式自我调节机制
纵观儒家自我调节的具体表现,可知其自我调节模式及其机制特征。那么,儒家何以能够有效地实现自我调节?究其原因固然很复杂,下面我们只从认知和目标两个层面来分析儒家自我调节的工作机制。
1,认知层面:儒家善于改变不合理的认知方式和树立认知源
正名孔子曾以“必也正名乎”为治国之要事,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心理学角度看,“正名”有着异乎寻常的正确性。孔子反复表达“恶紫之乱朱”,“恶乡愿”,原因是紫色似朱红而实非,乡愿似君子而实相反,它们的存在淆乱了人的认知,最后导致“言不顺”而“事不成”,所以要去掉或认清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使事物名实相符,各归其所;另外,由于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为救时代之失,孔子对许多名物予以新的内涵,它使人在认知上皈依仁礼,如上文已经提及的对“爵禄”的阐释。这种例证还有很多,如子张问“达”,并认为遐迩闻名就是“达”的表征,孔子予以纠正,指出“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才是真正的“在邦必达,在家必达”,通过指出“闻”、“达”的不同内质,使听者改正观念,从而为正确行动提供了保证。再如孔子在陈蔡之间受困,断粮七日,子贡问孔子这样是否就是“穷”,孔子纠正道:“是何言也?君子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指出“穷”的内涵是不得道,而不是物质贫穷。以这种方式,孔子赋予了“孝”、“仁”、“为政”、“君子”、“友”等牵涉到生活各方面的词语以新的内涵,从而厘清了概念,认识上的澄清为以后履道坚定提供了先导条件。孔子反复强调“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三“达德”,其“不忧”“不惑”“不惧”的处理机制即源于在认知层面对那些不正确的认知干扰的认清和排除,从而在心理上和行为上达到“不忧”、“不惧”、“不惑”。
亲逆境的心理态度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君子毕生都将履践和推行仁,任重道远,艰苦可知,所以要认识到艰难困苦是必然之事,从而在艰险到来时,泰然处之。当日孔子困厄陈蔡时,便以历史上挫折造就的人事来厘清弟子的迷惘:“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所以
面临挫折时,更要矢志不渝,激流勇进,挫折常常是成功的前奏,它于人有益。后来孟子用高度概括的话阐述了儒家亲逆境的心理态度:“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腠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挫折是人生提升必经的炼狱,是磨练身心、完美才能的必然途径。明人王阳明曾以自身经历证明了亲逆境的心态能成就“仁”道。他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时,外惧奸臣加害,内存生死之忧,为解除自身忧惧,王阳明造一石棺,日夜端坐其中,思考自古圣贤处逆境何以应对,内心澄清,忽然懂得了格物致知的主旨,平生苦心寻求达到圣人境界的途径在艰难困苦的历练中豁然开朗。正是儒家面对挫折困苦“端然俟命”与随遇而安的心态,成为王阳明绝处逢生且提升认识达到圣人境界的法宝。
法天儒家正名和亲逆境的心理态度都是针对世俗不正确的认知而随事树立,有一定的被动性。其真正具有积极建设意义可以执一以解万的核心认知方法和调节原则是则天,取法自然法则来思考、应对人生社会,正是以此为元认知,儒家自我调节机制才能遇事即解,贯通无碍。天道的特征之一是“于穆不已”,生生不息,永不停止,这是“天之所以为天”的根本原因,效法于此,儒家认为人应该“纯亦不已”,日新其德,永不停步,《周易》表达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反复申言“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都是君子效法天“于穆不已”而形成的进取原则;天行无言之教,万物各得性理,取法于此,孔子向往“我欲无言”,把“不言而教,不行而成”树为最高为人法则;另外,取法天道“四时成焉,万物生焉”的大仁,儒家的人生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天之所以能赞育万物就是因为“诚”,故君子效法于此,也以“诚”为上,“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儒家不但善于以天道的总特征推演君子之道及其细则,而且善于面对天道自然,随机生发,感悟人道当法天之处,从而不断调整自我。如孔子听到儿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告诫弟子:“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日:‘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有人问孟子:“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论及自然美的功利性时说:“对自然美中的功利,就其属性来看,是道德性的。……这一点就作为造化的最终目的指向了我们,指向了我们的‘道德规定。”在儒家阐释的天之特征中,的确把自然的最终目的指向了人类及其“道德规定”,天日新月进,儒家在其中取得永不枯竭的道德理念和行为法则,则天是儒家有效自我调节的源泉活水。
2,目标层面:儒家注重行为目标的崇高性与实际操作性的结合
(1)日三省吾身——每日检验和调整行为目标
如上所述,天既是儒家的认知取法对象,也是其行为的最高目标。儒家又善于把这种大目标分解落实,演变为通过日常的角色担任、人伦关系的演绎来达到。目标宏大高远,而实现目标的途径则非常具体,具有实际操作性、可检验性。
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伦关系中,儒家要求个体必须担任演绎好不同的角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就是马克思所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常常一身兼有数种角色,不管处在哪种关系中,要相应地演绎好角色规定的性质。曾子曾简约给出相处各种人伦关系对自己的要求是:“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每天都要反复以此三事警醒自己。
儒家的日常反省自身,还包括“恕道”,以“恕道”待人。子贡曾经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把这种“恕道”称之为君子的“絮矩之道”,并进一步阐释道:“君子有絮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絮矩之道。”对此,孟子总结道:“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每日以圣贤来激励自己:“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因此终日不敢懈怠。正是通过每日不断检讨自我、调整自我行为,君子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道德日修月进。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说一个人不每天反省自己做得怎么样,应该怎么办,那这个人就无所进益了。惟有对日常具体行为予以检验调整,把它落到实处,那么每天的行为就是践仁、履道和成“德”。可见,“日三省吾身”是儒家日常检验、达成目标的有效调节方法。
(2)下学上达——连通终极目标
宋儒程颐解释“下学而上达”,是“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儒家通过人事的履践来贯彻天道,同时又能从具体人事中自觉向上提升“上达”而至于“道”与“理”,程颐认为如此提升出来的就是“天理”。其实,具体论析,可以发现儒家“上达”分三个向度:个体内在和谐向度,人我关系和谐向度和天人和谐合一向度。这三个向度也是“上达”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第一步是个体修身诚意以达到身心和谐,第二层是身心和谐的个体处理好人我关系,他首先要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身作则,使家庭长幼有序,父慈子爱,孝悌盈门,只有这样,才能去处理好大的人我关系——治国平天下,因为“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把家庭之中的孝悌慈爱扩而大之,则可以治理好国家,造福天下。假如没有机会把德泽推行于天下,君子则孜孜于家庭、邻里、朋友、国人关系处理,“遁世而不闷”。完满地实现了身心和谐、人我关系和谐的个体,其行为实际已达到了天之“生物不倦,生物不测”的品质,万物条畅,各得生理,这样就已达到天人和谐合德。由此可见,儒家的“上达”是分层次的向上提升,但并不是说,第一步完成后便可以弃置不顾了,君子每天都必须反复地践行这两步;即使上达于第三步天人和谐,也不是到此为止了,儒家“下学”与“上达”是无限循环过程,上达于天理,再把天理指导
人事,落实于具体人事之中,既而又在人伦事物中体悟天理,天之“博厚、高明、悠久”,人之“仁、智、勇”在人事中不断展示它新的丰富性,生命就在这种体悟中不断“上达”,故孟子有“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内收则万物在心,外投则全心在物,天理人理终是一理,与天合德的人,万物的生理成性在天地之中,也就在他的心中,他不需外求,只须反身向内,专精诚意,便已与天理同一,这种身心同一、物我同一、天人同一,就是最高的和谐,达到这种和谐的人自然“乐莫大焉”,幸福莫大焉。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18世纪末于《论自在的人的使命》一文中通过理论推理得出一个结论:“人的最终和最高目标是人的完全自相一致”,“一是意志同永远有效的意志的观念相一致,或者叫做伦理的善;一是我们之外的事物同我们的意志(当然指我们的理性意志)相一致,或者叫做幸福。”早在二千多年前,儒家不但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于“人的完全自相一致”,从“上达”中感悟和体验“伦理”和“幸福”。这是怎样一个崇高的境界啊!
当然,达到三大和谐、与万物条畅毕竟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能达到的。儒家“下学而上达”的调节方法对那些不能或还没有达到最高境界者的作用,是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粘滞于眼前苦难,而能以超越的眼光看待困难,端正心态,调整意志。比如孔子弟子司马牛,因“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而忧愁,子夏就能从终极目标来帮助他排解:“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以上达之理来调节指导下学之忧与困惑,从而使下学能无问断进行,这就需要调节。同时,儒家很注重取法自然天道。用以调整下学时的困惑。如见“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感悟并调节君子之学的目的:“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君子“下学”不是以利禄为目的,而是为了“上达”,以求达到“不困”、“不忧”、“不惑”的境界。所以孔子被匡人围困,情势危机,而能客观平静地对待:“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程颐评价这段话是“丧乃我丧,未丧乃我未丧”,认为孔子以圣人气象在表达“我自做着天理”。由于下学上达,又以上达之理来推导事物,故能调节自我,临危不惧。
由此看来,儒家倡导的“下学而上达”,既是实现自我,达到大和谐状态的极好途径,也是儒家在艰难困苦面前从容以对,能够从目标层面上进行自我调节,达到不惧、不惑、不忧的最好方法。当今之世,人们为政为学、为事为业,面对困难与挫折,如果能够效法先秦儒家,予以自我调节,也许会省去许多烦恼,避免许多悲剧,从而达到更高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Lawrence A,Pervin,Oliver p,Jolm,人格手册:理论与研
究(黄希庭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宋]朱熹,四书章旬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宋]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四[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
中华书局1985,
[5][汉]王充,论衡·命义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6]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6,
[7][汉]班固启虎通德论·三纲六纪[M],北京:北京图书
馆出版社,2005,
[8]吕不韦,吕氏春秋·孝行览[M],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
店出版社,1996,
[9]荀子,荀子[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10][联邦德国]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王才勇译)
[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11][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