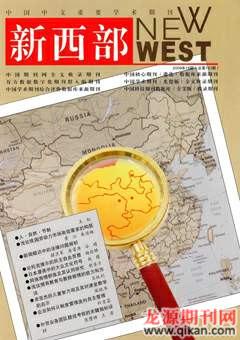柳宗元山水文学美学特点形成原因初探
赵 欣
【摘 要】 柳宗元的山水文学具有凄神寒骨的美学特点。本文就其美学特点的形成原因进行浅析。认为这种美学特点主要根源于柳宗元见弃于国家社会,见弃于时代的极为孤独的悲剧性品格,并且与他超然卓越思想家的见识、文学运动领袖的胸襟以及他自觉的美学追求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 柳宗元;山水文学;美学特点
所谓山水文学,一般指描绘自然景物,注重借景抒情。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直到晋宋以后才普遍发达起来,主要以诗歌和散文为主。柳宗元的山水文学更多的具有儒家的思想色彩,这区别于更多的受佛、道思想影响的山水文学。如:陶渊明笔下的“鸟弄欢新节,冷风送馀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日冥》)。孟浩然的“白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以上几位大家的山水文学,更多的是自我自觉的追求,他们心中的山水文学,是“无往而不美”。但是柳宗元走向山水,是获罪远迁,他笔下的山水无不烙印着作者强烈而沉郁的情感。柳宗元眼中的山水,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那些遭人遗弃,不被发现,不被赏识的山山水水,被作者以沉重、内敛的笔调,骨峭和淡泊简古的风格构造成为一种独特的凄神寒骨的美学特点。这种美学特点主要根源于柳宗元见弃于国家社会,见弃于故园,见弃于时代的极为孤独的悲剧性品格,并且与他超然卓越的思想家的见识,文学运动领袖的胸襟,以及他自觉的美学追求是分不开的。
柳宗元二十一岁考取进士,从而开始逐渐接近权利中心。他在任监察御史里行期间,和王叔文、韦执谊、刘禹锡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且对朝政的黑暗腐败有更深入的了解,从而逐步孕育了他要求改革朝政的愿望。贞元二十一年,太子李诵称帝,力图摆脱对宦官和豪族大官僚的依附,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柳宗元和他们政见一致,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从而开始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政治革新。这次政治革新被认为是“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跋扈之强藩。”因而这个还未站稳脚跟的革新集团,在做了六个月的皇帝李诵被赶下台后,便也立刻遭到宦官、豪族大官僚对他们继踵而至的政治迫害:王叔文第二年被杀,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十一月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十年后复贬为柳州刺史。永州那时极为荒僻,离长安和柳宗元的家乡有数千里之遥。这时的柳宗元,一方面继续遭受政敌们的人身攻击,老相识都不敢和他交往,文坛好友韩愈也指责他的这次革新行为。另一方面,他的妻子已逝,随行老母不久丧亡,所住之处连遭火灾。他写下大量的山水诗歌及著名的“永州八记”,以寄托自己的情怀。如柳宗元倾诉身遭贬谪的幽愤的诗:“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风露繁。”(《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以及描写他贬谪生涯中身心苦痛的诗“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还有描写他对故乡深深眷恋的诗“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登柳州峨山》)以上柳宗元描写山水的诗歌,不论何种情绪,在用词上都偏重于“孤”、“惊”、“独”,总是给人以凄冷峭厉之感。宋人蔡启说:“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蔡宽夫诗话》)而且这种情绪在散文中也是挥之不去的,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极富代表性的一篇。其中作者在描写了“如鸣佩环”的潭水,形状各异的岩石和怡然嬉戏的游鱼之后继续写到“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面对“心乐之”的胜景,作者不能恣情于山水风光。他内心极度的苦闷与寂寞孤愤在暂时得到释放与缓解之后,便又侵入其骨髓。又如柳诗《南涧中题》中“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诗人将自己的凄怆感受投射在美好的景色上,营造出一个侵人肌骨的清冷诗境。苏轼曾评价“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绝妙古今矣”。因为柳宗元对人生态度的积极执着,决定了他不能象王维那样,在自然山水中达到时世两忘,万念皆寂。柳宗元在永州听说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叛乱被平定后,还抑制不住内心的欣慰,写了《剑门铭》以“铭功鉴乱。”但可悲的是,柳宗元纵然一腔热情也只能在万里之遥,以文字来书写自己的理想了。因而柳宗元的这种悲剧性品格使他对山水的选择有独特的视点,山水之于自然如同人之与社会也有遭受公平与不公平的差别。所以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描写经过艰苦的探寻,才发现和达到的西山是“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以自况。并且柳宗元在“八记”的最后一篇《小石城山记》中更加明白的抒发自己的这种感情。作者先写小石城山令人赞叹的奇石景象。“士断而川分,有积石挡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然后作者奇怪这样美好的山川为什么不在中原而被弃置在“夷狄”,实则来譬喻自己的才能不为所用。正如明人茅坤所说柳宗元与“山川两相遭,非子厚之困且久,不能以搜岩穴之奇;非岩穴之怪且幽,亦无以发子厚之文。”(《唐宋八大家文钞•柳柳州文钞》)
所以柳宗元这种虽见弃于国家、故园、时代但仍一腔赤诚,积极用世之志,便是他的悲剧性品格,也正是形成他山水文学“凄神寒骨”的美学特点的主要原因。
他在两次被贬后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便转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继续斗争,广泛钻研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因而可以在山水文学中游刃有余的用运儒、道、佛各家思想。如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写他登临绝顶后畅游时的精神境界:“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的一刹那间精神上的超脱。但是,柳宗元的思想正如他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中提到的是“统合儒释”,其实质是援佛济儒。[1]因而他在不得已寻求精神的暂时解脱后,内心却压抑着儒家对现实理想执着而不能实现的更深的忧愤。[2]元和十年,柳宗元奉诏还京,他怀着怎样忐忑不安和期望的心情,却不料同年三月复贬柳州刺史。“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衡阳与刘梦得分路赠别》)。任是何种山水之美,能不染上作者忧惧而惨然的情感色彩吗?
再者,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柳宗元提倡散文,反对骈文。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一抑一扬,能使文章含蓄而明快;一通一节,能使文章畅通而又变化;一清一重,能使文章清新不俗。柳宗元的这种进步的美学追求,尤为鲜明的体现在他的山水文学中。尤其是卓绝千古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作者表面运用极为浅显的文字和简单的意象勾勒出一幅孤寒索寞的天地和严寒肃杀的环境。而在这简单的文字里却使用“孤”“独”“绝”“灭”来传达一种深深的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不肯低头放弃的执着。文章中愤郁的情感传达的令人难以呼吸。正如苏轼评价“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并且也符合作者“一抑一扬”的美学追求。再如在散文中,《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的水声,非所见,而是“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
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生动传神而又明快清新。表现出行文的曲折变化。写石,有“为坻,为屿,为堪,为岩”有“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钴鉧潭西小丘记》)还有“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阆奥”(《石涧记》),真是描摹细致,刻尽百态,而又清新不俗。但是作者眼中如此美妙的山水,也只能使他愁闷的心绪暂时得以释放。
综上所述,柳宗元体现在山水文学中的“凄神寒骨”的美学特点,是与其悲剧性的品格、与其儒家思想的浸染、与其自觉的美学追求是分不开的。
【注释】
[1] 此观点见:郎宝如先生的.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评价.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
[2] 此观点见:郎宝如先生的.论文学的超越意识与执着精神.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
【参考文献】
[1] 柳宗元集(全四册).中华书局出版,1979.10.1.
[2] 柳宗元简论.吴文治,中华书局,1979.5.1.
[3] 柳宗元传论.孙昌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
[4] 柳宗元选集.徐翠先选注.山系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12.1.
[5]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1.
[6]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王运熙、杨明著.1996.12.1.
[7] 柳宗元资料汇编(上下册).
[8] 论柳宗元山水田园诗对传统精神的扭变.王自周,佳木斯师专学报,1995.1.
[9] 儒家思想与山水文学.郎宝如.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
[10] 论柳宗元山水诗中的悲情.高建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