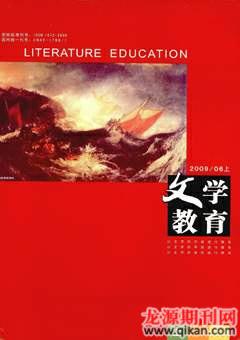《新娘来到黄天镇》的叙事艺术
柴 鲜
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1871-1900)活跃于1890年代的美国文坛,创办《云雀》杂志的吉伯特·伯吉斯在1895年公开评论说:“这位早熟的神童写的几部作品才气大得惊人。”①《新娘来到黄天镇》是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取材于他作为《纽约世界报》记者报道1898年西美战争期间的经历见闻。
小说《新娘来到黄天镇》讲述了美国西南部得克萨斯州一小镇执法官杰克·波特带着已在圣安大略市举行了婚礼的心爱姑娘,返回黄天镇家中的故事。作者采取了非线性的平行虚构叙事手法,将满怀甜蜜幸福的新婚夫妇从车站走回家与酒醉狂躁凶狠的恶徒寻仇至其家的两条线索交错展开,在主人公波特家门口突然相撞,用读者视角外聚焦讲述却又在情节高潮处陡然降落,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空间,令人久久回味,很具有叙事艺术美感。
一.时空上的非线性平行叙事
小说中,故事的发生时间是从吃中午饭前到下午三点四十二分到站下车走回家这段时间里。叙述以普尔曼式车厢内的波特夫妇怀着即将回到家的兴奋、紧张的复杂心情到餐车就餐,看着车窗外景色或交谈来消磨旅途时光到下车回家为一条线索,同时并行发展的是黄天镇上小酒馆内六个男人喝酒聊天的日常生活,突然被跑进的年轻人传来威尔森酒醉的消息打断了平静的生活,客逃人散,酒馆关门躲避,醉汉捣乱不成,侍酒寻仇往波特家,这时与作为正面人物的主人公突然相撞。作为书写叙事的时间,必然是线性的,故事气氛由轻松、愉快的幸福时间逐渐转向舒适、担忧、紧张、恐惧的气氛里,由缓慢向紧张斜向过渡。然而,故事的发生是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里并行发展的,归途中的主人公行进在回家的路上,小镇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场景里,醉汉威尔森既作为一个对抗角色打断了酒馆人们的正常生活空间,为我们展示了故事中隐含的另一生活空间,又作为一个联结角色揭示了小镇生活空间和波特夫妇现存空间的共同性,还是一个线索角色延续了故事的发展,导致了故事高潮的到来。
叙述者用主人公回家这个情节作为明线,以他的行动时间来点明了故事发展的具体时间域,如午饭前12点17分,②到站时间3点42分。这些由手表所提供的精确时间是机械的,相对于小镇人们的时间意识而言,作者是用在强烈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草及头放在爪子上打盹的懒洋洋的狗来表现的,火车站末端靠在斜椅上休闲抽烟的人暗示了小镇人们是以火车停靠站来获知准确时间的。镇上人们的生活时间是模糊原始自然的,叙述通过虚构的巧合,用火车停靠站时间点将主人公与小镇人们放置在了同一时间里,展现出三副生活画面在同一时空的不同位置上的平行发展,但事件本身没有因为人物位置的不同而停滞或孤立,他们在各自的空间里是独自自然发展的。当然,波特夫妇与威尔森突然相撞的那个时间点是情节自然发展的高潮交叉点,是作者安排的一种自然而又必然的虚构时间。
二.印象写实的色彩叙事与想象画面的隐喻
1.印象写实的色彩叙事
写克莱恩传记的作家及评论家贝里曼认为:“克莱恩是个印象派作家,他描写事物的方法,不单只描绘该物给人的印象,同时也据实描述。”③大概受歌德的色彩规则影响,克莱恩十分注意色彩的使用,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在《新娘来到黄天镇》里,画面色彩的运用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从车窗一瞥里闪过的是绿色的草地,暗绿色的牧豆树和仙人掌,嫩绿的树林,紫色迷雾般的斜坡。第一次坐火车旅行的新娘注视到的是饰有小图案花纹的海绿色、亮铜色、银色的车厢,在她眼里车外原野是泛着油层般的亮黑色、青铜色、橄榄绿色和银灰色。沙街上的草皮在酷阳下是鲜亮的绿色,长满牧豆树的大片平原是梅子色的。主人公的脸是红色,手是砖红色,黑色的衣服,新娘却是蓝色的天鹅绒裙子,餐车里黑人服务员的白色制服共同构成了一副写实的生活画面。醉汉威尔森身穿栗色的法兰绒衬衫,镶有金边印记的红色靴子,泛红光的脸,蓝黑色的左轮手枪。爱娃·海勒认为借助色彩可以达到对空间透视的想象,同样,作者用这些鲜艳明亮的色调勾勒出了酷阳下的西部景色及人物的生动形象。
绿色、黄色与红色是小说的主色调。绿色是希望的象征,尤其是在沙漠地带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在文中既反映了当地的自然景观,也暗示了主人公身上所承载的小镇人们对他的深深期望。黄色是一种明亮愉快的色彩,具有生命喜悦的外向色调,是阳光般的色彩。结婚本就蕴涵着生命循环的意味,小镇人们对生活是乐观而热情的。无论尴尬热恋或激动愤怒,人们都会脸红,红色既有生命的燃烧也有仇恨的狂暴,故事里的波特或新娘还是醉汉,不同的脸红表现了人物内心的不同心境与性格,作者在他的印象写实里突出使用了这些力量、灿烂、强烈的色彩。
2.画面想象的隐喻叙事
波特从故事叙述的时间起到遭遇威尔森之前,他的心中一直有两种情绪在激烈斗争着,出于对小镇人们的责任感而引起的自责与愧疚,伴随着带着刚结婚的新娘回家的兴奋与快乐。他知晓自己对于小镇百姓的重要性,想象中人们若知晓他带着新娘的归来会热烈欢庆祝福,欢送他们到砖墙房子门前。从他的想象里,可以觉察到波特内心对生活的激情,表面平淡实则内心热望刺激的矛盾性格,这种内心的矛盾冲突在到站下车时看见站台的冷清中变成了一种潜在的失落,拉着新娘的快步行走只是这种内心想象的英雄激情变成现实里或许被遗忘的失望的一种掩饰。
这种英雄激情的想象出乎意料地被一幕喜剧性的现实遭遇宣泄出来了。夫妇悄悄地溜回家,在家门口没有欢笑与喝彩的意外惊喜,只有一支冰冷的枪口对着波特胸膛。自以为是救人的英雄却反讽地面临被救,他没有被人遗忘,此刻,仇人的双枪正迎接在他家门口。波特心中此时所有的生命激情被激发到了顶点,但他没有机会去如他想象那样展露身手,本令他尴尬自责的带着新娘的已婚事实却挽救了他的生命。
想象画面与现实情景的反讽对比,隐喻了生活的平凡本质,生活现实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美好,也不如他担心的那么糟糕。在生死的关键时刻,一切的发生都那么自然,真正保护了波特生命的不是他自以为是的英雄激情,而是普通人平淡生活的人性。
三.不同声音叙事的转换
波特夫妇在车上愉快而甜蜜的旅行,文中使用了一系列的动词ask,cry,say,answer,tell,explain来描写他们的交谈,波特带着愉快的笑容,脸上闪着兴奋的光芒,一次又一次笑着。酒馆中的人们也在随意闲聊,突然关起门,酒馆内是无声的沉默,自在的高谈阔论变成了谨慎地窃窃私语。小说中前半部分的叙事是以人的声音为主导的,后半部分被射击声和怪物般的狂吼与狗吠取代了。
酒馆中的人们成为一种表面上的缺失,而射击声、狂吼声及缓慢移动的脚步声却暗示了听者的存在,他们的沉默是一种暂时的缺失。醉汉上场了,但他的狂吼怒骂是与狗吠声、枪弹声混杂在一起的,他的“人”表面存在实而缺失。
匆匆行路低声欢笑的波特夫妇突然沉默了,短暂的沉默后人的话语声再次显现。冷静而清楚的回答中,威尔森的声音从那混乱的非人类声音中显露出来,回归到人类话语世界。这种话语的回归也正是威尔森身上狂暴兽性的温情人性的回归,不同声音叙事的转变是小说世界从文明秩序→混乱无序→正常生活的回归。
这三种不同声音的存在,人的话语,动物狂吼,机械射击声,正是现实世界人性、兽性、社会暴力的三种对应存在,人性与暴力的结合是正义,而兽行与暴力结合则是黑暗。作者并没有把这种人性与兽性绝对对立,而是借酒馆中人们之口说出这种暴力与兽性的结合实质,当威尔森醉了时他才是可怕的,当他没醉时,他完全是正常的人。将酒归之为恶的原因当然只是表象化的陈述,而真正要表达的是,人有善恶两面性,没有完全意义的恶人,恶人在常人的世界中也具有普通人的人性光辉。
四.多重变换的叙述视角
克莱恩是个对具有浪漫色彩的骑士豪侠传奇抱有理想化幻想的人,他对生活充满了积极的热情。从他的大多数作品来看,他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总是会时不时忍不住跳进故事里来插几句,那种按捺不住的情感总在真实地感染着读者。
《新娘来到黄天镇》中结合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在客观化的叙述中不乏反语讽刺语气。叙述者用他的视角告诉我们火车越接近黄天镇,这位丈夫表现得越焦躁,时而兴奋激动,时而心不在焉,两种矛盾的情绪在他心中激烈斗争着。新娘对丈夫关怀是处于对焦虑的不知情中,透过波特的眼睛我们看见了这些。遭到枪口威胁时新娘如同旧衣服般腊黄的脸色却是作者让读者站在威尔森的背后看见的。然而,对于威尔森在空街上耍疯的丑态却是通过酒馆里躲在关着门后的人“偷窥”看见的。从不同的眼睛看到不同的景象,也展现了生活空间的丰富多样性。
尤为精彩的是酒馆门口狗与醉汉的视角转换。人们已吓得关门躲在店里,而狗还躺在酒馆门前打盹。这场人狗相逐的场景如同现代电影的反打镜头一样精彩,不过是在狗和醉汉之间。在狗的眼里,人停下来滑稽地举着他的手枪;在人眼里,狗突然出现并嚎叫着,垂着沉闷的头斜跑开去。其实在这里,狗看见的也是叙述者、躲在门后人们及醉汉威尔森和我们读者的视线,而威尔森的视线是叙述者、躲在门后人们及读者的视线。人早已吓得躲起来,也许狗正是因为对这样的闹剧习以为常了,故会在威尔森走到面前时才起身离开,可见狗都懒得理他。狗对醉汉的无理取闹如同困兽般狂吠尖叫,威尔森却仗着挂在臀部的武器而放肆大笑。狗和人的角色在这里已经互换了。
如同摄影机般不停变化的多重视角组成了一幅流动而充满悬念的画面,张驰并行,缓急相间,而结尾的画面定格如现代电影里一个拉的长镜头——他(威尔森)拿起右侧的手枪,将两把武器插进枪套,走了。沙地上留下了他漏斗形的深深脚印。漏斗形的深深脚印将醉汉走路摇摆的样子具体化在我们的眼里了。
尽管《新娘来到黄天镇》是发表于一百多年前的一部短篇小说,但毫无疑问的是,它的叙事手法具有明显的现代电影叙事特色。小说在时空转换、多重视角变化上及视觉与听觉叙事上都表现出作者个人鲜明独特的写作风格,也许正因为这些叙事特色,克莱恩同年发表的另一部中篇小说《蓝色旅馆》才会被改编成电影。可以设想,这位与西奥多·德莱塞同年出生又交好的天才作家斯蒂芬·克莱恩,如果能活的更久一点,也许他将能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留在美国文学史上。
注释:
①一八九O年代的美国∕拉泽尔·齐夫著,夏平、嘉彤、董翔晓译,上海:上海外语教研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
②文中所引英文来自The Bride Comes to Yellow Sky,by Stephen Crane, from An Approach to Fiction, edited Lin Liuchen, Published in 2004 b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ess,Shanghai,P5-17;
③美国小说评论集∕田维新等译,香港-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出版,1985年,第114页。
参考书目:
1.An Approach to Fiction, edited Lin Liuchen, Published in 2004 by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ess, Shanghai。
2.一八九O年代的美国∕拉泽尔·齐夫著,夏平、嘉彤、董翔晓译,上海:上海外语教研出版社,1988年。
3.什么是电影叙事学∕戈得罗,若斯特著,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柴鲜,陕西商洛学院中文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