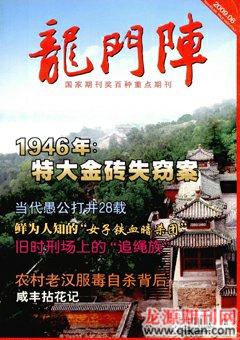亲历国民党军中悲惨事
李亚雄
今年我已76岁,曾在国民党军队中生活近8个月,亲身经历了旧军队黑暗、腐败,以及骇人听闻的事件。
拉 丁
1948年秋,我15岁,因家境贫寒,生活无着,经里人之友宋云鹤先生保荐,在成都市城守东大街安富里12号福隆公司当杂役。我在公司主要工作是早晚扫地,抹桌椅,客来端茶递烟,有时外出为公司送信件和资料,晚上在大门后面用两条板凳和一张木板支铺睡觉。这里吃饭不出钱,一年内无工薪,满年后每月以当时一斗米价作为收入。
1949年5月,国内战局紧张。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鱼贯退进成都。福隆公司受时局的冲击,北路承运已不通行,兼之多头制约,运作无力,业务已成瘫痪之势。公司股东纷纷撤走,职工大部辞去。我也感到生活走到末路,心中一片茫然。
公司一个会计叫陈如璧,善良正直,家住成都金玉街。有一天他把我叫去,对我说:“如今找碗饭吃非常困难。你不如暂时去当兵,先找个栖身之地求得一口饭吃。”
我对当兵本不情愿,可成都举目无亲,回老家一样生活无着,为了一口饭吃,只好走此下策。过了几天,由陈如璧的哥哥陈仲涛先生(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军医)亲笔写了一封信,要我到外北青龙场投军去。
我离开福隆公司,带上陈先生的信向成都北郊而去。约近中午时分,行至石灰街附近,突然后面上来两个军人,一前一后把我拦着。“小兄弟,到哪里去?”站在我前面的人不紧不慢地问我。
“到青龙场去。”我回答着,心中忐忑不安。
“好哇,我们也去青龙场,一路走吧。”
“我又不认识你们,凭什么要和你们一路走。”我虽嘴硬,但语气却是软软的。
“小兄弟,明侃吧,现今国难当头,人人应当兵卫国,今天跟我们走一趟吧。”他拉下了脸一本正经地说。
我一下子明白了,遇到拉壮丁的了。正想分辩,这两个“丘八老兄”不由分说,前拉后推一路搡着我向着田野中小道磕磕绊绊而去。
“慢点不行吗?我也是去当兵的。”我边走边叫着。
“少说话,别给老子来这套,再叫喊就把你捆起来。”走在后面的军人,在背后打了我一掌,恶狠狠地吼道。
我们来到好大的一座院落里,分前后两院,全是木结构青瓦房,前院正中五开间房着实宽敞,左右各三间耳房,大门两侧各有两间配房,正房右边一走道通另一小院落,是炊事班伙房,旁一侧门通后院是主人住宅。竹林树木栽满后院,一后门专供主人出入。前院地坝是三合土地皮,四周房屋内全是土泥砖加竹子搭成的连铺,供士兵住宿。
我被领到院坝中间站着,许多士兵一下子围了上来,争睹刚被拉的“壮丁”是什么模样。一个自称是连长的军官,看了陈先生的信后说:“我叫李世昌,就是你要找的人,这里就是黄家大院子。”我也不明白他说的是真是假,稀里糊涂地留了下来。
我当即被分配到班里,班长叫陈海云,随即又领了一身黄皮(军服),还有草席、被子、背夹,就算是正式入伍了。事后得知,这支部队的番号是新编陆军第95军,军直属辎重团三营八连。
抢 饭
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俗称“吃粮”,依照旧衡制16两为1斤计算,军中士兵每天配额为24两,合现在的1斤半粮食,加上一定的菜金,可以说是足够饱腹的。但旧军队扣粮克饷是司空见惯的事。一天三顿饭几乎千篇一律,早晨一锅稀饭,每个班两三勺胡豆,干炒后用水发胀,加一点盐,在锅内搅拌几下便为主菜。中午晚上吃饭,院坝中一个特大的筲箕盛满了米饭,每班一盆时令菜蔬(萝卜、白菜居多),放点盐和豆豉、辣椒,煮熟了就吃,很少见油珠。每月初二、十六打牙祭时才能吃到肉,但数量甚微。每天三顿饭全连集合在一起(军官另灶),等盛完饭后都站立起来,待值星官检查后,一声令下“开始”,方得进餐。如有先食者,则令你端着一碗饭罚站于队列之外,等众人吃完后,才能吃一碗白眼饭(即只有饭没有菜)。
刚到的几天,我根本吃不饱饭,兼之营养不足,人也日渐消瘦。一天,陈海云班长悄悄地告诉我吃饭的诀窍。于是我便改变了吃饭方式。早晨吃饭,盛好饭时,在回队列的途中,边走边用筷子搅动碗内的稀饭,并不断吹气使之快速降温。吃饭时碗不停地转动,稀饭边吃边冷却。俗话说:“走稀路要跑,吃稀饭要搅。”午餐和晚餐时,第一碗饭少盛一点,开饭口令一下,快速吃完碗里的饭。盛第二碗饭时,将碗往筲箕饭堆中扣下去,用力按住旋转,让碗里的饭压得又紧又多。如果能抢住了饭木瓢更好,可以使劲将碗中的饭按紧。归队时不吃饭,集中精力吃菜,菜吃完了再吃第二碗饭。总之,在这里吃饭不能按常规进行,人人都各显神通,连队中私下流传着一句怪话:吃饭胜过上战场,肚儿不饱×他娘。
割 股
国民党军队中缺医少药,营连一级不配医疗设备,当官的都不管士兵的卫生健康。军医一般都不下连队,士兵体质很差,生虱者较普遍。有的士兵生疮长疥,吸食鸦片,有的在外估吃霸赊,拈花惹草,弄得一身恶疮,奇臭难闻。
有一个姓张的老兵,40岁左右,身体很壮实,但臀部长了一个硬块,比鸡蛋还大,肿得老高,四周呈白色,显然已经化脓了。据班长说长的是“痈疖子”,属于一种恶性毒疮。张姓老兵整天趴在床上,坐不能坐,躺不能躺,痛苦不堪。到了深夜,毒疮跳脓,痛得他叫爹喊娘,闹得整个黄家大院都不得安宁。一次,班长掐了掐他的臀部,说:“是时候了,动手吧。”准备给他开刀。
这天,吃过早饭,全连出操完毕,班长叫了几个士兵,找来一条又宽又结实的长木凳,把张姓士兵裤子脱了下来,将其抬至长板凳上趴着。两人拉住手,一人按着头,一人按住腿,一人端了一盆从后院井中打来的冷水,一人抱了厚厚的一捆草纸。班长右手拿了一把锋利锃亮的匕首,在一盏油灯上烘烤了一阵算是消毒,他对姓张的士兵说:“兄弟,对不住啦,忍着点吧。”说完后班长喝一大口冷水含在口中,左手拇指和食指叉开成八字形,在痈疮四周轻轻转动抚摸。刚开始抚摸时,这个士兵痛得一边大声叫唤,一边直扭动身躯,肌肉不停战抖,头上直冒汗水,但被几个人死死地按住不准摆动。说也奇怪,少顷他便不动了,似觉很舒服,任由班长抚摸。就在这时,班长把刀轻轻地、慢慢地靠近痈疮,突然一口冷水“呼”地喷向臀部,这个士兵受此一惊,臀部抽筋似地突然向上一翘。就在这一瞬间,班长的匕首“哧”的一声飞快割下去,在痈疮上开了一个口子。只听“啊哟”一声惨叫,姓张的士兵脑袋一搭就昏了过去,臀部的酽脓和污血立即冒了出来。班长再用双手在四周挤压,脓血流了士兵一身,一凳,一地,也流满了班长一双手。拿草纸的人不停地一张又一张为其擦拭。班长又用双手掰开伤口,端盆的人便用冷水向着伤口冲刷。慢慢地,酽脓污血没有了,开始流出鲜红的血,两边能看到肌肉了。班长从另一人手中接过一大包事先采摘并捣碎的草药“野炎草”猛地按在伤口上,稍停一两分钟,见伤口不往外渗血了,才将草纸盖上,又用绑腿布捆好。一场惊心动魄的“外科手术”就此结束。
在场士兵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大气不敢出。事后听陈海云说,张姓士兵为这次手术支付了一个月的薪水。
活埋
国民党军中黑暗、腐败、欺诈,纪律涣散,人所共知,打士兵、搞体罚是家常便饭,黑吃黑的事屡见不鲜。在连队里,连长就是“太上皇”,有生杀大权。谁要是惹了他,就有猫抓蓑衣脱不了爪爪的危险,我刚到连队不久,就目睹了活埋士兵的事。
我班一壁之隔的一间小屋,是连队的禁闭室,内中关押着一名戴脚镣手铐的北方大汉,姓赵,30多岁,已经关押了一个月。其人个子高大,十分彪悍,很有一股蛮劲,没有文化,也没有家室,经常提劲打靶,赌博嫖娼,连队被他打过的士兵不在少数。听别的士兵讲,一天晚上睡觉,他似觉枕下有响动,揭开席子一看,一条长蛇盘在下面。蛇受了惊扰,“呼”的一下蹿了起来,向北方汉子袭击。赵姓大汉“啊”地大叫一声,眼疾手快,伸手便抓住了蛇的七寸,另一手抓住蛇身,往自己的手臂上缠绕,然后两手用力一扯,活活将蛇扯成两节。大汉发疯似地拿着两节滴血的蛇身,放入口中不停地喝血,观者无不倒抽冷气。他究竟犯了什么事被关押,大家都不得而知,连里也从未公布过。我私下向班长打听,班长马起脸严肃地说:“当兵的,一定要规规矩矩,做一个聋子、哑子、瞎子,遇事不要随便听,随便说,随便看,否则会有大祸的。”吓得我再也不敢打听。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天空下着密密细雨,连队早早地吹了熄灯号,人们已进入梦乡。大约午夜2时左右,我在睡梦中似乎听见有杂乱的脚步声。我从被窝中偷偷探出头来,从板壁缝中往外窥探,只见连长李世昌指挥着二排长带了几个人,肩挎枪支,手握镐铲出了黄家大院。副连长腰别手枪站在院子中间,另有十几个士兵荷枪实弹地站在四周的屋檐下,监视着大院里的动静,一带队的班长在四处走动查看。大约1小时后,外面的几个人回来了,在几支手电筒的晃动下,奔向禁闭室。只听“起来”一声低吼,随即屋内传出了脚镣手铐的撞击声,拳打脚踢的“叭叭”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可能是北方大汉知道今夜难逃厄运,拼命地挣扎。由于他人高马大,兼有几分蛮劲,几个人一时难以将其制服,挤在房中撕扯摔打。摔打中不时传出北方汉子撕心裂肺的绝望喊叫,“连长啊,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干了”,“连长啊,我的爹啊,你行行好吧,饶了我吧。弟兄们啊……”
慢慢地,喊叫声变成了瓮声瓮气的闷叫,可能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了嘴。接着又听“咚”的一声,似一人用重物击中了北方大汉的头部,他重重地倒在地上,禁闭室内再也没有挣扎声和喊叫声了。
“拖出去!”李连长低沉地命令道。
房门开处,手电晃动,两人拉着北方汉子的手,两人托着腰,像拉死狗似地拖出了黄家大院。大院内一片寂静,只有那个带队班长的身影,幽灵似地在院坝中来回晃动。又过了大约1小时,人们回来了,警戒也撤了。我又悄无声息地钻入被窝,似乎今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夜,好静!唯一能听见的是打在瓦房上淅淅沥沥的雨声和我在被窝内瑟瑟的战抖声。那个赵姓北方大汉从此冤死异乡,不知能否魂归故里?
断腿
这年9月初,连队移住沙河场,驻一农家院内,紧靠公路边。当时,每支部队都有“拉丁”任务,按军官们的说法是“形势紧迫,补足兵员”。
有农民王姓叔侄二人,叔父60岁左右,侄子20出头,外出路过沙河场,双双被“拉丁”进了我所在的连队,编入班排,连里安排有专人监视他们,以防其逃跑。
一日黄昏,那个侄儿去后院上厕所,见四下无人,顾不上解手,迅速脱下军装搭在后院竹竿上就翻墙跑了出去。直到有人解手,发现了脱下的军装,才上报给连里。李连长下令紧急集合,各班查人,方知是那侄儿逃跑了。于是不由分说先将其叔捆绑起来,再派人四处追捕。入夜后,那侄儿被抓了回来,吊在院中树上,叔父绑在另一棵树上。
连长命人用皮带先对其叔侄一顿暴打,接着又拳脚相加,打得当叔叔的哭爹喊娘,一个劲大喊饶命,埋怨其侄害他受罪。其侄被打得口鼻流血,除了大声喊叫外,一句也不求饶。连长要他们交代如何密谋策划逃跑之事,其叔大呼冤枉,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要跑啊!我们不在一个班排,哪有机会密谋策划呀!老天爷作证!连长,你行行善,把我们放下来吧,我担保再也不跑了。”
将其叔放下后,连长转问其侄是否还逃跑,其侄不应。李连长恼羞成怒,命打手用一条扁担,照其头部、背部、腿部猛打一阵。其侄开始还叫喊,后来就叫不出声了,活活被打昏过去。其叔一旁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大哭不止,大喊饶命,直至昏厥。连长命人放下时,其侄已不能站立。事后检查,其侄浑身都是伤,一脚踝骨被打折,已成残疾。连长只好另设一地铺,让他们叔侄同住,由其叔护理。
李连长要借整治逃兵杀鸡给猴看,达到“镇堂子”目的,哪知弄巧成拙,连队又无医生,部队也不愿花钱治疗。两天后,连长便叫叔侄二人脱下军装,雇了一辆鸡公车,将二人捆在车上,令其离开连队。王姓叔侄带着一身屈辱,饱含一腔怨恨,在“吱呀,吱呀”的鸡公车哀鸣声中,离开了农家大院,消失在大路的远方。
(压题图:《三百六十行大观》,谢颖绘)
(责编何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