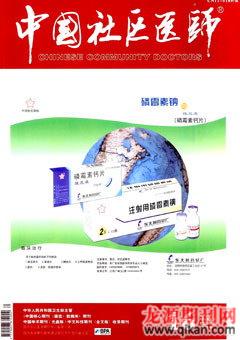疑难杂证如何辨治
董汉良
学生老师在上期所讲的2个辨治疑难杂证的总则之后,我复习了有关中医典籍,确实对我们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今天请把其余3条讲完。
老师第三是补阴、补阳、阴阳同补。阴阳必须保持相对平衡。疑难重危之痼疾常阳损及阴,或阴损及阳,故补阴、补阳诚为治疗痼疾之本。此言阴,为人之真阴,阳即为人之真阳。
补阴者,首推元·朱丹溪,他倡“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论,锐意于泻相火,补阴精的研究。后世视为滋阴派的代表。丹溪之学,源起于河间寒泻之说,河间之说直接影响温热学派的兴起,遂使后世有“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间”。热病最伤阴液,尤其病入营血或传入下焦肝肾,缠绵不愈,形成痼疾,治之棘手,此时常以养阴生津为要务,吴鞠通考究叶天士医案,参以自己的心得,著成《温病条辨》一书,总结出清络、清营、育阴诸法。温病后期,多成痼疾,伤及阴液,吴氏强调甘润存津,用加减诸甲复脉汤,此为滋阴之代表方。此方在诸多疑难痼疾中有很好疗效。
如董民康氏治黑尿热,小儿5岁,起病5天,突发高热,口大渴,尿棕黑色,泄泻呈黑色水样便,腹痛烦躁,病势危急,诊为:黑尿热。中医辨证为热久不解,转而入里,灼伤阴液,津血热涸之证。病属热病后期,热灼阴伤,即以三甲复脉汤主治,服药8剂,诸症消失而告愈(《中医杂志》1956年第5期)。
黑尿热是恶性疟疾的严重并发症之一,来势凶险,此案可资借鉴,并说明补阴之重要。丹溪倡补阴之说,大补阴丸,此方治疗疑难怪异之痼疾亦颇见奇效。如邱友文治双足心冷热异常案,七旬老翁,双足心冷热异常感7年,至夏双足灼热如焚,至冬胫以下至足心冷如冰,多方中西治疗,无时效。症见:颧红,舌红,脉细。用补水制火之大补阴丸治之竟愈。
学生我过去一直认为补阳重要,现听了老师的讲述和所举的病例,知道了补阴是补阳的基础,是缺一不可的,但补阳也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亡”,老师您说对吗?
老师你说的很好!补阳者,明·张景岳最有见地,他在《大宝论》中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凡阳气不充,则生意不广,故阳惟畏其衰。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万物,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矣。”这是张氏学术思想之核心,这对后世扶阳救脱,挽救垂危之痼疾起了很大作用。如现代河南著名中医周连三氏,据证凭脉认为: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后期应多用温阳之法。此三病都具有“实不受攻,虚不受补”之共同点,强调“有阳则生,无阳则死”。若病至后期脉欲绝,真阳欲脱之危候,常用茯苓、桂枝各30g,附片、党参各15g,干姜、炙甘草各12g,以回阳救逆,挽危重于倾倒。足见补阳在治疗垂危痼疾中的重要意义。
学生前后讲了补阴、补阳在治疗疑难杂证中意义,那阴阳同补是否更加全面?
老师你的认识完全正确,阴阳的本义就是这样。阴阳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所以单一补阴、补阳是不多的,故阴阳本需同补。张景岳所创右归丸为阴中求阳之方,左归丸为阳中求阴之剂也。后世治疗痼疾常多用之。如潘江涛氏治卧而半身不遂案,纯属怪异之痼疾,男,35岁,侧寐上侧肢体瘫痪,醒后须下肢体使劲推向平卧,待片刻即康复,两侧一样,昼夜不分,夏轻冬重。起病2年有余,且日趋严重,兼嗜睡形寒,舌淡,各医院诊断不明,后以右归丸治之,服10剂诸症若失,继服20剂,至今未发。
学生阴阳的调补、脾肾的调治、痰瘀的同治,这些都是原则上的东西,是否有具体的方法和方药?
老师下面要说的是具体治疗方法,但仅是给你一个提醒而已,扩展你的治疗思路为目的。即第四、五两条。
第四是内治、外治,运用偏治。
内治,是指内服药物的一种治疗方法,前后所述皆为内治之法,故不再重述。然而内治法的应用,尤其在痼疾证治中必须分清疾病的主次,明辨证候的真假,分析疾病因果,区别标本缓急,进行立法处方,以针对病机,审因论治,方能中的。在具体应用时根据痼疾真假不同,运用反佐、逆从之法,如大剂寒凉药中少佐温通之药,以治热盛火炽之证,重剂温热方中少辅寒凉之品,以疗寒盛阳微之候。或用热因热用,寒因寒用,通因通用的反治之法。根据痼疾的复杂性,在组方中必须周密布筹,汇集补泻、寒热、祛瘀化痰于一方。如王清任所列的诸多血瘀证,与寻常所言血瘀证不同,就得按王氏经验,按瘀血病机论治,像王氏所列秃发、白癜风、酒渣鼻、久聋为上部血瘀证,可用通窍活血汤治之。至今应用,常应手取效。王氏所创的诸逐瘀汤,治疗疑难怪异之痼疾的报道,屡见不鲜。
学生老师对内治疗方法的精密总结,对我来说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我将笔之于书,记之于脑,使于今后提醒自己。如何用外治之法来解决疑难杂证呢?请予指点。
老师外治之法,清·吴师机说:“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医理药性无二,而法则神奇变幻。”在治疗痼疾时为了弥补内治的不足,配合或单独使用外治,有时疗效甚著。吴氏以自己亲身体验认为“与内治并行,而能补内治之不及”,“余初亦未敢谓外治必能得效,逮亲验万人,始知膏药治病无殊汤药,用之得当,其响立应,衰老穉弱,尤非此不可”。可见外治法也很适合久治不愈之痼疾,也日益为医者所重视,外治专著纷纷问世,因此外治法在治疗痼疾时起着旗鼓相当的作用。如温州医学院儿科用麻黄、白毛夏枯草、贯众、象贝等制成煎剂,雾化吸入以缓解肺炎喘憋;青海传染病院用甜瓜蒂吹鼻治疗传染性肝炎;解放军181医院儿科用麻辣饼(生姜、葱白、胡椒等)敷脐治疗虚寒性腹泻等,不胜枚举。
学生偏治之法我第一次听说,请老师详细介绍。
老师所谓偏治,清·陈士铎说:“偏治者,乃一偏之治法,譬如人病心痛,不治心而偏治肝,譬如病在上,而偏治下,譬如病在右而偏治左,譬如病在四肢手足,而偏治其腹心也。”这就是一种灵活变通的治法。陈氏所著《石室秘录》有“临证一百二十八法”,皆可在治疗痼疾中为我们扩大治疗思路。如朱丹溪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医治以利药,益甚。翁诊之,右寸颇弦,谓日:‘此痰积病也,积痰在肺,肺为上焦,而膀胱为下焦,上焦闭,则下焦塞,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窍通而后下窍之水出焉。乃以法大吐之,吐己,病如失”。(《丹溪翁传》)此为下病治上之法。所以偏治常用于寻常治法无效时的一种治法,对于痼疾的治疗就要如此多加思索。
学生内外治法的配合,再加上偏治,对于打开我们的治疗思路确实很大,可谓数管齐下,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中医特色疗法。请老师讲最后的问题。
老师第五是药治,食治,巧用神治。
药治,即用药物的治疗方法,如前所述内治、外治之药。在药治中值得引人注意的是广采民间秘验方,收集民间草药以治疗痼疾之用。赵学敏在《串雅·序》中说:“昔欧阳子暴利几绝,乞药于牛医,李防架治嗽得官,传方于下走。”说明民间流传着许多治疗痼疾的灵丹妙药。故有谚日“单方一味,气死名医”,诚非虚言。如治癌肿的药物半枝莲、半边莲、猫人参、野葡萄根等,皆民间草药。笔者用山荷叶块根,治疗泌尿系结石,实践证明有排石作用(《琐药话》金盾出版社出版)。
学生食疗是很普通的方法,对治疗疑难杂证有何帮助令人费解,请老师费神了。
老师食疗,既可防病养生,又能疗病祛疾。前者称食养,后者谓食治。食治,虽视若平淡,然在治疗痼疾中也占一席之地,因为这是病人乐于接受的好方法,自唐·孟诜之《食疗本草》之后,元代有忽思慧《饮膳正要》,清时有王孟英《随息居饮食谱》,现今食疗专著更是琳琅满目。食疗中食养与食治两大优势在治疗痼疾中起着一定作用,自古至今不乏应用。如仲景之白虎汤,以粳米配石膏、知母,以清气分之邪热:大半夏汤以白蜜配人参、半夏,以治反胃呕吐;其他如桂枝汤、当归生姜羊肉汤、甘麦大枣汤等。后世开禁散,用陈仓米、石莲子配人参、黄连、石膏,以疗病重而垂危之禁口痢。如此之类,可以明证食治痼疾之力。江西著名中医杨志一,用食治法疗痼疾颇有经验。如文蛋鸡治哮喘:母鸡1只切块,上等柚子1只,切一盖去果实,纳鸡肉于柚中,加少许盐和水,盖上,黄泥封固,入火中煨熟,取鸡肉汁服食,立冬服1次,冬至服1次,以疗顽圆性哮喘:还有鸭蒜汤治水肿、水臌;猪胰治风疹瘙痒(《著名中医学家学术经验》之一)……痼疾转愈,可用食养调之,如龟板黑枣丸(龟板、黑枣为丸)以疗乳腺癌和术后调治;还有冰糖杏仁糊(南、北杏仁,冰糖)以作肺癌调养之用(《实用防癌保健及食疗方》),食疗优势正迎合了痼疾治疗的需要。
学生“药治不如食治,食治还需神治”。这句话,我似乎听到过,但具体出在哪里,原话我不清楚,老师一定知道,请您告之,并予释义。
老师程钟龄《医学心悟》中说:“谚语有曰‘药补不如食补,我则曰:‘食补不如精补,精补不如神补。节饮食,惜精神,用药得当,病有不痊焉者寡矣!”我从程氏之论,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药治不如食治,食治不如神治。七情六欲,情志之变,为人所独具,所以某些非器质性痼疾,如精神、神经及功能方面的疾病,常可调神达到病除。许多疑难怪症用神治可以见功。如张子和在《儒门事亲》有案可证:张氏治一富家妇人,思虑过度,“二年不寐,药石无效”。乃与其夫以怒激之,多取其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方而去,病人大怒,汗出,是夜困眠。神治的另一方面就是医生与病人需感情交流,所谓神往。减轻病人思想负担,密切配合治疗,促使痼疾能愈。作为医者《灵枢·师传》篇,有言:“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告之以其所苦。”使病者安定神志,焕发正气,提高抗病能力。
综上所述,痼疾证治虽列此五点,其实概括为二:①提出治疗思想即扶正与祛邪。祛痰瘀,以铲除深锢之病根,补脾肾,调阴阳,扶正气助赢弱之机体。②提出治疗方法即内外之治,药治、食治、神治、偏治等。此两者为治疗久治难愈之痼痰,设计初步的临证思路。分述的5条仅作临证时,碰到疑难杂证需辨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