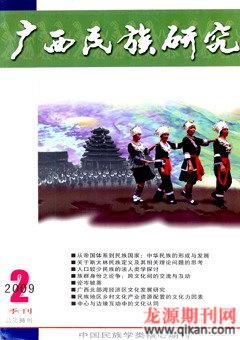关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反思
摘要:自2003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和保护工作就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以此为契机,各种旅游文化节应运而生。本文以“中国瑶族盘王节”这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模式为例,试图阐明以政府主控的旅游文化节给本民族“精神家国”可能带来的危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速失”,主体或“缺场”或“失语”,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了挑战,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反思
作者:谭红春,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讲师。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2-0172-007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技能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公约》同时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并会在与自己周边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是与已经逝去的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认同,并激发起他们对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同时,《公约》还表明“本公约所保护的不是无形文化遗产的全部,而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包括符合现有国际公约的、有利于建立彼此尊重之和谐社会的、最能使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那部分无形文化遗产。”可见,《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这样一些基本认识:1、是群体认同的依据;2、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3、保护的目的在于实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建立和谐社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公约》的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和保护工作也在我国迅速展开,大势之下,一呼百应,“申遗”工作一时热闹非凡。然而,成效如何,是否能达到《公约》所期望的保护目标,看来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索。
一、遗产主体的“缺场”
在遗产学与遗产实践中,遗产(heritage)的主体性和整体性至高无上,任何遗产的概念、分类和遗产的认知、分析都与遗产主体性、整体性的关系互为彼此、互相链接,它们构成一个原生性的有机整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遗产与人类的关系密切。就词义来说,遗产指一种继承关系,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继承关系从祖先那里获得遗留下来的财产。换言之,构成遗产至少应具备三个要件,即遗留物、继承原则、继承者的责任与义务,三者配合起来才构成遗产定义的框架。就遗产的本意而言,遗产是个人的、家族的、宗族的、村落共同体的、族群的,遗产属于继承者——“我”,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显然应当属于它的创造和继承者——某一个人、家族、宗族、村落共同体或族群。
在当下的“遗产运动”中,《公约》对遗产的界定具有立法的效应,它“不仅成为各缔约国在制定基本条款、指导分类、操作规章的依据;同时又赋予自身以政治性‘话语特征”。《公约》规定民族国家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唯一合法主体,从法理和技术的层面来说,《公约》的这一规定是勿庸置疑而且合理有据的。作为全球最大的政府间合作组织的下属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拥有200多个成员国,它们也是参与组织活动的合法行为主体,因此,将“民族国家”确定为遗产主体是合法的;此外,从技术层面来说,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无数的族群,如果遗产的主体仍确定为“个体”——某一个人、家族、宗族、村落共同体或族群的话,可想而知,遗产的申请和保护工作将陷入操作上的困难,加之保护工作还需要国家资金的大力支持,因此,以国家作为遗产主体更具合理性。由此我们看到,在《公约》确定民族国家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唯一合法主体之后,遗产的主体由“我”转变为“我们”、“民族国家”,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作为遗产主体的“我”真地就被“国家”所取代了呢?如果有人持这种看法,显然是对《公约》的误读。从《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释,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公约》倡导对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尊重,如果因为《公约》确定主权国家为遗产的主体就认为国家可取代真正的遗产主体,可以在遗产问题上越俎代庖,实际上就是对这一基本原则的无视甚至破坏。然而,在现实中,尤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类似的问题正在发生。某种程度有意的误读之下,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遗产保护的主导者。在发展地方经济的现实目标的驱使下,政府“积极地”承担了保护的工作,遗产保护和经济、旅游挂钩成为普遍的现象,结果造成和遗产主体分离,文化遗产的主体架空了,遗产的保护脱离了遗产的“土壤”。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包含的内容来看,瑶族盘王节的主体是瑶族同胞,也包括国外的,如越南、泰国、老挝、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地的瑶族同胞。我国有260多万瑶族人口,分布在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江西等省区。瑶族的支系有30多种。瑶族盘王节源自农历十月十六日的盘王节歌会,每逢这天,瑶民便汇聚一起,载歌载舞,纪念盘王,并逐渐发展为盘王节。“盘王节”,又称“还盘王愿”,有单家独户举行的,也有全村人举行的。盘王节的限期包括三天三夜和七天七夜两种,其仪式主要分两大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是“请圣、排位、上光、招禾、还愿、谢圣”,整个仪式中唢呐乐队全程伴奏,师公跳“盘王舞”,包括“铜铃舞”、“出兵收兵舞”、“约标舞”、“祭兵舞”、“捉龟舞”等;第二部分是请瑶族的祖先神和全族人前来“流乐”,“流乐”的瑶语意思是玩乐。这是盘王节的主要部分,恭请瑶族各路祖先神参加盘王节的各种文艺娱乐活动,吟唱表现瑶族神话、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内容的历史长诗《盘王大歌》。盘王节仪式由4名正师公主持,各司其职,还愿师、祭兵师、赏兵师、五谷师,每人1名助手,共8人,此外还有4名歌娘歌师、6名童男童女、1名长鼓艺人和唢呐乐队参与盘王节。这是传统瑶族盘王节所承载和构建的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共享传统文化的身体实践,在仪式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这种参与,强化了自己情感和认同,明确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责任,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村落生活和情感生活都是很有利的。
以我参加过的“中国连江第八届中国瑶族盘王节暨第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为例,可以更好地阐述这个问题。从节日的名称不难发现,这是一次捆绑式的展演,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政府行为,以保护文化遗产为名,以发展本地的经济、旅游为实的大型的文艺演出。从此,仪式或盘王节叙事的主题从民间、底层向官方、上层转移,仪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村落的、分散的、自由的,而上升为民族的、政府的、集中的、组织的。这是一个重新认识、建构、重现(展示)的过程。政府、
学者、开发商、民间组织、媒体在共同建构一个新的神话,现代版的神话一中国瑶族盘王节,而真正的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持有者——瑶族同胞,成为仪式表演的观摩者、局外人,政府和媒体掌握了话语权和操控权,他们在对文化遗产重新进行梳理、包装、整合和推销。这就是今天瑶族同胞所经历的盘王节,似乎已经悄悄变了味道:由亲近自然而变得遥远陌生。原来,节日就是自己生产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亲近而自然,如今,生活变成了表演,成了远方城里众人观瞻的节目,虽然还是熟悉的那套仪式和表演。然而,却显得那么陌生。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当遗产不可避免地涂上了现代社会中的商业色彩,当遗产进入到社会再生产的操作程序,当遗产变成国际组织和政府立法、行政的一种商议和实践对象时,现代权力便要“发言”,遗产便很难真正成为“发声”的主体,而要通过政治权力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对它的认识和保护价值。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毕竟商业化连接着一个巨大的文化再生产系统和消费观念,其中有许多是中介性机构和组织在起作用,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职能、利益和目标,它们会将遗产的价值引导到符合自己利益和目标的方向上去,比如将遗产引导到“消费方向”上去。这样就势必造成遗产主体性“在场”或“缺场”,而这种在场或缺场,不在世俗传统意义上的在与不在它们可以发生在空间(space)和地点(place)相分离的“虚化空间”。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支配的。即地域性活动的支配的。比如传统的瑶族盘王节,仪式空间和地点是一致的。在他们生活的村落,参加的主体是村落的居民。而现在,却不一定是这样,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空间日益从地点中分离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场所完全被远离他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仪式的发生地已经转移,在远离他们生活村落的城镇,仪式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符合舞台和媒体转播的要求,戏剧化、虚拟化、夸张化、舞台化。萨义德在《东方学》中阐释:“东方学家之所以在场其原因恰恰是东方的实际缺场”,这里套用到盘王节上,我们可以说:“瑶族盘王节之所以在场其原因恰恰是瑶族的实际缺场”。在这种市场化、旅游化、消费化的盘王节仪式表演或者庆典中,瑶族完全是缺场的,这种替代和错位的正好给政府从过去的“利用、发展”到今天的“保护、守护”敲响警钟,热闹的表象背后是对遗产的漠视。
二、被创造的“遗产”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述,有三个必要条件:1、群体或个人;2、文化空间和环境;3、认同感和历史感。我们相信,每个遗产都属于某一个特定民族的集体表述与记忆,即“过去”与“现在”到“将来”的联接纽带,没有这种表述与记忆便失去了“自我”,消弭了“认同”。瑶族一直用自己民族构建的神话、用神话语言表述自己的存在和瑶族人的身份,它隐藏起了自身的起源以及它所描述的那些东西的起源。按照福柯的解释,这是一种“历史——政治话语,通常,处在边缘化地位的群体为使自己的身份合法化,从而有利于理解自己的传统,在社会底层寻求解释,往往采取这一策略性选择,尤其是在发达社会处置不那么发达社会、强势文化支配弱势文化的情境之下,造就了民族精神内在一致性,从而享有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我们倾向于把文化遗产视为“族群性表述”和“谱系性记忆”,以强化某一族群的凝聚力。当今的遗产保护,由于外部因素的介入尤其是现代旅游、休闲与公共关系导人,“遗产”经常成为一个“被劫持”的符号。有学者甚至认为,它已经成为“制造遗产”的一个舞台。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表面上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实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的,而且有的甚至是被发明出来的“被发明的传统”。“中国瑶族盘王节,,正是这样一个被发明、建构和确认的“传统”。盘王节是瑶族人民纪念其始祖盘王(盘瓠)的盛大节日。瑶族是一个多族系的民族,本无全民族统一的节日。1984年8月,各地瑶族代表汇集广西南宁,共同商讨全民族统一的节日事宜,大家一致赞成以“勉”族系的祭祀节日跳盘王(或称为盘王)为基础,加以发展成为盘王节,并确定每年农历十月十六(盘王诞日)举行。1985年农历十月十六,全国各地的瑶族代表和民间艺人云集广西南宁,以联欢会的方式,欢度了瑶族有史以来第一次全民族的盛大节日——盘王节。1988年12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考察南岭地区,提出建立南岭地区经济开发区的构想,引起反响。1990年由广西瑶学会发起,贺县(现八步区)举办了南岭地区瑶族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提出由各县市轮流坐庄,每两年举办一次盘王节。1992年11月,贺县(现八步区)举办了湘粤桂南岭地区三省区十县市首届瑶族盘王节。2004年7月,在富川召开了第七届南岭瑶族盘王节预备会,与会的三省区市县市的分管领导和民族局长形成共识。认为南岭地区瑶族盘王节已成为南岭地区盛大的传统佳节和独具风采的文化活动,是南岭地区一道亮丽的旅游风景线和卖点,对发展地方经济大有可为。经商议,决定将“第七届湘粤桂南岭地区三省区十县市瑶族盘王节”更名为“中国第七届南岭瑶族盘王节”。2006年,“瑶族盘王节”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把盘王节做大做强,2006年7月,在连州市第八届南岭瑶族盘王节筹备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一致同意,从第八届开始,把“中国南岭瑶族盘王节”更名为“中国瑶族盘王节”。短短十多年,我们看到盘王节的名号花样翻新,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大,涉及地域也越来越广,涉及人群也越来越多。而这十多年,也是“盘王节”被再度“创造”的历史,而这其中,政府发挥了主要作用。
的确,“文化遗产”就像历史一样不能例外,它既是一种“传统的发明”,也是一种“传统的制造”,而在制造“传统”的过程中,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一个文化体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而只是对它的一种表述。表述,受制于表述者使用的语言。其次表述者所属文化的、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当政府以“理所当然”的主体介入保护工作时,遗产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这股强势力量的左右。我们从瑶族盘王节时间和名称“发明”,来看,就不难发现,当这种叙事的权力从民间向官方转移时,或者说被政府接纳和掌控时,传统的、自然的仪式会和权力、商业、旅游紧密的结合,成为一种新的象征符号,承载了更多的内涵,如:1992年湘粤桂南岭地区首届瑶族盘王节、1993年湘粤桂南岭地区第二届瑶族盘王节、1995年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四十周年暨湘粤桂南岭地区第三届瑶族盘王节、1998年广西钟山县第八节体育运动会暨湘粤桂南岭地区第四届瑶族盘王节、2001年湘粤桂南岭地区第五届瑶族盘王节暨清远旅游招商经贸洽谈会、2002年第六届南岭瑶族盘王节暨女书国际研讨会、2004年第七届中国南岭瑶族盘王节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