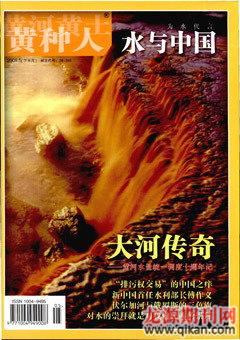“老河口”的黑色记忆
侯全亮
1972年春,渤海湾。
蔚蓝色的海面上,一股潺潺浊流缓缓地弥漫开来。黄河,从遥远源头的泉流中起步,一路接溪纳川、曲折跌宕,来到这宿身之地。然而,往常奔腾万状、极尽英雄之气的它,不知什么原因此时却疲态凸现,那悲怨的轻声低语,像是在倾诉着一路艰难的行程。
这年4月23日,河口右岸,旷野中坐落着几间简陋的工棚式院落。一位疲惫不堪的中年人从工棚里头重脚轻地走了出来。
黄河入海处,苍凉料峭,地势复杂,河汉纵横,芦苇丛生。大自然的孕育造化,在日益延伸的河口大陆架下留下了丰富的石油宝藏,但同时,由于这一河段窄如胡同,势似弯弓,加之地理纬度不一造成的上游河段偏暖、下游河段偏寒的气候温度差异,每当冬春季节封河开河之际,极易卡冰阻水,形成凌汛,决堤成灾。为解决这一忧患,一座规模宏大的南展宽工程于头年秋天破土动工。所谓“南展宽”,说白了,就是在黄河尾闻的南侧再修一道大堤,在两条呈“人”字形交合的新旧大堤内,延展出一片宽阔的蓄洪区来,以便凌汛紧急时开闸分洪,确保胜利油田的安全。
工棚架构的工程指挥部里走出来的这位中年人,就是南展宽工程的设计者——王锡栋。
王锡栋,胶东昌乐人,1951年山东黄河水利学校毕业。这位后来在黄河队伍中赫赫有名的“老河口”,此刻正显得忧心忡忡。
“老河口”的忧虑是有原因的:“文革”开始,他便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黑帮”、“绊脚石”一顶顶大帽子。正在这时,1967年伏秋大汛期间,黄河水涨势汹猛,情势十分紧急,在这举国动乱的年代,王锡栋被“洪水”解放,得以投身参加防汛……洪水安澜入海后,他作为技术组组长,率人测量查勘、规划设计,几经论证,一项南展宽工程的蓝图出笼了。如今,一万多人就在面前的展宽堤上施工作业,防凌安全,事关重大,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对于一个“臭老九”来说,任何环节一旦出现一丁点儿闪失,都足以给他再加上“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名,那后果便不堪设想。
施工现场距黄河主流只有百余米,当王锡栋赶到大堤上正想看看水情时,不料一场奇观出现在眼前。
“咦!黄河怎么还会断流呢!”“老河口”不禁惊叫起来。
他还从来没听说过黄河还会自己断流。自打少小时起他就听说,黄河洪水多么多么的厉害。后来参加了治黄,这种认识益加深切。百余年间,黄河在这一带决口达72次。当地老百姓流传的歌谣道:“棘子刘,王家院,黄河决了口,群众要了饭……”
的确,如若不是眼前活生生的情景,人们是很难将黄河与“水尽流断”的萧杀气韵联系在一起的。当天夜晚,“老河口”王锡栋在茫茫荒野的工棚里苦苦思索了半夜。
据资料记载,黄河这次首开记录的自然性断流一直持续了5天,自济南泺口以下至黄河入海处,断流河道长度达310多公里。两个月后,山东利津至河口河段又接连两次发生断流。这一年,古来奔腾不息汇身入海的大河,总共有19天停止流动。
对于蒙受这条母亲河哺育之恩的华夏民族来说,这无疑是一件石破天惊的重大事件。然而,当时的中国,笼罩在“文革”阴影下的人们,仍在为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所困惑。于是,发生在这年4月的一桩母亲河“首次断奶”奇闻,除了王锡栋等人的唏嘘与困惑之外,就此飘然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