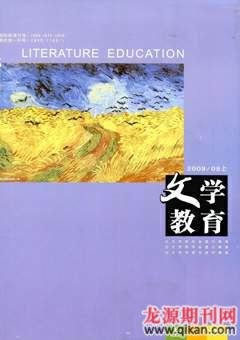从《终局》看贝克特戏剧中的荒原景象
在爱尔兰籍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所有作品中,《终局》是对“荒原景象”最全面、最完美、最绝望的描绘。
《终局》也称《最后一局》,是贝克特的第二部作品,这部独幕剧始创于1954年,1956年定稿,1957年4月3日在伦敦皇宫剧院用法语首演。像荒诞派戏剧的其他作品一样,此剧并没有任何明显的意义和主题,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剧中人分为两对:一对是哈姆和与哈姆不可分割的克劳夫,哈姆是一个又瞎又瘫的残疾人,克劳夫是哈姆的仆人兼儿子,他与轮椅上的主人一起等待着世界的“终局”;另一对是哈姆的父母——丧失了下肢的耐尔与纳格,他们被关在两只垃圾桶里,只有偶尔探出头来讨要一些残羹剩粥、说一些无聊往事。《终局》是贝克特作品中最灰暗荒凉的一部,同时也是剧作家最喜爱的一部。“终局”本是象棋中的一个术语,指象棋比赛的最后一个阶段。而戏剧《终局》则一开幕就出现了“终局”的效果,没有任何进展变化:剧中四位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是在荒凉世界中等待死亡,观众从一开幕看到的就是死亡世界中的“荒原景象”。而剧中人物所处的环境,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语言都是在诠释和证明这“荒原景象”的触目惊心。
首先,贝克特在场景的设置上给了观众最为直接的“荒原”感受。荒诞派作家非常强调舞台背景、道具、灯光等综合效果,贝克特把这种舞台语言称之为“直喻”,尤奈斯库称为“语言的延伸”,他们认为直观的舞台效果较之于语言更能引起观众的注意,激起观众的同情,所以荒诞派戏剧往往都会在剧本开头出现大段的场景提示。但需要说明的是,在舞台场景的具体设置上,尤奈斯库和贝克特这两位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却是截然不同的,尤奈斯库喜欢让他的剧中人在热闹的场合出现,比如吵闹的街区,布置繁琐的房间等,而贝克特似乎更习惯于让他笔下的人物在荒芜的场景中出场。观众最熟悉的也许是《等待戈多》中那条只有一棵秃树的乡村道路了,两位老流浪汉爱斯特拉冈(戈戈)和弗拉季米尔(狄狄)就是在这样的荒野中相遇并等待。贝克特1956年创作完成的另一出戏剧《哑剧一号》的主人公也是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上进行着哑剧表演。同样,他1961年用英文创作的戏剧《啊!这美好的日子》的场景也是万里无云的天空下一片光秃秃的平原以及一个长着几棵枯草的小土丘。相比而言,《终局》的场景则是从内到外的荒芜。这出戏的舞台设计非常简单:“舞台上无家具。淡灰色的光线。左右墙上,景深处,高高地开着两扇小窗,遮着窗帘。舞台前部的右侧有一扇门。靠近门的墙上挂着一副颠倒的画。舞台前部的左侧,一块旧的床单蒙着两个挨在一起的家用垃圾桶。”(萨缪尔·贝克特2006:5)屋内的荒凉是观众能够一目了然的,至于屋外的荒凉,剧作家则是透过剧中人哈姆的“眼睛”——克劳夫告诉我们的,小屋外是一切生命都已消失、一切运动都已停止的世界:没有了大自然,种子将永远不会发芽,没有任何东西在动,没有地平线,没有太阳,到处都是淡淡的黑色。这是一个绝对的荒凉世界,小屋中的几个生命就是在这个即将消失的茫茫荒原中等待最后的灭亡。
其次,贝克特通过展示人物之间的隔膜与仇恨让观众体会到人际关系的“荒原景象”。人际关系的恶化是现代派文学的表现热点,存在主义大师萨特提出的“他人就是地狱”这一主题是二十世纪文学的热点,荒诞派戏剧也尽力地在表现这一主题。但贝克特戏剧中的人物之间并没有过于明显,或者说过于轰轰烈烈的仇恨和争斗,在剧作家笔下一切都那么平静,似乎发生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而人与人之间平静的淡漠,无声的疏离却又是那么的悲凉。贝克特戏剧中的人物大多孤独,而剧作家又特别喜欢让这些孤独的人成对出现,比如戈戈和狄狄、波卓和幸运儿、《哑剧二号》中的A和B、《最后一盘磁带》中现在的克拉普和以前的克拉普。这些成对的人物相互对立而又彼此依赖,他们形影不离但却永远不能消减对方的孤独感,反而会因为隔阂与不解增添对方的孤独感。剧作家这样做一方面增添了作品的喜剧效果,另一方面也用反衬的手法进一步说明了个体的孤独以及人际关系的荒凉。《终局》中的人物也是成两对出现的:哈姆与克劳夫、纳格和耐尔。他们表面好像是一家人——人物以家庭单位出现在贝克特的戏剧中是很少见的——哈姆有父母,有既是仆人又是儿子的克劳夫。但是这个家庭的亲情关系却令人悲哀:首先哈姆和父母的亲情已荡然无存,他把父母装在肮脏的垃圾桶中,如果嫌他们厌烦,还会命令克劳夫关上桶盖,置他们于黑暗之中。父母对儿子也是非常地冷漠,从他们的回忆中我们得知,在他们年轻时,曾因孩子的哭闹搅扰了他们的安宁而置孩子于不顾,偷偷地搬到别的地方去,母亲耐尔也曾悄悄地劝克劳夫抛弃哈姆。父母的自私、儿子的冷酷完全违背了传统的家庭伦理和家庭道德。而主人公哈姆和克劳夫的关系则更令人绝望:瞎子哈姆虽然不能离开克劳夫,因为后者是他的眼睛,他的手臂,他语言的行动者,他长篇大论的忠实听众,他也似乎把克劳夫看成他的儿子:“我将在那儿,在那又旧有老的避难所里,独自面对静寂和……呆滞……我将呼唤我的父亲,叫唤我的……我的儿子。”[1](萨缪尔·贝克特2006:62)但是哈姆实际上却对克劳夫没有任何的亲情和怜悯,他表现更多的是自私和冷酷,他不断地指使和呵斥克劳夫,使后者一直处于忙乱和恐惧的状态。而克劳夫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他很小就失去了亲情,从哈姆的叙说中我们知道克劳夫是被父亲遗弃的,哈姆收养了他,所以即使哈姆对他很粗暴,他也不能离开供给他食物,给他安身之地的哈姆,他必须服从哈姆的任何命令,因为如果他离开,他将因食物的缺乏而必死无疑,然而他表面上虽唯唯诺诺,内心却十分的憎恶哈姆。这一对互相仇恨却互相依赖的人物使整个戏剧充满了张力。
再者,通过思想的空洞以及行动的残缺来塑造人物的“荒原景象”。《终局》中的人物卑微低贱,他们不具有丰富的思想、高尚的感情和崇高的理智,他们的精神世界就像他们所处的自然世界一样荒芜。全剧以哈姆和克劳夫梦呓般杂乱无章的对话为主线,夹杂着纳格和耐尔庸俗下流的调笑和抱怨,他们的话语既无逻辑性也无趣味性,充斥着重复、跳跃、感叹和疑问。正常语言的缺失和交流的困难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和思想的“荒原”——他们的思想只是一片已干枯的、失去了青春的、没有绿色的不毛之地,虽然主人公哈姆似乎正在构思一部长篇小说,并且他也一直在讲他的作品,但是他话语的断断续续和思维的紊乱却使我们感觉不到也捕捉不到他未来作品的丝毫重要性或是必要性。另外,舞台上的四位主人公生理上都是残缺不全的,他们的行动都是受限制的:哈姆双目失明、下肢残疾、无精打采、哈欠连连;而他的搭档克劳夫则关节僵硬、步履踉跄、目光呆滞、语调平直;那两个垃圾桶里的老者更是像他们的栖身地一样的残缺肮脏。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思想都正在“荒原”上死亡。这种死既是自然的死亡,是人的生理器官在损耗中的最终衰退,是春华秋实之后的酷暑严寒,也是精神的死亡,是现代人在道德上的自我沦丧,自我摧残,也是西方人对上帝、对社会、对存在的“荒原”的彻底绝望。
总之,在《终局》中,作者通过对“荒原景象”夸张至极和绝望至极的描绘旨在强化现代人的危机意识,唤醒麻木的观众对当代生存环境,对现代人际关系,对人类自身的存在及未来发展的关注和忧虑。只有察觉了荒诞,发现了荒诞,才可以改变荒诞。荒诞派作家们正是通过让观众感受荒诞去抨击荒诞。因此,这种戏剧表面看起来是消极的,但它却并不一定是虚无主义的。剧作家在描绘自己所认为的一种时代景象时,也要求我们共同分担他的义愤和沮丧。虽然他常常不作回答,但却激起人们去寻找答案,促使人们在生存困境中去摸索一条出路。于绝望中发现希望,赋予无意义以意义,在有限的自由中寻求脱身之法,这是荒诞派戏剧家们借他们的作品所暗示和启发我们的。英国剧评家、荒诞派戏剧的定义者马丁·埃斯林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表述这种绝望的情景,赋予观众睁眼正视它的能力,便构成了一种净化,一种解脱。”(马丁·埃斯林1992:185)这正是荒诞派戏剧家们所孜孜不倦追求的最终目标,也是他们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
注释:
[1]文中译文均选自萨缪尔·贝克特:《终局》,节选自赵家鹤、曾晓阳、余中先译:《贝克特选集》(4),《是如何》,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参考书目:
1.马丁·埃斯林:《荒诞派戏剧》刘国彬译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
2.赵萝蕤编:《荒原》(中国翻译名家自选集)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
黄珂维,女,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外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