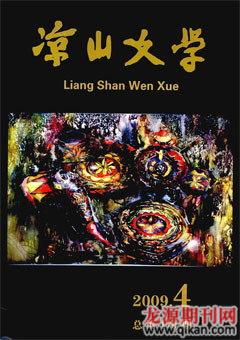木炭·彝人(组诗)
普驰达岭
突入城市,我们就像一支迁徙的部落,无以着陆。
——题记
木炭·彝人
我是彩云之南深山猎人兰花烟头点燃的一粒木炭
我是云岭牧人背上那一块皱巴巴翻着穿的羊皮褂
我是纳苏毕摩念经作法摇落的那串叫魂的铃声
山林季风柔柔抚不平我原始沧桑的足迹
历史悲惨茫茫诠释着我一路指路滑落的泪水
当锅庄灿燃的火光照亮了瓦板房的四壁
当呢喃的阿依悄然在阿嫫怀中睡去
当鹿子和獐子的蹄印
连同那片与岩羊一样孤独的冷杉林
变成老猎人梦中千万遍涉猎的风景
季节的河流在我的身后不再流淌
我是阿普手中传送的那碗香醇的转转酒
我是阿嫫在瓦板房下夜夜缠绵呻吟的歌谣
我是游牧于红土高原上的那一枚不落的太阳
其实啊
我是那一粒被遗忘在瓦板房墙脚的木炭
山谷冷冷的风是我的白天
猫头鹰凄凉的鸣叫是我的黑夜
破旧的蜘蛛网封锁着我的视野
午夜裸奔发情的老鼠在我的四周肆无忌惮地窜来窜去
我离喧嚣的都市越来越远
当寒冷的季节封冻了那扇破旧的木门
我期待被一双温暖的手
抚摩着回到燃烧的锅庄旁
用智慧的目光
找回我的记忆和骄傲
如令我离瓦板房的老主人越来越远
如今我距瓦板房的新主人越来越近
其实啊
我就是那一粒被遗忘在瓦板房墙脚的木炭
需要温暖的人会点燃了我
不需要温暖的人会熄灭了我
石之语
太阳是支格阿龙的
月亮是蒲嫫妮依的
天地是阿苏拉则的
石头是阿迭阿嫫的
太阳的高度是阿达的
大海的宽度是阿嫫的
雄鹰的速度是天空的
锅庄的温度是彝人的
太阳请带上彝人千年的荣耀吧
月亮请把远古的眷恋叠成翱翔吧
雄鹰请将毕摩的祈祷带给天菩萨吧
石头请把彝人矗立成天空的高度吧
直眼人从高度俯视
我的忧伤飘在风里
我的快乐躺在云上
香树坡
被深冬梳理过的香树坡
就安静地坐在那坡头
占着一片天空
日夜乘着自由的山风
香树坡就躺在
我花了一个半小时上坡
再花两个半小时下的坡头
远看香树坡很小
近看香树坡很大
看着香树坡很近
走起香树坡很远
近得我一跨就可以到这
远得我三步一停十步一息
爬过香树坡的人都说
人间香树坡累倒十头驴
香树坡就在云南
就在云南那个叫双柏的地方
它靠着六芝的坡头
它离无煤猿人的牙齿很近
它离那片红色的土上长出的红色土林也很近
诵词与玛纳液池有关
所有的太阳就算在星回节的夜晚
重蹈而来七月的洛尼山顶
依然会有厚厚妁雪躺着
布与默尼与恒武与乍
会潜藏着史尔俄特之雪脉
举起毕摩冥箕的诵词
凝视水的源头和归祖的方向
再次上路或开始或结束
迁徙中的旌旗总会以水的姿态
一次次越过昭通垭口
抵达玛纳液池
河流的宁静还是高原的驰远
总有夷人成片的光芒在玛纳液池
无法释怀就像归祖路上迁徙的羊群
在前方等你等你携带祖灵和经书
鹰语与经诵浩瀚而来
在阳光之外在洛尼山以东在朱提以西
每一片雪花都将恪守指路行移于归祖
每一个漂灵都将留守聆听候游迂祖训
每一句毕诵都将繁盛神旨浩荡之定势
在玛纳液池荞麦还原为荒凉的时刻
阿迭逐渐衰老远方漂泊的灵魂
穿越河流再次移行
在去往玛纳液池的路上水落石出
所有摇曳在归路上的魂灵
都将抵达玛纳液池放置
风蚀的眼睛风沙的耳朵
干枯的手指龟裂的嘴唇
“阴间水昂贵渴也喝三口不渴喝三口”
抵达了玛纳液池
审视归祖之路渐渐冷却
当忽略疼痛与阳光之一刻
所有的生命都将俯身于沉默之间
我也将接承祖训
“阴间水昂贵渴也喝三口不渴喝三口”
祖灵之舞
洪水泛滥之前在夷龙河畔
没人知晓祖灵仰望的眼神
时间流逝日升月落
星光茫茫宇宙游移
在地平线上游走的时令像一片孤云
一切幻变是遥远的生命之脉
清浊浮沉而乾坤的光芒
在蝌蚪一样的经文中闪烁
神灵的品性从混沌中折射智慧的底色
在天地之间
混沌是你的影子
你的肤色与水有关
从清气而来从浊气而生
混沌就是你的命脉
哺和哎撤下的光芒
引领你一路灵舞而来
沿着美姑河沿着金沙江溯源而上
翻过乌蒙山越过哀牢山苍茫迁徙
沿着阳光雨露浸蚀过的路你找到食邑之地
高高的天菩萨与天地融为一体
鲜血擦拭过的双手举起来
陈旧的物事涌出来
羊皮书上的文字如同春天的花草
在我们眼前次第开放
砍倒大树做成房屋
捣碎苦难欢歌成舞
霞光漫过南高原
甜荞花开灿烂一片
夷龙河上的歌谣
一群鸭子顺着你的翅膀而来
绕过冬天深处的群峰
用成群结队的语言拍打着两岸
漂蓝了夷龙坝子的天空
那个年月
有个叫罗婺的营盘
安静地坐落在你的怀中
手中的利剑划过苍茫的洱海
那个年月
有个叫纳苏的部落
安静地用透明的羽毛
弹拔着动听的马布
用黑黝黝的语言喝唱着《梅葛》
他们迁徙的步伐一次次抵达
那个名叫玛纳液池的地方
一眼清泉
总淌着他们幸福的眼神
那个年月
夷龙河肥肥胖胖奶水充足
人们快乐着
躺倒在水的深处
即使在梦中都能起身
用幸福的手掌
把星星一样的鱼群
赶回瓦板房
用残损的鱼刺
刻出动听的歌谣
传唱着夷龙河的悠远
昭觉路雪
五月的雪翻过博什瓦黑梁子
走近腹地凉山的前后左右
解放沟山连着天天连着地地连着雪
苍苍茫茫路雪
萦绕出凉山最深切的语言
高挺的英雄结成群结对
穿过白得透明的峰峦
季节在五月的深处
诠释着被雪孩子嚼白的大凉山
那件挂在身上的擦尔瓦
串连着阔别十四年的思念
点沸成温暖的巢
阳光像一朵盛开的索玛花
移植在我站立的山头
可以自由转身的空地上
鸟的踪迹已被洁白的语言覆盖
像倒挂的羽毛
纷争着竖起白白的指尖刺向天空
很多熟悉的母语
在雪峰粗细不一的根部
在雪线以上在雪线以下
在雪的上面在雪的下面
纷纷向我靠拢
顶着雪迹而上的羊群欲语又止
散落在路雪上的热气聚聚合合
慢慢爬上有黑雾散步的雪峰
在路雪之下
五月的昭觉裸着身体坐在水之源头
生命的缘淌过千里彝山
在低低的山谷上高高地举起
我再次深入凉山腹地的背影
那些看不见的水
那些看不见的水停在空中正在六月
那双远离南高原的手活在家园舞在十月
那棵站立于风中的树用骨骼的呼吸和生命的光芒
摆渡着历史的忧伤熟悉的母语被风高高挂着
那些看不见的水那些做梦开花的树
那双待在风中的手或在六月或在十月
在北方独自合满一个彝人的思念
一年十个月在南高原上升起来的月亮
是在六月涉过掌鸠河蹿回罗婺部后
到一个叫普施卡的彝家山寨来过火把节的
一年十个月沿金沙江走下山坡的太阳
是在十月穿过大小凉山潜入洛尼山后
到夷龙河畔叫普施卡的彝家山寨来欢度彝族年的
在六月所有那些看不见的水
在十月所有那些做梦开花的树
所有停泊在六月的碎片
所有驻留在十月的语言
在月光下清清楚楚
在阳光里明明白白
木板房锅庄石鹰爪杯……
羊皮褂百褶裙擦尔瓦……
让南高原成形的往事。
以及在思念过往中变老的一切
忠贞地验证着所有的存在与真实
那碗候在神座前献祭祖灵的转转酒
那杆靠在火塘边让阿普怀旧的老烟枪
那支还剩半截不欲丢弃的蓝花烟头
那只挂在屋檐下遭遇无数猎物的老猎枪
那声声被毕摩(百末)通天祭铃透穿的经文和弥弥的毕(百)诵
在月光的肯定下走向那条不可逆转的隧道
停在六月止于十月的一切元素
如那些看不见的水即使倚着倒塌的栅栏
也会纷争着挤出双眼推开一扇通往南高原的门
让一个彝人在北方亮出记忆厚实的依靠
那些看不见的水那些做梦开花的树
那双待在风中的手在六月的北京
勒紧一段段彝山的往事如那只布满鹰虎龙图腾的木碗
被轻轻握于掌心熟悉的味道一直流向十月流向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