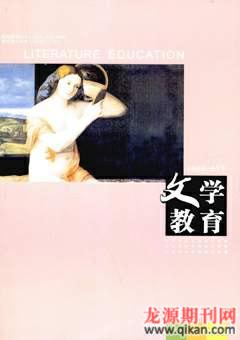李清照前后期词愁情比较
一.李清照前期词中的“愁”
(一)少女的浅浅闺愁
十八岁之前,李清照的生活简单而平静,在闺阁绣楼中过着养尊处优的少女生活。但悠闲的日子总会泛起些许少女愁绪的涟漪。深闺独处,不免心生空虚孤寂之感。寂寞的背后,隐然飘荡着一丝少女朦胧的“思春”情怀。在《浣溪沙》(莫许杯深琥珀浓)中,将深闺沉闷和心灵苦闷的闺愁表达得淋漓尽致。“醒时空对烛花红”,一个“空”字牵出了词中人的幽怨和寂寥,散发着女主人心无所依的惆怅,以及渴望爱情的意欲。同时,感叹韶光易逝的惜春愁绪也浮现在词人早期的作品中。《浣溪沙》(小院闲春春色深)中,女主人面对暮春,梨花欲谢,不胜惋惜春事将残,叹息自己青春年华的流逝,人生命运的无奈,滚滚愁思又在心中翻荡。
(二)少妇的淡淡离愁
十八岁,李清照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开始了幸福的婚姻。甜蜜替代了闺愁。但当夫君起至莱州,短暂的离别,又荡起少妇心中无尽的相思离愁。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缠绵,“人比黄花瘦”的憔悴,“新来瘦”的无奈,词中人处处向读者倾诉着一寸柔肠成千缕的愁情。希望与丈夫永远厮守,但诸多的意外让他们不得不饱尝分离的酸苦。悠悠的思情,折磨着思妇脆弱的身体和敏感的心灵。一个愁肠满怀的思妇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从少女到少妇,从汴京到青州,李清照的愁绪都还停留在个人情感上,关注的只是个人情感生活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但无论是闺愁,还是离愁,都显得那么的淡,那么的浅。
二.李清照后期词中的“愁”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李清照的生活不再幸福安定,由于主和派的卑躬屈膝,词人被迫南渡,开始了漂泊的日子。南渡后不久,丈夫去世了,她开始了凄凉感伤的寡居生活。家亡国破的不幸,深深地刺痛了她那颗柔弱的心灵,也唤醒了她关注大局的忧患意识。但她只是封建社会一个普通的弱女子,只能借助文字,直击现实,将所有的哀愁凄苦、爱恨离愁,都渗透到词中的每一个文字。面对一场劫难,词人的情感已经不再局限于自身的点点滴滴,而是充满了暮年飘零的沦落之悲和故土沦丧的身世之感,进而升华到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命运的关注,她的灵魂开始敏锐地思考,深沉地思索,暗暗流着哀国之泪。痛彻心扉的分离,凝结成永远的思乡愁,亡国恨。《武陵春》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词人唯有借泪来倾诉南渡的亡国辛酸,无依的孀居之痛。《菩萨蛮》中“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道出了词人无法排遣的乡愁。《永遇乐》今昔对比,热闹的元宵节背后,深藏着词人无限的感伤和落寞,道尽了悲怆凄凉之感。
三.两段不同滋味的情愁
词人前、后期词中倾吐的“愁”,是在品尝生命历程中不同滋味时所生发的思绪。南渡前,词中带着几分少女朦胧且稚嫩的愁绪,将一个愁肠绵绵,充满相思、幽怨的思妇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南渡后,词中蕴含着国破家亡的酸楚,愁思更浓烈深沉,一个在离乱中从深闺少妇转变为饱经风霜的暮年孀妇的形象已悄然进入读者心间。“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原本幸福快乐的李清照,就是在与心爱的丈夫离别,与深爱的祖国别离后,孤寂和落寞牵动了内心最柔软的愁肠,触碰了全身愁苦的神经。
后期词中的“愁”,是前期情感中的升华和凝练。在前期词中,词人塑造的形象还是一个含蓄矜持的大家闺秀,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人,目光仅在花花草草,分分合合中游离,独享一花一世界的快乐与忧伤。但后期词中的主人公形象已是一个充满忧愤,能心念国家存亡,懂得亡国恨的大女人。满腹的愁情是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沦亡的无限哀叹和深深痛惜。
从少时的闺愁,到之后的离愁,再到暮年的哀愁,从小女人的情趣到大女人的成熟,两段不同的“愁”滋味,是词人内心情感的真情流露,将复杂多样的愁绪串联起来,勾勒出李清照真实的生命轨迹。
参考文献:
[1]《李清照词鉴赏》齐鲁书社 1986
[2]《自是花中第一流》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惠娟 2005
[3]《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4
廖冬萍,女,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