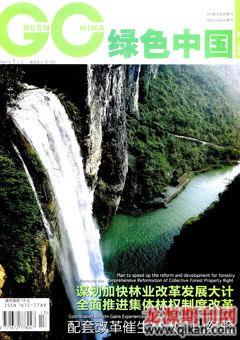现代经济学的生态缺失
蒋伏利
2009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将在2008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4.59%、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4.42%和5.95%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推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定不移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天降大任于中国。其显著标志是,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不但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而且,还于2009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这说明,中国正在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挥手告别。
能够与中国政府走循环经济之路的坚定之音形成呼应的,不是西方诸国的政府,而是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作家凯尔斯盖。他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种种乱象,毫不客气地发出了尖锐之音:“被广泛应用于过去、当今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根本性的谬误,不是简单的修补就能够解决。甚者,需要一场革命,在经济思想认识上进行彻底的‘范式转变,才能透过重新认识经济和经济学的本质,以达到架构一种新的能够指导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说的预期。否则,就算人类逃过此劫,更大的灾难还会不期而至。”
凯氏指出,传统经济学,无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即西方现代经济学),其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一直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的”。可是,事实证明,这些假设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甚者,本次全球金融之海啸只是表象之一,更大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自然之海啸,已经有所表现并显示了强大威力,2004年东南亚海啸不过是其冰山之一角。
保护生态社会发展的需求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须臾不能割裂的依存共生之复杂生态系统。而且,本质上,复杂生态系统是大系统,经济系统不过是其众多子系统中的一个。经济系统得以存在的基础或者前提只能是也必须是生态系统。之所以如此,盖因人世间普遍存在“社会——经济——自然”之共生共荣关系。在人口、资源、环境等社会经济发展诸要素中,谁也无法脱离这种关系而单独存在。在上述关系中,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物质来源。然而,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人们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各种各样的资源,与此同时,人们又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这样,就必然产生两个问题:一个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从而引起它的供给能力的问题;另一个是自然环境对人类排出的废弃物容纳量的有限性,从而引起它的自净能力的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关系,便产生了所谓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人与自然即传统经济学与自然生态矛盾作用的结果。
无论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承认与否,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都是人口与人均产值同时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由科技革命引起的工业革命持续发展。由此造成全球性两大环境问题:一是自然资源耗竭。表现在两方面:可更新资源的破坏日益加剧;不可更新资源储量不断减少,有的濒临枯竭。二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城市空气和噪音污染,食物污染等。由此,我们可以认知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合理的保护和改善环境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这是由环境所固有的功能决定的。其一,环境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质的来源。如矿藏、空气、水、土地等,都是人类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二,环境是处理废弃物的净化器。其三,优美的环境能大大提高人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盲目破坏环境,就会严重限制经济发展,甚至使发展难以为继。其一,环境的破坏不仅对当代的发展不利,而且对继承遭到破坏了的环境的后代人的发展更不利,有些后果甚至是不可补救的。其二,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不仅对一种经济组合体产生整体负效果,还会由区域化发展为国际化、全球化。其三,严重的环境压力,又必然与高经济损失和高治理成本相联系。
基于上,我们可以得出环境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的理性判断。然而,由于受研究对象制约,传统经济学理论,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只能看到也只能重视经济规模、经济人的作用,而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决定性作用和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作用,则严重低估并忽略不计。对此,致力于研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的法国索尔邦大学经济科学终身教授勒内·帕塞提出了强烈质疑。尤其当有人问及环境退化是现代经济学体系的一个可以纠正的偶然意外,还是现代经济学体系运转逻辑的结果的问题时,勒内·帕塞激动地说,“我认为,而且我们许多人都这样想过,损害环境是符合自由贸易和生产本位主义体系的逻辑的。因为这个体系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结果把生产成本转嫁给环境。这种趋势现在更加变本加厉,其原因众所周知,即权力已经从公共政治领域转到国际金融和私人利益集团,后者越来越多地控制企业的管理和决策。追求产量和过度使用资源是同金融资本迅速赢利的迫切需要连在一起的。”
人类在长达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因为对环境的影响有限(没有被发觉),微观经济学侥幸发展了一百年。虽然,后来有所察觉,宏观经济学在投入产出方面,也试图通过重视价值平衡、物质平衡来弥补环境缺陷,但因局限于一国经济系统内部之物质循环和价值循环,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依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以关心制度变迁之交易成本、激励机制等著称,但因与生俱来的短视,同样没有对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给予足够重视。即便融会贯通、有机综合了市场、竞争、需求、供给、成本、价格、收益和分配等微观经济学基本要素,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所得、财政、金融、就业、外贸、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学基本要素,以及制度、交易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要素之大成的传统经济学之显学,也因为沉湎和陶醉于学科概念体系的成熟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拒绝接受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和启蒙。
对此,作为一位强调公民义务,强调尊重人类、尊重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持续发展的模式,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基于现代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学家,勒内·帕塞更有强烈抨击:“经济学认为污染是一种偶然意外,而且根据经济体系的逻辑,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充其量在市场上把环境的成本纳入产品价格。于是市场成为灵验的污染控制者,污染化为一个次要的功能障碍,只需通过价格逻辑加以纠正就是。对于这种看法有好几个异议。首先,污染源并未全部发现,受害者和受损情况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很少考虑到真正的代价。其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所谓代价不仅仅是市场价格。污染涉及人类生命,涉及容易破坏的资源,涉及大自然环境中不可逆转的
效应,因为大自然中每一个物种既是捕食者又是被捕食者,起着一种调节作用,同其他物种相互依存。这些因素都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只是在一个自然财富变得稀少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大自然的大平衡中保护它为时已晚的时候,市场才会赋予它价值。因此,我们要维持环境的运作状态,因为生命,特别是人类生命,以及经济活动,都有赖于环境。你若破坏环境,你就毁灭一切,包括经济。”
毁灭,毁灭大自然,毁灭人类,这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其在发展上的表现,即单向度“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线性经济运行模式,单向度“资源—产品—废弃物”(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之线性经济发展模式,被传统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而价值高贵不能怠慢的生态系统,不但被传统经济学排斥于发展和保护的行列,而且,还被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腴厨娘被恣意蹂躏和践踏。有学者指出,在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影响层面,传统经济学向来是“只见经济不见外部不经济”、“只见经济效率不见生态效益”、“只见特定资源稀缺不见所有资源稀缺”、“只见发展不见生态”,其不可持续发展缺陷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全球气候变暖之东南亚海啸等重大自然灾难。分开说,微观经济学由于过分相信经济人的理性(这种理性是靠不住的。岳玉珠教授指出,利己是人之本性,它一方面成为价格机制下的市场竞争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人性的自私和机会主义也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在一定的条件下,人在利己的时候有意或无意的去“损人”,包括环境等)而对达成的经济效益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害视而不见。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过分强调国家政治对经济过程的干预作用(这种干预作用同样是靠不住的。陈文平教授指出,国家政治表现形态之一为政策,而低劣国家政策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带来的只能是恶之花,不但不能帮助国家经济保护环境,而且,还在冠冕堂皇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的口号下,极尽环境破坏之能事),无心亦无意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带来的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其理论上的根本错误,按照勒内·帕塞的说法,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没有“让经济服从于人类和环境的终极目标”。其一,没有一种经济理论,敢说经济不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改造大自然的一种活动。舍此,经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其二,环境的种种问题,以及人类和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都是因为经济活动本身成为了目的,而忽略了人类终极目标,即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用老子的话说,是天人合一。其三,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都强调要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然而,经济增长的概念和基础是什么呢?传统经济学解释说,国民生产越增长人们的需求越能得到满足,即是经济增长概念及其基础的总和。源头上,这种经济观与其形成的时代大体是相吻合的。其时,人们的基本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此经济发展阶段,确实是越多生产就越多创造财富。现在最贫穷的国家也是如此,比如乌干达,比如朝鲜。此阶段,由于生产活动危害生物圈还未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还未危及生物圈的重大功能,例如今天全球的热调节功能,故自然生态问题被经济学家抽掉了。令人可怕的是,在发展的向度里,现代经济学依然依历史惯性坚持把经济同人文和环境相隔离,脱离背景片面地考虑经济问题,即,只重数量不讲质量。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问题是,在当下的发展里,不能说地球上汽车增长一倍,人也跟着舒服了一倍。因为,汽车更多了,是为谁?为什么?有什么后果?等等这一些,都要求我们考虑人的问题,考虑社会的问题,考虑大自然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需要思考,通过损害人类和破坏自然环境而获得的增长是发展吗?这种行为发生的理论基础即现代经济学反动吗?
由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无限度追求经济利益、利润最大化,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从而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大索取和大消耗,让生态赤字演变成今日全球气候变暖之东南亚海啸。这种恶果的产生,基于传统经济学一厢情愿对“资源稀缺”的假定,只是针对“特定资源的稀缺”并作出了相应的“最有效的配置”,从未认识到这个星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需要“最有效配置”。故此,催生了经济增长无极限的预设,并将经济增长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等同。其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粮食、工业品、资源的消耗以及污染都在增长。尤其资源消耗和污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经济增长速度更快更可怕。
现代经济学的生态短视
一个不得不提及的问题是,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下,上述情状有救吗?对此,勒内·帕塞回答说,很难。其一,没有比思想体系的改变更难的东西了。其二,抵制太多,尤其在经济理论范围内。其三,现代经济学俨然以惟我独尊的科学理论之面貌惑众并拥有了包括西方之资本主义和东方之社会主义在内的广泛的受众。其骗人的招数之一,就是把市场说成是中性的,因而是经济问题上主宰一切的惟一的裁判员。这个所谓的市场调节中性论实际上是维持目前的体系原封不动,包括无法接受的人文和环境的代价,以及永远对掌握金钱和吸引金钱的人有利的力量对比。其四,是既得利益的作用。有此四者作用,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宁可牺牲地球的未来,也不愿触及人文和环境。因此,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是荒谬的,如果一直让其荒谬下去,我们大家包括他们自己都将一起被毁灭。
然而,还是要问,为什么?尖锐学者告诉我们说,盖因植根于非数学概念之社会科学范畴,而又比自然科学范畴之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更强调数学概念及其运用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将物理学之研究物质客观规律的方法、手段运用于经济运行过程、经济发展模式等研究中,导致研究者只见经济之物不见超越经济的诸如文化、道德、生态等非经济之物。其所见到和重视的只能是物化(即以最小代价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及其作用,而对于非物欲的诸如文化、道德、生态等“类本质”诉求,一概加以排斥和拒绝。其结果是,传统经济学已然登顶数学化程度最高的学科祭坛,在事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反复强调,作为一门特定的学科、一种特殊的职业,传统经济学及其学家不讲道德,也不应该讲道德。其以“物化经济人”为特征的经济原教旨主义在这里暴露无遗,其违反自然生态的本质也在这里暴露无遗。
在历史长河里,考虑大自然是十分长远的考虑。勒内·帕塞警告说。相比之下,经济上的长远考虑根本微不足道。从大自然的节奏、资源的再生、环境的恶化考量,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下的经济活动之影响,何止以百年更是以千年来计算的。于是,这里就涉及道德责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范畴里是找不到答案的。于是出现另外一个东西,即哲学家汉斯·乔纳斯所说的“责任原则”,即我们对生命、对人类发展的责任。在这个有关责任的价值范畴里,因为价值多种多样,而且无法论证,于是必然牵连两个东西,即涉及目的之政治范畴高于经济功能,以及允许各种价值对抗和共存的民主的合法性。而这,也许就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之经济原教旨主义的由来。与生态原教旨主义一样,都是反动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邪教。
鉴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及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学正在走向反动,正在成为自然生态和人类的敌人,甚者,由于这种反动不但导致了当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而且,还将以毁灭为代价让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同归于尽。所以,如何反思并架构、推动一种新的经济学来指导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即勒内·帕塞所说的,如何创造一个能考虑到这个复杂世界中相互依存的各种因素的新的经济学方法,是将来之事,更是当务之急。好在基于反思精神并扬弃、超越传统经济学的生态经济学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上世纪已经诞生、发展并开始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指导经济社会的发展。
(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责编耿国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