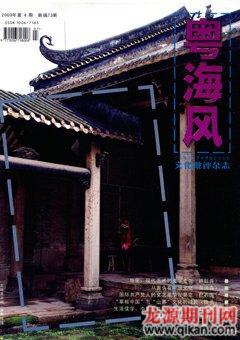“山寨中国”与后发现代性国家的历史宿命
徐 刚
时下所流行的“山寨”这个话题其实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在实体层面,指的是广东等南方诸省近几年出现的“黑手机”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这些模仿、贴牌的“山寨手机”的巨大影响对品牌市场的冲击;另一方面指的是由“山寨手机”推而广之而上升到的文化层面,这包括“山寨春晚”、“山寨明星”,甚至“山寨劳模”等极具颠覆性、戏谑性和娱乐性的“文化造反运动”。在大多数人看来,极具“亚文化”特性的“山寨文化”,也就是山寨的后一种意思,更具有文化阐释的价值。但在我看来,后一意义其实不过是此前由“馒头”事件煽动的狂欢及“恶搞”文化的一次并不遥远的回声,依然是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对消费文化所裹挟的“点击率的经济学”(或“眼球经济学”)的诉求,并隐约表达了一种后社会主义威权政治结构下的民间怨恨。坦率来说,这其实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文化新意,而恰恰是“山寨”在其实体意义层面上引起的,对资本及品牌意义的思考更具有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比起“山寨”的文化意义来说,它的实体意义其实更具有文化意义。
在此,我们有必要将话题锁定在“山寨手机”之上。而在这个地方,一个显而易见的二项对立就是“山寨”和“品牌”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对“品牌”这个概念做一个探究,就会发现在这个概念背后隐藏着一套异常清晰的资本主义的逻辑。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资本的逻辑中,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价值形式,一种是物质层面实在的部分,即商品的“物性”价值;而另一种则是商品的虚拟价值,即“神性”的部分,它们作为物品的附加值而存在。一般来说在市场上,越是高档的商品,所谓大品牌的商品,其虚拟部分的价值就越高,泡沫越多。因为对于它来说,它出售的不仅仅是一个物品,而更多的是附着在这个物品之上的虚拟的品位和时尚,而这一部分的价值却是远远超过实际物品本身的。在这个意义上,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来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越是大品牌的商品其实越是暴利的商品。我们如果看看整个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的运转逻辑都是围绕着巨大的虚拟价值展开的。对于资本家来说,他们早已不再满足于仅仅通过制造业来剥削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了,而是转而大力发展商品本身的虚拟价值。一方面,他们通过广告来制造消费者对时尚和品位的欲望,来成功销售单纯商品外的高额附加值。这就像美国理论家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这本书中所讲述的,在广告中,万宝路香烟把自己从一种“物”提升为一个“神”,这种神圣化和性格化使它变成了和粗犷的西部、强健的男人紧密相关的东西。于是,对香烟的消费就变成了对一种迷人的幻想的消费,而这部分的价格是远远超过烟草本身的。而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立法来保护所谓的“知识产权”,杜绝别人对自己产品模仿的可能性,从而保证自己对相关技术的垄断,以维持一种高额利润。
简单来说,“山寨”手机其实就是对资本主义“知识产权”,以及技术垄断的一种颠覆。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种后现代的社会运动。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中,实际上已经勾勒了这种新的社会运动的形式。当今世界,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后果,资本的逻辑无处不在,反对知识产权,生态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的蓬勃兴起,已经构成了对这个制度的抵抗,同时又是这个体制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其实最为重要的是,“山寨”对资本逻辑中甚嚣尘上的“品牌文化”进行了有组织的反动。提起“品牌”,就不得不谈到加拿大女学者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那本《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该书的中文版最近在大陆得到了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克莱恩被认为是反思品牌文明最深刻、最重要的文化观察者。她走访跨国企业在欧美、亚洲、非洲各地的作为,写成《No Logo》一书,引起了全球广泛的回响和争议,并被反全球化主义者奉为运动宣言和理论圣经。这本书提出了“拒绝品牌”(No logo)这个概念。她认为,我们已经落入了一个“人即品牌、品牌即文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企业已不再以制造产品为己任,而是制造图像,营销品牌,产品本身反而成了品牌的“填充物”,这其实是“伴随着无限消费选择”而出现的一种“奥威尔式对文化生产与公共空间的新型钳制”。在这种状况下,世界的多样性正在消失,城市景观被广告影像淹没,社区文化被品牌文化吞噬,人看似有了更多的选择,实则已经没有选择。而在跨国公司的第三世界代工地,每一个血汗工厂都是工人悲惨状况的印证。在书的最后,克莱恩鼓动读者挺身抵制,“为全世界人民而战”,走上街头,大声抗议,涂抹广告牌,改写广告语,清洁社区,收复街道。
毫无疑问,这本书包含着一种反全球化的浪漫与激情。这其实就是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所概括的“后现代的社会运动”,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抵抗姿态。中国的山寨运动显然并没有达到那样的境界,但或多或少体现了一种对品牌的颠覆和拒绝,对品牌文化的一种“去魅”。从社会心理上说,山寨是对品牌意识的反动。品牌的原初意义在于节省交易成本,防止信息屏蔽,但我们时代的品牌,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是质量本身难以让人信任,二是品牌附加值泡沫化。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有人指出的,山寨之所以在2008年爆发,主要是源于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应对。今年山寨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整个中国社会对品牌的信心大幅下降”。这个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初,由于苹果公司与中国移动的谈判失败,导致Iphone的热爱者只能购买解码后的水货;毒奶粉事件,对消费者的品牌信心打击非常大;金融海啸,雷曼兄弟银行的倒闭,包括美国三大汽车厂商纷纷减产或者关闭生产,还包括百度竞价排名事件等等,由此而延伸到年年重复的“央视春晚”,导致大家对“品牌”的信心全面丧失。本来品牌的产生,就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通过多次博弈建立消费者的信心与忠诚度,让大家能有一个消费指南。现在既然品牌全不可信,那就只能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或者口碑,来选择自己使用的产品。在整个社会对品牌信心大幅度降低的背景之下,山寨产品终于大行其道。以山寨手机为例,它以较高的性价比满足了消费者的市场需求,它之所以受到追捧的市场逻辑其实非常简单。正如经济学家所分析的,国外品牌的手机在市场上卖到2000多块钱,但是山寨机卖不到1000块钱。这说明国外品牌的手机有很大的暴利成分,反映出市场竞争的不充分。其实在这背后最实质的问题,恰恰在于一种“去品牌化”的价格还原。山寨手机将手机从品牌的包裹中剥离出来,将商品还原到了一个“物”的层面。这样,“联发科”的芯片加上自己生产的外壳,手机只是一个成本加利润的简单贸易,在去除了高额的品牌附加值之后,山寨使商品贸易回归古典式的简约与单纯。
由手机产业带动的山寨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风起云涌,已经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对此,香港的《亚洲周刊》提出了一个“山寨中国”的说法,这恰是对这一现象的生动把握。“山寨中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提法,在这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全球化历史氛围中,后发现代性国家的历史宿命。在一种全球化的历史氛围中,消费文化的弥漫和跨国资本的扩张,现代性的“脱域”机制使得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被迫卷入到这个系统当中。对品牌文化或奢侈品的消费,也许对于前现代的人们来说并非必要,但正是全球化使得后发现代性国家也开始迷恋品牌,热衷消费。然而现实的情况其实又无力支撑这种奢侈的消费格局,于是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就悲剧般地产生了。后发现代性国家不得不面对现代性的挑战,资本的流转和品牌的扩张正是题中之意。在此,山寨的勃兴其实包含着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比较复杂的情绪,有一种伤感和无奈,也有一种戏谑和狡黠。香港学者阿巴斯主编过一本文化研究论集《国际文化研究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中收入了英国的穆斯林评论家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的一篇论文,题目叫《赝品的政治经济学》(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fake),其实就从第三世界的角度谈到了类似“山寨”的问题。他的短文讲的是赝品和盗版的问题,其中举了印度孟买与拉美的例子,还指出在信息时代如CD等文化制品,在物理上已不存在正版与盗版的区别。不过他上升到道德层面,指出后发国家很容易认可全球文化,但无法支撑其消费成本,必然会产生“赝品”,而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其实既培养又支撑了这种文化。最后他指出,“赝品”其实正是欠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的一种对策,一种“无赖式”的颠覆和无奈的反抗。
对于“中国制造”开始席卷世界,当代中国已然成为引以为傲或者令人羞愧的“世界工厂”时,“山寨中国”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正如经济学家郎咸平经常举的那个例子,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在国际市场上售价10美元,而它从中国出厂时才仅仅一美元,也就是说,从生产到销售,有9美元进到了美国人的腰包,而辛勤的中国人只分到了十分之一。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是一个品牌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国际经济格局中不平等的经济结构。如果对这个结构足够警醒,或者不再沾沾自喜于那一美国的血汗收入,“芭比娃娃”的中国制造者们就应该在既有的制作工艺上做一些改进,加入自己的创新成分,开发出“山寨”版本的“芭比娃娃”,那么它的竞争优势是极为明显的。在这个意义上,“山寨”也许是“中国制造”摆脱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
当然,中国的精英分子和“有志之士”既看不起“中国制造”在国际格局中的低端地位,也对山寨产品的模仿、抄袭、创造力的匮乏、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猛烈抨击。但是实际上,我们看看亚洲的一些后发现代性国家,如韩国、日本等,其实都是在对西方的模仿,甚至剽窃中起步的,如日本精工对瑞士手表的学习,韩国三星对日本索尼的学习,甚至是中国的联想对美国惠普的模仿等等,前者正是在对后者的学习、模仿中进一步创新,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向成功的。正如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在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概念。它的含义是说,假使发达国家最早进行创新,创新的源头在发达国家,那么其产品向世界销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次发达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掌握技术了,可以进行模仿创新。模仿创新到一定程度的话,也可以形成竞争关系。这时,如果先行者再不进行创新的话,他是有可能会被超越的。从经济发展的阶段上来看,模仿是欠发达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要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肆无忌惮地漠视既有的经济规范和市场逻辑,也就是说,这个过程的展开也需要在当下的经济秩序中完成,尽管这个秩序对于后发现代性国家来说并不一定是合理合公平的。因此,对于当下风起云涌而又良莠不齐的“山寨”产品来说,“知识产权”等等也是需要高度尊重的。而对于政府来说,山寨在名称、外形、商标、品牌等方面的侵权固然应该加以限制,但对于那些技术成熟了的企业,政府应该提供合法的生产保障,而企业也应该向创立品牌的正规化生产转变。因此,对于“山寨”来说,它面对的是一个如何在边缘处求索的课题:既要在规则之内,又要伺机颠覆这个规则,这便正如当代中国在资本全球格局中的命运。可以预见的是,良莠不齐的山寨必将经历一个分化整合的过程,在这大浪淘沙之后,谁也不敢保证“山寨”的“寨主”不会是中国的下一个精工、三星或者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