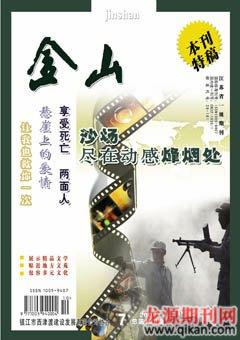谁来了
韦如辉
一阵警笛忽然划破平静,一队车辆按编号从大街上驶过。每个车子都打着应急灯,并十分礼貌地保持着车距。
来了,大伙儿说。谁来了?大伙儿又问。
交警全部上街,岗亭上加强了警力。昔日的红绿灯下,站立着英姿飒爽的女警。女警全副武装,双手戴白手套,身材俊秀挺拔,动作干净利索,与红绿灯的配合天衣无缝。
工商人员三五成群,正在清理店外店。他们的语气很严厉,少了过去的劝说。几乎所有的工商人员都是一个口气:三个小时内搬完。否则,罚款三千。这语气,省略了许多的法律程序,包括陈述申辩和听证。
市容局正在对损毁的主干道护栏进行修补,原来有锈迹的地方,紧锣密鼓地加紧刷漆。油漆很白,阳光下有点儿刺眼。中午他们都没下班,有五六个人站在路边满头大汗地吃方便面。
环卫的洒水车倾巢出动。各主要干道,都跑着这些笨重的家伙。白色的水柱,扇面似的打开,正好覆盖整个路面。人群朝人行道散去,各行其道。相向而行的车子,立马摇上玻璃。跟在后面的车子只有耐着性子如影随形。有一个骑电动车的,没来得及拐进人行道,淋得落汤鸡似的。
园林规划处的同志,在县界的省道口,用各种各样的鲜花,摆上一个大花坛。鲜花竞相怒放,五颜六色,姹紫嫣红。细一看,是五个字:热烈欢迎您!
社区的干部们根据职责划片包干,赤膊上阵,大打一场垃圾歼灭战。垃圾车左一趟右一趟地穿梭,垃圾堆越来越小。这些城市的毒瘤,正在被信心百倍的人们彻底铲除。只有苍蝇,嗡嗡嗡地围着垃圾车不肯离去。它们这些活跃分子,正在失去快乐的家园。
文化馆接到一项政治任务,抓紧排演一场既丰富多彩,又凸显地方文化特色的文艺晚会。馆长急坏了,脸上流的不知是汗还是泪。他在电话里哀求,您快点回来,机票给您全报,还安排专车到机场接您——演地方戏的一个名角,远在南方打工,馆长不得不像孙子一样地央求他。
城关二小和西关村幼儿园的院内,分别训练着一群统一校服的孩子。大一点的孩子练着舞蹈,小一点的孩子手里摇晃着彩带。老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教,一个姿势一个姿势地练。她似乎还有点儿不耐烦,不过嗓子哑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变调,好像要冒出火。孩子们的脸蛋红朴朴的,汗水从头上流下来,通过额头,脸,流到嘴里,咸咸的,涩涩的。但他们有足够的耐心,无论扭、转,还是蹲、卧,都十分认真,生怕有哪一点做得不好,不到位。
城市的上空,有两架滑翔机不停地飞来飞去。滑翔机的噪音很大,飞来震耳欲聋,飞去还余音袅袅。
街道上迅速拉上横幅,如同从地底下一下子冒出来似的。横幅上有大体相同的宣传口号。横幅的下面,都有一行小字,分别写上某某局、某某办、某某处、某某校的落款字样。
大街上有许多闲人。大伙儿仿佛闷在家里无聊,都被这奇怪的现象吸引到街上去了。
大伙儿才想起来,这天是星期天。星期天,大家都在工作,都没有休息。
思维敏锐的人问,谁来了?
大伙儿伸出目光的触角互相探询,谁来了?
没人知道。
我打电话问一个单位的头儿。这个头儿平时跟我关系很铁,在我这儿,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头儿电话那头气喘吁吁的,不耐烦地说,没事儿玩去,别烦我。我推测头儿不是在加班,就是刚挨上边的批评。不然的话,不会对我发那么大的火。
第二天,这个城市仿佛脱胎换骨,空气中弥漫着芳香的味道。上街的人们,都觉得舒服极了。
一阵警笛忽然划破平静,一队车辆按编号从大街上驶过。每个车子都打着应急灯,并十分礼貌地保持着车距。
来了,大伙儿说。谁来了?大伙儿又问。
大伙儿还是摇着头。
晚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五儿吗?
我问,你是?
那头说,唉啊,我是三儿。你让我找得好苦啊!你快点来,我在春色满园大酒店。
三儿,是我小学同学。那一年临放暑假,我一拳打掉他一颗门牙。
车把我接到春色满园大酒店,县委办的主任给我介绍,这是书记,这是县长,这些都是我们县六大班子的领导。主任还说,你是张三的同学,也来陪一陪张三。
我悄声问张三,你小子怎么混这么大?
张三哈哈大笑,一嘴的黄牙在灯光下十分扎眼。
张三后来在我们县办了一个工厂,很大,可以安排上万人就业。
再后来,我在张三厂里当上厂副,月薪八千元。
后来的后来,张三的厂冒出来的烟,把县城上空的太阳都弄黑了。
后来的后来的后来,厂子倒了,张三腰缠万贯地走了。
张三说,跟我走,到外边发大财。
我没去。我说,我恋家,发不了大财,命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