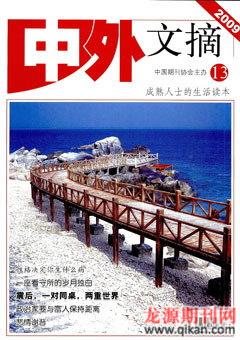麻桌上的国学大师
锅 贴
麻将,亦称马吊,又称雀牌,自清末流行开来,成为一种相当普及的娱乐活动。不仅深受市井百姓青睐,就是文化名人、达官显贵,也乐此不疲。他们与麻将的不解之缘,也留下了诸多趣闻轶事。
梁实秋,想打麻将到八大胡同去
梁实秋自小家教甚严,及到读书,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也留下了对麻将的坏印象。
梁实秋身边的好友如胡适、徐志摩、潘光旦等人都是麻将爱好者和高手,有几次硬被拉上桌,他玩了玩,很是吃力,觉得打牌不如看牌轻松过瘾。以后好友酣战,他总是作壁上观。
对此,他解释说“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为自己志行高洁。我脑筋迟钝,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我缺乏机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顾不过来,遑论揣度别人的底细?干脆不如不打。”
相比之下,一贯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的梁启超就痴迷得多。他认为“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它是好的”。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有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就是约了麻局。
梁启超有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任公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据说梁启超的很多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
胡适,麻将里头有鬼
胡适也喜欢打麻将,他曾谐趣地说,从各国对游戏的特殊爱好上看,可以说英国的“国戏”是板球,美国的“国戏”是棒球,日本的“国戏”是相扑,中国呢?“自然是麻将”。
但胡适的水平并不高,梁实秋就曾亲眼见胡适输过,有一年在上海,胡适、潘光旦、罗隆基、饶子离饭后开房间打牌,梁实秋照例作壁上观。当时,胡适坐庄。潘光旦坐对面,三副牌落地,吊单,显然是一副满贯的牌。胡适摸到一张白板,地上已有两张白板。胡适的牌也是一把满贯的大牌,且早已听张,犹豫好一阵子,啪的一声,还是把白板打了出去。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板。胡适身上现钱不够,还开了一张三十多元的支票,这在那时可不是小数目。
相对于胡适的每战必败,胡适的太太江冬秀在方城战中可谓每战皆捷,这让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适,坚信“麻将里头有鬼”。据唐德刚(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回忆,胡先生时以“手气不好”自嘲,认为手气不好是“鬼使神差”的,与技术无关。
上世纪50年代初,胡适和太太江冬秀困居纽约,全靠往年积蓄度日,生活拮据。“中华民国驻纽约领馆”曾奉“政府”之命,给他送来一万美金宣传费,以解博士之困,但胡博士一丝不苟认死理,坚决不收,于是乎外援断绝。幸好胡太太垒四方城的功夫十分到家,麻将收入成了一项补贴家用的“计划内收入”。
徐志摩:最暧昧是打麻将
在文人当中,辜鸿铭的牌技是最差的,还因而获得了“光绪(光输)皇帝”的雅号。而徐志摩的牌则打得最漂亮,他善于临机应变,牌去如飞,不假思索,有如谈笑用兵。
据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中记载,徐志摩对鸦片与麻将还有一番妙论:“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不过,文人里头也有对麻将深恶痛绝的。例如,鲁迅就从不打麻将,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晚年住在上海,几乎天天听到邻居打牌的喧闹声,妨碍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恶。”
算起来,胡适应该是对麻将爱恨交加的那一类。他一方面爱打麻将,一方面又痛心地说,“如果举国狂打麻将,对一个民族来说是极危险的。”
据胡适估计,当时全国每天至少有100万张麻将桌,“按每桌打8圈,每圈半小时计,可消耗400万小时,相当于损失了16.7万天的光阴。”他并以史为证:麻将的祖宗马吊在明代曾风行天下,士大夫整日整夜地打马吊,把正事荒废,清入吴伟业认为明朝正是亡于马吊。
(摘自《看天下》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