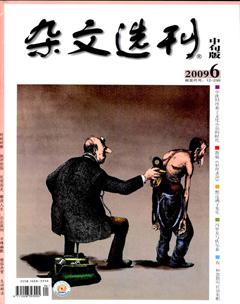我是社会的晴雨表
何满子
我是社会的晴雨表。只是我的遭遇稍稍具有典型色彩,晴雨表上水银柱的气压升降刻度指示得格外醒目而已。
解放初期我在高校教书,既不是官,也和金钱事务无涉,因此,“三反”、“五反”这类运动同我沾不上边。接着,文化领域里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以俞平伯为靶心的《红楼梦》研究,气压也颇低得窒人;幸亏那时还没有逼得人人必须表态的规矩,上钩不上钩取决于我自己,我这支晴雨表暂时还没受到干扰。自此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前的历次运动,我都恭逢其盛,无役不预。我的生涯中的重大折腾都精确地反映了社会的气压变化,简直是如响斯应,十分灵验。
下面是我的履历表反映的社会气压表:
1955年,天才的组织家把我组织进“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逮捕入狱,关了一年零五个月,糊糊涂涂地进去又被糊糊涂涂地释放。
1957年,我被“扩大化”为“右派分子”。以后在处理时,因有“胡风案”的“前科”,不能按处理“右派”的六条办法来,由法院判处机关管制三年,管制期间剥夺公民权,相应开除公职。
1958年,大跃进,我被遣发至宁夏自治区,以拉板车为业。
1960年,因“彭德怀右倾反党”运动的蔓延,宁夏展开“双反”运动,我被遣送劳改农场服苦役。其间被处理为“劳动教养”,押送到三处劳教农场,均以“不堪劳动”被退票,仍回原地服苦役。
1961年,服苦役时我在劳动现场休克,假死数小时,被送到医院急救。此时,“大跃进”已掩盖不住全国浮肿的“大跃退”,气压稍有回升,开始了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我被解除劳教,管制期也已届满,我请假回上海治病。在此一年间,微升的气压略呈稳定,我几乎有了调回上海工作的可能性。
1962年,气压陡降,发布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律令,人事、户口冻结。次年我不得不再回宁夏,因为“人在单位中”,倘若花名册上没有列名是没有生路的。
1964年,宁夏拒绝接收我这“废物”,不知哪来的一线机缘,我被调回上海,在愈来愈低的气压下苟延残喘了两年。
1966年,黑云压城,十年动乱开始。我被红卫兵定为“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后一条是属于很文明的“无罪推定”)三项罪名,押送回原籍交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呆就是十二年,正如我当时效黄景仁《绮怀》的一首自嘲打油诗中的一联所说:“烧尽诗书归大火,丢光文化出中年。”
1978年,拨乱反正。我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旋即召回上海,重操旧业。接着又改正“右派”的错划,“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彻底平反,我的生命从六十岁开始。
八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年中,总体说来还称得上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痛韶华之浪掷,恨追挽已无方。二十年来不敢懈怠,贡献微薄,平均每年以一又四分之一本的频率出书。即使所发的尽是些谬论,至少也为盛世的文化市场添了些微热闹。除了感叹自己本事实在不济之外,自顾也还对得起自己和世界了。
以上扼要开列的我五十年来生涯的流水账,庶几能反映社会的风雨阴晴。那些年头里窒息人的气压和那个十年的狂飚暴雨,身处其中是十分难堪的。经过一番死去活来,终于盼到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顺顺当当地活了二十来年,真该心平知足了。
五十年中前一半的日子是难过的,但不幸中也有可庆幸之处。因为我在1955年知识分子最早的一起大灾难中就沦陷了,所以在以后风谲云诡的年代中免除了一场场严峻的考验。我的贱民身份使我无须掺和到人群中去表演、作秀,做出事后令人作呕的失态、丢格的丑事来。在那种低气压的年月里,能洁身自持者不多,没有创造性的表演已算很不错了。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因为早沦为贱民而逃脱了考验,这不是很该庆幸的么?不能行善,也免作恶,伟人说“坏事变成好事”,信然信然。
【原载1999年10月17日《南方
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