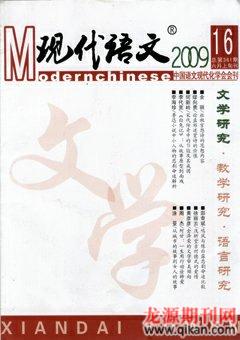都会性爱与情爱的不同感应者
谭 华
摘 要:性爱与情爱是刘呐鸥小说中的两个重要元素,而活跃于都市的男性和女性则是这两个元素的实践者。他们虽然都是性爱与情爱的参与者,但对性爱与情爱的感应却不同。
关键词:刘呐鸥 性爱 情爱 都市
刘呐鸥是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开山作家。这个“敏感的都市人,操着他的特殊的手腕”,用那几近“解剖刀”式的文字,书写着现代都市男女的两性关系,传达出现代都会男女性爱与情爱观。
一、性爱至上
两性主题是新感觉派小说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新感觉派小说最具特色的主题。在刘呐鸥的小说中“性爱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渐渐疏远,性爱本身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看重”[1]。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笔下的性爱描写也真正具有现代性的意义。性爱至上是刘呐鸥着力表现的一个现代元素。这种性爱至上的生活观在刘呐鸥小说中的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性爱的满足与享受是女主人公孜孜不倦的追求和乐此不疲的实践。对于这些穿行于都市的女性而言,“性的社会角色功能已然悄悄的降低” [2],“五四”情爱神圣的理想灯塔在她们面前轰然倒塌。家庭、贞操、道德、羞耻等等像被“扭碎的白纸一样”坠落。性爱至上超越了一切社会理想而成为女性追求的终极存在。
性爱至上在文本中具体呈现为:女性往往是性爱游戏的发起者,性爱游戏过程中的施虐者和受虐者,性爱游戏结束后的弃绝者。小说《游戏》是这样来描写移光和步青的整个性爱游戏的。在一个充满光色味杂沓的“探戈宫”里,上海摩登女郎移光主动上前和一个手托着腮,桌上放着一瓶啤酒,老守着沉默的独身者搭讪。在短暂的交流之后,他们便在声光的刺激下疯狂地享受彼此跳动的生命。她在一边享受旧情人爱恋的同时一边接受作为工厂主的“新郎”馈赠的六汽缸的意国制的一九二八式的野游车。在“新郎”走后,移光再次主动约上步青,在短暂的邂逅之后,他们又上演了一场逢场作戏式的性爱游戏。游戏中,移光主动成为性爱的施虐者,步青甘愿作为性爱的受虐者。当这场戏曲终人散的时候,移光毫无惦念地告别了仍在回味着的步青。这场游戏从开始到结束,女性始终处于主动者的位置,她“是欲望和欺骗游戏里的圆满赢家”[3]。她丝毫不因袭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担,不受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纠缠。对于移光而言,性爱不再预约给婚姻,而仅仅流为人的动物性的满足。
刘呐鸥笔下的都市女性大多毫无掩饰地享受性爱带来的肉欲乐趣,甚至堂而皇之地以此收获实利的消费品。在刘呐鸥其它的小说中如《风景》、《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流》、《残留》等,其中的女性如移光一样,都是性爱的表演者和操纵者,也是性爱的至上主义者。在《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一个刚刚在赌马中赢得了一千元钞票的H,便被一个微笑的“她”盯住,在打发空闲时间的过程中,这个近代型女性把自己的身体像商品似的出租给H,但是对H一点也不露什么感情。在属于H的时间中,“她”完全献身于H。当短暂的租期到期之后,“她”便毫不犹豫地离两个呆得出神的人而去。在这场交易中,性爱于“她”而言已经超越道德情感的界限,而成为可以换来物质回报的媒介。性爱于“她”具有至上的意义。
对于刘呐鸥笔下的男性而言,性爱和情爱于他们更显驳杂。他们和这些都市女性一样,同为性爱的消费者。性爱的原始性力量在他们身上依然合理存在着。他们和这些现代都市的“尤物”一样,体验着现代性爱的自由、开放、简洁、轻便、刺激和疯狂。作品中的每一个男子几乎都不会拒绝性爱,都抵挡不住女性的引诱和吸引,都在性爱的狂欢中寻求精神的刺激和肉体的释放。《游戏》中的步青没有因移光架设的“三角恋”而放弃享用她贞操的破片。《风景》中的燃青虽然表现出绅士般的尊严,但他还是抵不住火车上邂逅的太太的主动邀请。《方程式》中的密斯脱Y在像解决了方程式一般的爽快中一边闻着身边氲氤的温香,一边手掌里乐着美满的触感。他们都是性爱的接受者。在刘呐鸥小说中不管是自由、大胆甚或随便的现代女性还是充当男人附属品的女性都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了男性世界的一道“都市风景线”。男性也在主动或被动中接受着享受着现代性爱的快感与刺激,他们也是性爱的消费者,性爱至上的实践者或崇拜者。
二、情爱欲求
情爱是文学中一个古老而年轻的话题。情爱的浪漫与张扬是“五四”启蒙文化理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情爱神圣是“五四”都市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情爱神圣的命题逐渐被刘呐鸥及其海派作家对性爱的超验书写所取代。但是在早期的海派作家笔下已然残留着情爱神圣的影子。生活于都市的男性虽然身居最现代化的都市,过着摩登的生活,但是他们并不像都市女性一样完全迷恋和沉醉于现代的都市性爱中。他们对情爱有着特殊的欲求。对情爱的追求反映出“五四”情爱神圣的命题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延续。他们身上仍然残留着传统的情爱神圣的因子。他们有的渴望情爱与性爱合一,有的祈求性爱指归于婚姻,有的梦想情爱的神圣与纯真。《流》中镜秋一面被晓瑛原始、自然的身体跃动了满身的血,一面又向晓瑛虔诚地求爱。镜秋对待女性的态度体现出性爱与情爱的合一。
刘呐鸥作品中男性既是现代性爱的实践者,又是传统情爱的思慕者。他们向往圣洁的爱情,希望从女性那里得到的不仅是能释放性爱的肉身而且还是能慰藉自己的真诚灵魂。在《热情之骨》中比也尔把玲玉看作一个梦寐以求的圣女,可是正当比也尔与她缠绵悱恻,渐入佳境时,“在那强大的压迫的下面,那脆弱的身体像要溃碎了。她并不抵抗只以醉眼望着他。但是忽然樱桃一破,她说‘给我五百元好吗。惊得比也尔半晌不能讲出句话来。他想梦尽了,热情也飞了,什么一切都完了。”比也尔一直以为玲玉不仅外貌娇好,而且灵魂高尚。但是当他得到这个女性的那一刻,他才发现他一直犯着错误。比也尔渴望的是性灵的合一,哪知道最后得到的还是脆弱的肉身。这个事例反映出刘呐鸥作品中的男性不仅在乎女性的身体,也在乎女性的灵魂,不仅需要性爱的满足还需要情爱的慰藉。
男性复杂的情爱观折射出他们身上仍然残留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刘呐鸥的男主人公依然保持着过时的父系制的道德感性。”[4]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依然有着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神皈依”[5]。在传统的文化中,男性往往主宰和占有着女性。不管是在婚恋还是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刘呐鸥小说中的男性也在不断追求他们在都市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如《礼仪与卫生》这样写到:妻子可琼跟随一位认识不久的法国商人离开姚启明,她主动提出让妹妹白然来陪伴丈夫,并哀求丈夫不要与她离婚。妻子的哀求实际上满足了姚启明将妻子视为财产,即使无爱也要永久占有的欲望。对于姚启明而言他其实是名利双收。因为早已厌倦了妻子,巴不得妻子离开留给他猎取其他女人的自由空间。这样姚启明就既可以尽情享受肉欲的狂欢,还不承担一夫多妻、道德败坏之名。姚启明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反映出刘呐鸥在作品中所持的男性中心主义立场。
刘呐鸥的男性情爱观是建立在菲勒斯中心主义上的。男性对女性的情爱追求事实上体现着男性的强势。刘呐鸥作品中的男性在与女性的交往过程中,他们总是无意识的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着女性的形象。比如《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H在把“她”像手杖一般地从左腕搬过右腕的过程中体验到优雅、摩登和出风头。H在没有感到时间的有限之前,明显把“她”当做一个既可以向世人卖弄的招牌,又可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玩物。H对“她”的情爱欲求显然是从男性中心的立场上出发的。
两性之网中的女性在情爱上则表现出决绝的姿态。她们大多不像男性希望性爱与情爱的合一,也不希求情爱的神圣与纯真。在两性交往中,她们很少被动的皈依于男性,也很少把自己看作男人的附属品,也很少置身于男人编织的情爱网中。她们大多能摆脱传统情爱观念的束缚,大胆、开放和肆无忌惮地追求性爱的满足。她们不再是男人眼中纯美和忠诚的女人,也不再因情爱的神圣而降低性爱生活的质量。刘呐鸥笔下的都市女性和男性相比,她们看重肉身,轻视灵魂;重视性爱,轻视情爱。从对待性爱与情爱的态度可以看出,刘呐鸥笔下的女性要比男性更现代一些,她们身上的现代因子更多一些。她们表现出与男性不同的情爱观。
作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创始人和中国都市文学的开创者,刘呐鸥以新奇的眼光打量着都市和都市中的男男女女,他的小说书写出女性对性爱的迷恋与崇拜,对情爱的鄙夷与抛弃;也也书写出男性对性爱的把玩与依附,对情爱的向往与尊重,传达出同为都市人的男性与女性不同的性爱与情爱感应。
注释:
[1][2]吴福辉:《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3][4]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8页、第207页。
[5]李俊国:《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谭华 贵州都匀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 558000)
-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的其它文章
- 古典诗歌中的绘美二法
- 敦煌文研究综述
- 《惜诵》发微
- 军礼与《诗经》战争诗
- 蝉联对比,因果不爽
- 爱情与婚姻的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