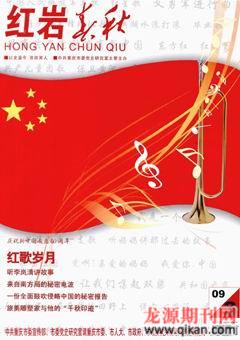日本留学拾掇
何 林
时间像捐失的流沙,转眼间离2005年留学日本已经四年有余了。现今,中日关系已基本步出四年前的困局。回眸四年前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不由感慨时空变迁。然岁月的穿梭却又让往昔的记忆清晰起来。

感悟导师
先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朴实,学术味十足。在东京大学校园一隅的不足五平米却堆满线装书的小屋内,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由于自己主修中日关系,东大校方为我安排了三谷博先生作为在日本研修的导师。校方在通知三谷博老师为我在东大的导师之前,并没有告知他的完全身份,以至于我后来回北京后才知道三谷博先生是东大乃至亚洲知名的历史学家,是《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的大作者。
我和先生的师生情谊就在懵懵懂懂中开始了。时而英语,时而日语的交流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尽管从我居住的地方到东大乘坐地铁也要一个小时左右,但应该说我是期待每周三次同他的两小时见面的。说实话,其实不全是为了聆听历史的教诲,部分原因却是因为三谷博老师把我们每次的见面都选在了东大附近的一间小酒吧内。炎炎夏日里,舒适的凉风,惬意的咖啡,老师不熟练的英语和我结结巴巴的日语恐怕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吧。
与三谷博老师的交流,在学术方面多已不记得了。但老师对于中日历史认识之争的精辟见解却让我受益匪浅。记得我们聊两国的历史问题,聊中日两国间的外交,聊中日的合作与斗争。我们之间观点自然有一定的差异,其中也有激烈的争辩,但没想到最后我们往往达成共识:中日两国必须合作,合则利,斗则伤。老师是一个坦诚的人,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自己对发展中日关系是一个中间主义者,既不激进也不保守。他的谈话透露出他对当时日本领导人缺乏战略大局观的忧心忡忡。作为一名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他对自己国家有深沉的爱和自己的维护。他把自己对国家的爱,融入到对19世纪日本历史孜孜不倦的研究中;把自己对国家的维护,放入对浩若星海的历史资料的考证中,让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历史对于老师而言已不再冰冷和尘封,而是寻觅与责任。如果说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东西的话,我想老师对于自己祖国的那份责任和以历史为方法探寻现实,是我得到的最大的财富。

数月以后,和老师在东京的最后一次见面,老师选择了东大附近的一间小酒屋,生鱼片、清酒,数月下来结成的情谊已让我们在席间忘记一切争辩。老师聊他的家庭,一个人的他选择终生与他那满屋子的线装书为伴了。两人的酒宴,最后的结局就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步出居酒屋,我们俩不免踉跄。攀上地铁,离别时的场景至今还记得,挥手、告别,相约中国再见!
后来,老师到北京出席2006年的“北京论坛”,我又与他见面,并力邀他在北大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那时以后直到现在,老师很忙,便再也没有见面……
对话驻日公使
在日本的时候,因为研究的需要,通过国内外交部的朋友联系了时任驻日公使程永华先生,相约北大的几位同学
一起去向他请教。程先生很谦和,满口答应。
程永华先生在长春外国语学校毕业后,就通过外交部的选拔考试直接被国家送到日本留学。当时是1973年,因此他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第一代留日学生。而这批学生在国内动乱的情况下之所以获得了留学的機会,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对日语人才的迫切需要所致,其间经过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因此,程先生也可以算动乱年代在周总理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了。大学毕业后程先生就直接进入了中国驻日使馆工作,除去其中奉调回国任领导人翻译及亚洲司副司长等职位的时间,当时他在驻日使馆已经工作了整整21年了。
程先生讲述的中日关系句句经典,然最深刻的是他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预判。当时由于小泉首相固执参拜使得中日政治交流特别是高层政治往来表现得十分冷淡。因此,我们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担心小泉的倒行逆施会对中日关系带来更大的影响。程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表示,他说,目前的态势与20世纪70年代佐藤荣作时代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当时中国方面的立场是“不以佐藤为对手”,直到佐藤下台、田中角荣上台,才开始积极与日本发展官方的政治往来,最后中日两国成功恢复邦交。
时过境迁,今天想来,程先生对中日外交的思考和判断依然让我折服不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啊!
在东京期间,我还参加了一场中国驻日大使馆举办的由一名日本女导演拍摄的纪录片发布会。这部纪录片反映了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研究遗留有毒化学试剂对东北居民带来伤害的史实。时任驻华大使王毅先生也即席发表了讲话。那位日本女导演直面历史的努力虽稍显单薄却让我敬意顿生。
直面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是当时触发中日国家关系出现停顿的症结。到了东京,作为研究中日外交的人,不能不去靖国神社探个究竟。
快到靖国神社,已经依稀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靖国神社的门口,高大的鸟居门旁,一块石碑上四个大字“靖国神社”赫然映入眼帘。沿着道路前行,路过挎刀昂首的神社创始人大村益次郎的雕像和一重再一重的鸟居门,即可看见拜殿。拜殿前低垂着巨幅的白色布幔,上饰四枚日本皇室的菊花徽记。巨大的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样帷幔包裹着拜殿,穿透一抹阴森,可见身穿白色传统服饰的神职人员的晃动。殿前,三两个人正双手合十,低头参拜。想要拿出相机拍摄拜殿里面的状况,却被禁止。
神社里的游人不多也不少,表面甚是平和宁静,与日本众多的神社似无二致。但表面的平和却掩饰不了隐隐透出的剑拔弩张。有一对建于1935年的石塔,塔身共有16块浮雕,描绘日本侵华的“丰功伟绩”,如侵占台湾、占领东北等,其中一幅绘有日本兵打开天津城门,日本军官持刀趾高气昂鱼贯而入的情景。靖国神社对历史的意淫可见一斑。
靖国神社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的描绘集中在拜殿旁的“游就馆”。游就馆是一个典型的军史纪念馆,完整记录了一个“帝国”的军队从弱小到强大乃至武功辉煌但终于失败的全过程。一面呈现着日本风物的静寂之美,一面供奉着铁血武士的夺命利器。这里摆放的是日本的所谓战争辉煌,没有丝毫的反省和自责。
游就馆里共11个展室,有一间展厅从天花到墙面布满了死亡军人的照片。一场又一场发生在别国土地上、其中大多数是在中国土地上的侵略战争,在这样颠倒黑白的历史记述中成了“靖国”战争。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变成了“进入”。解说词列举了日本是如何的资源短缺,比如当时日本的石油、铁、铜等只够维持多少天、多少个星期、多少个月,多么“无辜”的理由呵!展室里不同时期的亚洲地图上,勾勒出日本帝国的荣光,而我眼中只见亚洲人民的血光。在最后一间展室的几大本留言簿上,我看见一个英国人写道:“是否要在柏林建一个纳粹博物馆呢?别忘了你们杀了那么多人!”一个美国人写道:“我只是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为战争找到正当的理由。”但不少日文字体的留言,表达的则是对日本这段历史的“无上骄傲”。
走出游就馆,对“游就”二字唏嘘不已。“游就”二字来自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的劝学篇。“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意思是君子定居时一定要选择好的地方,外出交游一定要同有知识、有才能的人接近,用这种方法来防止邪恶的东西污染,从而接近真正的思想。荀子此句乃是期望人们“防邪僻而近中正”。然而何谓邪僻?何谓中正?在靖国神社的历史记述里却是那么的强词夺理、是非颠倒。游就馆祭出的两大主题:战争缘由归咎为苏联、美国、英国、甚至中国对日本的“压迫”,日本倒成了“受害者”;战争的目的,则解释为帮助亚洲摆脱白人殖民统治,实现“大东亚共荣”,日本倒成了“解放者”。战后一贯潜流于日本大众意识底层的所谓“正义的战争论”的民族情绪和经济大国日本的意识烟消云散后,在一定程度上收揽日本大众的“战争的光荣”的意识在靖国神社真是可窥一斑了。
但是,历史不是小姑娘,任人打扮得了的。
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难免会成为历史的弃儿。
现在,我由于工作关系对发生在二战期间日本对重庆的野蛮轰炸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时常在想,如果把“重庆大轰炸”的史实摆在那些仍然顽固坚持扭曲史观的人面前,看他们有何话说!
偶遇重庆饭店
一日,同几个同学一起去了大阪。路途不熟,终至天色已晚还在陌生的大阪街头徘徊。大阪的建筑很多是19世纪的老建筑,比较类似于上海的石库门建筑。我们一行人等早已饥肠辘辘,好不容易见到街边有一家小卖店,冲进店里准备买一打面包,情急之中居然直接用汉语与售货员交流,却听见标准的普通话回答。原来售货员小姐是在大阪留学的中国学生。
夜色中,原本想去大阪海滩的我们几人,居然瞎撞到了大阪的中华城——也就是“唐人街”了。中华城里,熟悉的各式吆喝声怎么也调动不起我们的购物欲望。在茫然中穿梭,突然眼前一亮,原来前方有一个“重庆饭店”,店名居然还是于右任先生所题。店里面富丽堂皇,却鲜有顾客。老板是个胖乎乎的女士,我尝试用重庆话与她沟通,她却不会说。于是我猜想,这不是一间真正的重庆饭店。惋然,走出饭店,抬头,一轮圆月透过薄薄的云雾依稀可见。那时在想,月亮还是故乡的明吧!
雨中岚山
2005年8月的一天,雨,淅淅沥沥。几个朋友相约来到岚山。岚山就在京都的近郊,这座山的名字连着中国的一位伟人,中日友好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周恩来总理。2005年,即使中日关系处于低潮时期,拜谒中国总理诗碑的游人却不少,还有一些日本的青少年。透过他们的谈话,可以明白感知他们对我们开国总理的景仰之情。
我走近,吟诵开国总理的诗——《雨中岚山》,无限豪迈、无尽思念……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觉愈娇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