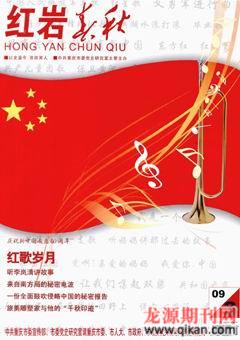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是与“两弹”亲密接触的日子
吴银强 唐 黎
提起中国的原子弹,大家都能想到钱学森、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等“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与原子弹有过亲密接触的热血青年。杭州老人吴银强就是其中的一位。自从他走出学堂之后就一直协助钱三强、邓稼先等研究“两弹一星”,并亲自参加了我国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
激情年代 青春不悔
1959年,我作为杭州市勇进中学(原省级重点中学)的高材生,考入了我的大学第一志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196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

九院在四川绵阳,是专门研究核武器的。军队编制,不穿军装。当时的院领导有邓稼先、王淦昌、陈能宽等人。因为保密,好多年后他们才显身扬名。九院下属有十几个研究所,分散在绵阳所辖三个县的各个角落。所与所之间,坐车要花上半天到一天时间。所与所之间联系工作要持介绍信、通行证,外出办事手续更麻烦。单位用代号,通讯地址只能写信箱编号。
进了九院,我被安排在一个研究所搞核辐射研究。这个研究所有几百号人,下设研究室、车间。研究室下设若干小组,每个组各干各的。别的组干什么,怎么干,不能打听。
我参与的研究工作是比较前沿的,要求很高。当时,超级大国早就在用计算机了,我们还在拉计算尺。所以,工作起来,我觉得自己学识太浅,脑子不够用。好在九院老师多,我随时可以请教。那些老师可不一般,比如王淦昌副院长,他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33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王淦昌一肚子学问,却没有半点架子,对我们这些小毛孩子非常和蔼。

我参加过三次核试验。其中一次是地爆,两次是塔爆,地点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每次核试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要求我们做到万无一失。核试验需要的器械、仪器大都是我们自行设计、工人师傅加工制造出来的。为了保证所有仪器在核爆后自动、准确运行,百分之百精确地拍摄、记录有关图像与数据,不出一丝一毫差错,每次去核试验基地,仪器的装箱、搬动、装上车,我都是自己动手,小心翼翼,生怕出什么意外。
要进行核试验了,我们便与外界中断联系,只能事先写信告诉家里这段时间有出差任务,请他们不要惦记。
我们坐军用专列从四川出发。专列到大站要重新编组,到兵站要补充给养,所以,走一段停一阵。途经宝鸡、兰州、天水、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七八天后到新疆吐鲁番。到吐鲁番后,我们再换坐军用卡车翻过天山去南疆。

天山,顾名思义应该是高耸入云、美丽壮观。汽车爬上天山,我放眼四望,上不见飞鸟下不见寸草,一点生命的气息都没有。空旷、荒凉、静寂,如同上了月球。这一路花了一天时间,我们才到达了核试验基地司令部的所在地马兰村。
马兰村在罗布泊边缘,有树有水有人烟,是个小小的绿洲。第一次到马兰,我眼睛一亮,哇,世外桃源!听说现在马兰村已经对外开放了,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核试验场设在罗布泊深处。罗布泊蒙古语为“罗布淖尔”,意思是“多水汇集的湖泊”。这里原是塔里木河的终点湖。沧海桑田,严寒酷暑、经岁狂风,将曾经碧波荡漾的罗布泊侵蚀得水断湖干,层层沙砾掩埋了昔日繁荣的楼兰古都、热闹的通商要道,罗布泊成了广袤无垠的洼地。支离破碎的盐渍地上堆积着沙砾、雅丹,还有虚幻的瞬息万变的海市蜃楼。罗布泊气候恶劣,年降水量少于10毫米,而蒸发量却在3000毫米以上,是中国最干涸的不毛之地。
1962年2月,羅布泊地区被划为军事禁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布泊便成了“蘑菇云”升起的地方。充满奥秘的罗布泊又增添了一层神奇色彩。
从马兰村到核试验场有好长一段路,汽车还要跑上一整天。开始的一段路工兵同志修过,还算路,再往里面走就没有路了。浩瀚旷野,长长的车队满载着人员、仪器、小动物、帐篷被褥等用具以及各种食物,浩浩荡荡地往罗布泊深处开进,非常壮观。然而,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上面左歪右斜地摇晃,像喝醉酒似的,颠得人头痛脑裂、骨头散架,车轮扬起的松散沙尘久久弥漫,真是“平沙莽莽黄入天”。我们年轻人都觉得不堪忍受,何况邓稼先等上了年纪的老科学家们。
所谓核试验场,是一片略有起伏的砂砾地,因为干涸而呈一片黄垩色。我估计远古时代这里是河滩,要不,哪里来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砾石呢?
到了目的地,大家分头做临爆准备工作。我们组在确定地点进行仪器的安装调试。调试到预定要求后,至少还要测试、联试三次以上,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反反复复地调试仪器,神经高度紧张。
冬天,这里的气温低到零下三四十度,寒风怒号,飞沙走石。我们穿皮大衣戴皮帽子在野外作业,单薄得像一片小树叶。有时暴风来了,刮得人站立不稳,连呼吸都困难。工作的那种难度、强度,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想象不出来的。
试验场有几处临时搭的简易房,如果人多住不下就住帐篷。我们的伙食当时是最高标准,大米饭、馒头,大鱼大肉管够,不收钱也不要粮票,这里饱含着全国人民的期望和支援。在生活上领导和我们一样,邓稼先院长同我们一起,吃的是一个锅里饭,睡的是同样的铺。他白天带领我们忙碌,晚上有时间便与我们聊聊天,下盘棋或甩把扑克牌,调节一下紧绷的神经。风小的时候,晚上放电影,大家便背着风,头顶星星月亮,坐在旷野沙石上,翻来覆去地看《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
准备工作就绪。核爆的前一天,全体人员撤离现场,集中到距离试验区70公里以外的地方,每人发一个把光线强度减弱一万倍的黑墨镜戴上,观看核试验。核爆炸产生的光辐射很强。如果不戴眼镜,眼睛就瞎了,这叫“闪光盲”。有一位同志忍不住好奇心,把眼镜拿了一下,刹那间眼睛就坏了,并且永远治不好。
原子弹爆炸了。戴上墨镜,我先看到一个大亮球,十几秒钟后,传来了轰隆隆的巨响。因为音速比光速慢,这跟我们先看到闪电后听到雷鸣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时,蘑菇云升了起来。紧接着,原子弹爆炸后的冲击波来了,气浪热乎乎,每个人都感到被推了一把。据说这时核爆炸的灰尘日本上空也能测到。
原子弹是利用铀原子分裂产生巨大能量,它用黄色炸药引爆。而氢弹爆炸是热核聚变,引爆所需的温度只有原子弹爆炸才能达到,释放的能量比原子弹爆炸强多了。氢弹爆炸后,空中马上出现一个沸腾的火球,像太阳似的。在热辐射和冲击波的共同作用下,试验区内坦克、装甲车、钢筋水泥建筑物顷刻被摧毁。
爆炸后要过两三天,才允许我们穿上特制的防化服进入现场收取试验结果。这两天我们觉得特别漫长,让人等得焦心,睡不安稳吃不下。纵然我们准备工作精益求精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但到关键时刻仪器还是可能会莫名其妙地出毛病,有时线路突然不通了,有时开关没有自动打开,有时与爆炸不同步等等。准备了几年就是为了这一刻,心里总念叨着:千万千万别出差错啊!每次爆炸一结束,就有同志急不可耐地要去现场取测试结果,但进试验区越早,危险性越大。因此,未经批准,谁也不准擅自行动,我们只好忍耐着,等待进场命令。
试验完毕,我们就拔寨撤退了。长长的车队载着人员物资原路颠回马兰村,再辗转回到四川。这样一去一回总要超过一个半月的时间。
蹉跎岁月皆成珠玑
与原子弹、氢弹亲密接触的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平常人。从哈军工毕业到九院,我已是大龄青年,男大当婚。可是,我所在的单位很封闭,与外界没有来往,女青年又特别少,我们这些小字辈技术员的婚姻问题就成了老大难。虽然经济条件不差,长相也不赖,可是,那阵子成千上万的城市知青下乡、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城市姑娘一听是在山沟里的“保密单位”,又是臭老九,掉头就走。
后来,经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哈尔滨姑娘。我利用探亲假与她见了面,交谈了一下,双方没有意见,事情就定了。我们的恋爱刻板得像解方程式,没有一丁点儿浪漫,婚后生活也是两地分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臭老九翻身了。解决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因我爱人不适应四川的气候,调她到四川工作不好安排。无奈之下我便打了个报告,要求调到哈尔滨,解决一家三口分居三地的困窘。九院的门一向关得紧紧的,我的报告送上去一年后竟批下来了,老同事说我是“从门缝里钻出去的”。
回到哈尔滨,两口子是团聚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没房住!我调入的科研单位,十年动乱,欠帐太多。知识分子成堆,困难也成堆,新来乍到的不可能分配住房。我们两口子住哪呢?我们就白天上班,晚上等我爱人工作的照相馆关门后,在照相馆的摄影室里搭起床、铺上被褥睡觉。这样狼狈不堪的日子我们整整熬了两年多。
因为没有住房,儿子不能自己带,只有请我父母帮忙,可苦了他们。但他们理解我,知道我是在报效国家。因为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儿子小时候不认识我,对我不亲。可孩子慢慢长大了,理解了爹妈的难处。他很懂事,学习好,自理能力也很强,现在工作已经小有成绩了,令我欣慰。
从九院离开时,我带回了很多专业书,因为住房问题没解决而没地方搁置,只能放在朋友家的煤杂棚里,时间一长,书全都受潮霉烂了。书烂了,人也改行了。
我很爱原子工程专业。我的特长、性格挺适合做科研工作,也渴望在核能研究上干出点名堂。离开九院前,我犹豫过、痛苦过,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人民的安宁而从事核试验是神圣而光荣的。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与原子弹、氢弹亲密接触的日子,我认为值!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又调入杭州市级机关,改行搞物价工作。我文理不偏,兴趣广泛,虽然物价工作与原子弹风马牛不相及,但我很快调整过来了。物价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搞原子弹的人搞物价,也算是军工转民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