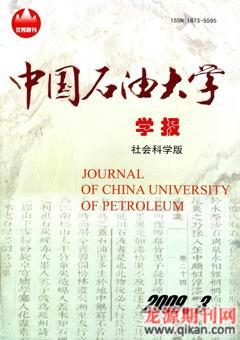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思潮及其启示
董雪梅 张丽昙 程玲娟
[摘 要]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其理论因子来源于“中体西用”论以及国粹主义思想体系。出于时代的焦虑和“西方的没落”,东方文化思潮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应运而起。它主张以东方文化之长解西方文化之弊,力图为中国寻求一条超越西方模式的健全的近代化道路。虽然东方文化思潮有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但它在谋求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的转型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宝贵的贡献,对当前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东方文化;现代化;思潮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09)03-0062-(05)
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是与当时的反传统主义的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鼎足而立的主要文化思潮之一。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汗牛充栋的显学局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关于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的研究在学术界却长期受到冷落,这方面的论文或论著相对较少。学界对于东方文化思潮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该思潮的理论端点、兴起原因、代表人物、主要观点及发展脉络尚缺乏系统的梳理,尤其是该思潮与其他社会思潮如西化思潮、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关系尚需多角度的深入研究。由于这一思潮本身有着内在的理论缺陷,且其文化设想在操作上的难度有违于当时急于求成的社会心理,而它所使用的古奥怪僻的术语和艰深晦涩的文字亦不适合当时激进青年人的胃口,从而决定了该思潮的坎坷命运。但作为一种历久不衰、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其关于文化建设的某些方案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道路的
探索仍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东方文化思潮的思想因子及理论来源
所谓“东方文化思潮”,一般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西化、提倡东方文化,主张在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新旧调和、中西调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及其后继者钱智修、作者陈嘉异,《甲寅》主编主撰章士钊,东南大学教授吴宓,以及《欧游心影路》作者梁启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者梁漱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玄学派主将张君劢等著名学者,这些学者被称为东方文化派。与“国粹派”和“孔教派”不同,东方文化派一般出身新学,不少人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就是未出过国门的人,受的也是新式教育。因此,他们除运用传统理论提供的武器来护卫过去的传统,更注重用西方现代的研究方法,从哲学和文化层次上去建构自己保守主义的文化理论。《东方杂志》、《甲寅》、《学衡》等杂志是该学派主要阵地。《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办(1904—1948),主编杜亚泉及其后继者钱智修、陈嘉异等以《东方杂志》为阵地批评新文化运动,宣传文化保守主义。1921年,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打出“东方化”和“新孔学”的旗帜。1922年1月,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并以此为平台, 聚集了一批学界名流。1925年,章士钊创办《甲寅》,成为反对西化,倡导东方文化的又一阵地。
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思潮的理论肇端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19世纪中叶,在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华帝国国门的同时,西方文化也发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本土文化面临着生存危机。这一形势强烈震撼了当时的有识之士,为了应对这场挑战与危机,思想界的探索很快就超越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面而上升到政治制度层面,继而又深入到对东西文化进行全面比较以求得救世治弊的良策。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明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这一主张可谓“中体西用”论的雏形。到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这个口号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发挥,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次努力结合。
“中体西用”论以其对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明确的处理而成为当时知识界的流行语,以至于举国上下都把它当作至理名言。显然,这一命题强调以传统政治秩序为体,以西政、西艺、西史为用,即在维护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力图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进行有机结合,以创造出一种适宜于中国需要的“新文化”。可以说其折衷调和的理论特色给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定下了理论基调。“中体西用”论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主从关系的立场显然是东方文化思潮关于吸取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实现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中西文化调和互补主张的理论因子。据此,“中体西用”论可谓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思潮的理论端点。有意思的是,东方文化派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又猛烈抨击其弊端,主张“全盘承受”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同时,“又批评地重新把中国原来态度拿出来”[2]432。这里表现出了一种对西方文化“欲迎还拒”的矛盾心态,它和“体用派”为保“中体”而采“西学”时所表现出的矛盾心态有某种相似。
国粹主义是东方文化思潮的主要思想资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对“体用论”发出质疑,并提出了一套独到的见解,被称为“国粹”派。 “国粹”派认为国粹是一种“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而这种精神蕴涵于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文学遗产中。“国粹”派高扬“国粹”大旗,对崇洋媚外醉心欧化倾向进行了坚决批判,主张“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决心“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国粹主义者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时,既主张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又不盲目排斥西方文化,认为中西文化不仅可以不相妨碍,而且可以相互会通,相得益彰。同时,他们还对西方文明的弊病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种在批判传统文化基础上学习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文化发展思路,对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思潮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二、东方文化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及条件
东方文化思潮的兴起与一定的社会背景及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但是,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假共和之名,行独裁专制之实,还亲自导演了一场帝制复辟的闹剧。之后的北洋军阀为争夺权力,连年混战,国家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严重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危机使中国思想界陷入了迷惘:民主政治为什么失败,救时济弊的良方何在?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焦虑和困扰,而其结果之一就是东方文化派的出现。
当时,陈独秀、胡适、吴虞、钱玄同等新文化知识分子以涤荡专制余威,宣扬民主、科学为主旨,对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陈独秀等人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革命仅仅停留在社会政治的表层,而未能触及伦理道德,即人的精神层面,要实现这种“伦理的觉悟”,就必须发动一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运动。与此相反,杜亚泉等人则认为不是因为辛亥革命没有触及伦理道德,而是由于西方物质文明和“权利竞争”学说的输入,造成了社会伦理道德的普遍失范。更有甚者,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为了“警世醒民”,甚至以自杀的方式对当时社会的道德沦丧表示抗议。杜亚泉再三强调,道德为救国之良剂,必须高扬道德传统,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救世良方。
五四激进派不仅认为传统文化要为民主政治的失败负责,而且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孟儒学还为帝制复辟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的“孔教会”极力鼓吹尊孔读经,还参与帝制复辟),因此,他们从1916年开始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抨击孔孟儒学,特别是纲常名教和伦理道德的文章,到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和吴虞写出《吃人的礼教》时,这种抨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谓物极必反,文化激进主义“极”,则文化保守主义生。这种激烈的反传统行为不仅遭到了以纲常名教为“立国之本”的顽固守旧人士的反对,也引起了梁启超、杜亚泉、张君劢、梁漱溟等对传统文化怀有深厚感情并且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救世良方的知识分子的深刻不满,与激进派的反传统和要求“西化”相反,东方文化派主张批判地认同传统,高扬东方文化的旗帜,宣称未来的世界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如果说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是杜亚泉等认同传统文化的现实依据,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引发的西方文明危机,则为其主张“东方化”提供了时代契机。延续5年之久的“一战”及其造成的空前的物质灾难和精神失落,诱发了世界范围的文化大反省。在西方,注重生命与直觉的哲学思潮和柏格森主义,主张返回宗教道德的新托马斯主义,以及强调自我意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等,都应运而生。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大战期间完成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在战后引起轰动,它宣布了欧洲中心论的破灭。既然西方文明已经“没落”,那么只有靠“东方文化”来拯救,因而当时出现了一股世界性的“东方文化救世”思潮。许多西方学者如杜威、罗素等都将中国视为“世外桃源”,来寻觅失落的感情和匡救西方文化的灵丹妙药。
在中国,“西方的没落”使一些长期对西方文化羡慕不已的人开始怀疑西方文明。杜亚泉说:“近年以来,吾国人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3]1梁启超号召中国青年以“孔老墨三大圣”和“东方文化”去拯救西方:“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4]梁漱溟于1918年前后称“看着西洋人可怜”,“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如果说时代的焦虑是东方文化思潮产生的内在原因,那么“西方的没落”则是其兴起的外部诱发因素。
三、东方文化派之主张
东方文化派在与西化派的文化论争中,逐渐发展起东方文化思潮,其理论要点如下。
首先,关于东西文化差异的性质问题。东方文化派反对西化派把东西文化的差异视为“古今之别”,指出二者“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实质上是“中外之异”。1916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撰文对中西社会及其差异作了对比,认为其差异不外“动”与“静”的区别。他写道“综而言之,则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发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发生静的文明。”[3]4梁漱溟也从“中外类型”的区别上对东西文化的差异作了比较。与杜亚泉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东西文化之根本区别在于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西方走的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一文化路向”,东方的中国和印度分别走的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第二文化路向和“以意欲反身向后面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三文化路向。[2]406-407除此以外,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则强调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
其次,关于新旧文化的关系问题。东方文化派反对将东西文化的类型之别视为新旧之别,反对西化派把传统文化说成是“旧文化”,把西方文化说成是“新文化”,反对“破旧立新”或“弃旧图新”的观点,反对西化派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和批判,而强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继承。他们认为新旧是一个历史范畴,其涵义因时、因地和内容的变化而异,“昨日为新,今日则旧”。吴宓称“旧之有物,增之损之,修之琢之,改之补之,乃成新器”。.①他们认为,文化演进是一个由新而旧、由旧而新的递嬗过程,新旧不能彻底分开。杜亚泉提倡所谓的“接续主义”:盖接续云者,以旧业与新业相许之谓也,往过者,来者续,接续者如斯而已。他们一再强调没有旧,就没有新,唯有旧,才能生出新,强调新旧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承认事物在矛盾斗争基础上的发展,不承认文化发展的间断性,甚至否认“新旧“之间有质的规定性,认为所谓新旧不过是程度问题。
再次,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问题。东西文化差异之比、新旧文化关系争论的目的是为了选择中国的文化出路。西化派认为西方近代文化是优于中国固有文化的新文化,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西方化”。东方文化派则认为,虽然西方成就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但精神生活却十分贫乏,中国正好相反,精神生活丰富而物质文明相当落后。基于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东方文化派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固守传统,而是“一面迎新,一面复旧”,取西方文化之长,补中国文化之短,实现中西文化折衷调和以求东方文化世界化的目的。梁启超指出,可以引进西洋人研究中国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把我们的文化综合起来,若有不足,就把外国文化拿来,起化合作用,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系统,把这个新的文化系统向外扩充,让它对世界文化发生影响,即使东方文化世界化。杜亚泉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一面“统整吾国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一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西洋之断片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国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5]梁漱溟虽然在理论上赞同陈独秀等新旧不可调和的观点,但实际上也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主体的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
四、东方文化思潮的理论特征
其一是鲜明的民族立场与深切的忧患意识。19世纪末,法国学者拉克伯里以当时欧洲考古界对近东地区的挖掘成果为依据,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的新观点。新观点传入中国之初,很快得到国人的认同。但到五四前后,拉克伯里的中国文化“西化说”遭到国人的批评,其中尤以东方文化派最为激烈。梁启超、柳诒徵、缪风林、陈嘉异等人分别在《学衡》、《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强调“西来说”并无确凿证据,不足为信。东方文化派引用最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批驳“西来说”不确,并鲜明地提出中国文化为“独立的”、“自创的”观点。东方文化派运用在欧美兴起的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强调中西文化之间并无直接的源流关系,它们属于不同起源、各自独立发展的两个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完全是在中国本土内由中华民族独立创造的。东方文化派的观点否定了西方文化中心论,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立价值,它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已经被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学证明是十分正确的。东方文化思潮可谓中西文化危机的产物,是东方文化派对中国文化出路的一种选择。“东方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振兴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选择一条强国富民的文化出路,所以民族立场与忧患意识可谓其最基本的理论特征。
其二是东方文化优越感。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东方文化派先驱者杜亚泉就以“静”和“动”来概括东西文化的不同类型。20世纪初少数国粹派知识分子以“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来概括中西文化的特点,之后孙中山、李大钊等人也有过这样的表述,在五四前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不仅成了东方文化派的口头禅,而且也成为东方文化派提倡“中国文化复兴”和世界文化“东方化”的主要理论依据。在他们看来,以精神文明为其特色的中国文化,其价值要大大高过以物质文明为其特色的西方文明。中国文明重艺术、情意与内心世界的修养,西方文明重科学、理智与外在世界的征服。前者是一种“超官觉(感觉)主义”的文化,而后者则是一种“纯官觉(感觉)主义”的文化。[6]东方文化派的这些论点显然是荒谬的。梁漱溟当时主张全世界都走“第二路的路向”,梁启超也强调“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陈嘉异等人更是提出“中国之新命”的说法,凡此种种形成了东方文化派“拯救西方”的观点。东方文化派是怀着东方文化优越感来主张中国文明统整融合西洋文明的。最具东方文化优越感的梁漱溟提出“全盘承受”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又将其态度“根本改过”,即“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2]432。这实质上就是将“中国原来的态度”和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进行调和,以促进世界文化“东方化”。总之,东方文化优越感与文化调和模式的统一,是东方文化思潮另一显著特征。
其三是高扬人文精神,反对科学主义。东方文化派与西化派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迎拒民主科学,而在于崇废科学主义。梁启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欧洲人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过于相信“科学万能”。“玄学(人生观)与科学”论战为东方文化派的反科学主义提供了绝好的讲台。张君劢认为,世界分为两个真实的领域,一是自然,二是人事。科学讲究理性分析,确实可以提供自然知识的钥匙,但是人生的问题不能仅用(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科学无论如何的发达,人生观问题的解决,还是只有靠人类自身,因为人生观的特点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第一性的,这就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此论抛出后,张君劢立即遭到丁文江、胡适等的口诛笔伐,被说成是“玄学鬼附身”。梁漱溟对那种早已逾越本份的科学概念,也深感不安。他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在其方法不在其所得结果,科学绝不能与哲学(玄学)混为一谈,因为对人的情感、意欲等内心生活的把握只能靠“玄学”的“直觉”而非科学的“理智”。包括梁漱溟在内的东方文化派都相信直觉,他们坚信,惟有直觉体认的方式,才能引导人们去体会内在世界的精神要义。而这一条,正是中国文化所高扬的人文主义的根本价值所在。
五、对当前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东方文化思潮代表着当时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失范的情况下对中国文化出路的一种选择,而且它在谋求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的转型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探索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剖析这份遗产,从中汲取有益于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首先,对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确立珍视传统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在当年近代化过程中发生传统与近代冲撞时,东方文化派反对西化派激烈反传统的态度,并认为对传统的认同与回归是近代化所不可须臾离开的历史基础。东方文化派认为,传统文化是先民长期积累的结果,对于“保守固有之文明”,应该持一种“积极之肯定对答”的态度,而不是弃之如稻草。考虑到“一国有一国之特性,则一国亦自有之文明,取他人之长,以补吾之所短,可也;乞他人所余,而弃吾之所有,不可也。”[7]东方文化派强调传统、维护传统,并没有不加区分、不加分析地全盘维护传统。对抹杀人性的纲常礼教他们都作过深刻批判,他们所认同和弘扬的主要是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具有超时空价值的部分。这些部分绝不会因近代化的兴起而失去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东方文化派来说,挖掘传统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使之成为新文化所赖以扎根的丰厚的土壤,是他们的共识。学者费孝通说,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能空地上造好新型式,然后搬进来应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新的得在旧的上边改出来。很明显,这与东方文化派在传统与近代化关系的看法上可以说是基本相通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东方文化派传统观的理论意义。今天看来,完全抛弃传统的现代化,只能是水中捞月,沙上建塔。
其次,对于现代化过程本质的分析也富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东方文化派在承认科技进步是近代化基本内容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了近代化本质的另一面:物质的丰富并不能替代精神的满足,心性人伦也不应成为科技进步的牺牲品,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应该在近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并以其关系的协调和谐来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协调和谐。换言之,科学技术和心性人伦的共同进化,才是人类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全部本质。循此思路,东方文化派反对西化派为实现近代化而抛弃传统,实行西化的主张。他们认为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近代转型。他们相信,惟有用心性人伦的完善,才能去救助西方近代化进程中发生的片面追求科技进步而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力图为中国寻求一条超越西方模式的健全的近代化道路。在当今的现代化进程中,科学和技术往往被认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途径和重要工具。基于此,人们往往侧重于人对自然的征服,而疏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侧重于人与人的竞争而疏于人与人的关顾。因此,东方文化派的思想理论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现代化过程的本质。
再次,对于解决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问题有巨大的借鉴价值。东方文化派提出的“中国文化独创”说、“中国精神文明”说、“世界文化三路向”说,着力揭示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优长,显示了其在文化民族性问题上的建树。但是,东方文化思潮的根本理论缺陷,在于没有理顺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关系,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文化的近代化道路问题。实际上,文化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集合体。就时代性而言,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有进步落后之分,而就民族性来说,则没有什么优劣高下之别,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东方文化派只看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征,以民族性否认时代性,从而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化形态。在中西文化比较时,他们认为中国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中国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拒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这种错误认识使他们不可能对中国文化的出路作出完全正确的选择。
西化派错误地将“西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而东方文化派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他们痛感西方近代化进程中由于片面追求科技进步而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力图寻找一条超越西方模式的健全的有民族特色的近代化道路,这种愿望固然是无限美好的。但由于他们没有理顺东西新旧文化的关系,错误地得出了中国的近代化只能是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加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这从理论上看,似乎可以成为实现其美好愿望的理想途径,但从实践意义上检验,却毫无可操作性。因为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仁义礼智、内圣外王、知足寡欲、乐天知命,以及他们所标榜的“孔老墨三大圣”、儒家人生态度、儒家精神等传统因素,尽管仍在顽强地作用于近代化的社会,至今仍有一定的存在价值,但它已不再是古代历史条件下的原本意义,原本形态上的传统了。所以,东方文化派虽然找出了实现其美好愿望的“理想途径”,但却因他们对传统文化作了抽象的、超时空的理解和诠释而最终不得不陷入失望之中。
东方文化派的思想理论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新时期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文化的一元与多元、整体性与可分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走综合创新之路,以便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桂芬.采西学议[M]//郑振铎.晚清文选.上海:上海书店,1987:105-106.
[2]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 伧父(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J].东方杂志,1916,13(10).
[4]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74.
[5] 伧父(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1918,15(4):6-7.
[6] 杨思信.东方文化派的中国文化观及其特色[J].兰州铁道学院学报,2002(5):19.
[7] 高劳.现代文明之弱点[J].东方杂志,1912,9(11):2.
注释:
①参见吴宓所著《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
[责任编辑:王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