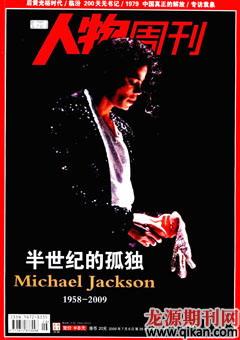电光倒影
做个聪明的小丑
埃塞俄比亚有句谚语,“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默默地放屁。”60年来,从餐桌围炉,到手机网络,讥讽、调侃政治人物的笑话,粮食断绝时也从未断绝。但在舞台上,钱越多,赵本山们就越嘲讽弱者不嘲讽强者。范伟们就只忽悠江湖,不指向庙堂。郭德纲们也只贬低道德,不贬低政治。他们不是小丑,而是在努力扮演一个蹩脚的小丑。滑稽列传写到现在,实在写不下去。马季先生当年说“宇宙牌香烟”,还带着一股启蒙时代风尘仆仆的味。略微结合了天桥上的相声和西方的talk show,一炮而红,也一炮而猝。先生去世后好事者作“滑稽列传之马季列传”,其中两句令我扼腕:“然季之术讽刺者寡,而颂扬者多,沉积既久,渐亦为人所轻。季显知时移势迁,非独力堪支,遂乃垂钓京师之北,退求一己之安逸。”
上海滑稽演员周立波,久已离开舞台。他弟兄劝他复出,一起看了香港的talk show节目“栋笃笑”。许冠文和黄子华,每天在电视上嘲讽时政人物,惟妙惟肖,优雅的刻薄大有英伦之风。尚未成为特首的曾荫权,坐在下面,脸上阴晴不定,手上使劲鼓掌。周立波看了说,其实我能做得更好。于是有了今年红遍上海滩、一票难求的“笑侃三十年”。
虽然段子参差不齐,但分头调侃布什和温家宝被扔鞋典故,立场褒贬不定,风格庄谐不分,脸上要笑不笑,首开了这个国家60年来小丑戏仿领袖之先河。其他瑕疵都不重要,周立波说,他的“海派清口”的特点,就是关注时事。制片人说,只要我们避开政治、宗教的敏感话题就没问题。这是古人的滑稽列传绝种多年后在上海的复燃。上海的正副市长,也效法曾荫权看“栋笃笑”去美琪大戏院听清口。周立波不是用上海话,而是用对现实的嘲讽,尝试将自己与当代所有笑星,区分开来。
小丑的任务就是在台上放屁,虽然放得还不够响。但这恰好也是中国滑稽列传和英美talk show的差异。“滑稽”的原意是指转壶吐酒,一泻而下,不中断,不梗阻。可以有两重解释,一是出口成章,应对自如;二是言论自由,不阉割,不屏蔽。所以针对滑稽这个词,也有两种口若悬河,一种是言论自由的产物,一种是言论不自由的帮凶。
上海学者李天纲说,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周立波不能不谈政治。但就如齐国的淳于髡、楚国的优孟、慈禧跟前的刘赶三,谈政治要有小丑的聪明,先唾面自干,谁要和小丑较真,就不是一个民主问题,而是一个智商问题。我很小就看过刘赶三的故事。说他在台上演皇帝,瞥见光绪站在慈禧背后,就拖足腔调,指着光绪说:“我这个假皇帝还有座儿呢,你这个真皇帝啊,连个座儿都没有。”全场吓得大气不出,过了一万年,慈禧才慢悠悠地说,“给皇帝摆个座儿吧。”
自古只有滑稽演员,有这个特权。所以当了笑星不放屁,就如蹲着茅坑不拉屎,都极不仗义,因为直言批评风险实在更大。当年邓拓在《燕山夜话》中说,有次京城干旱,皇帝问为何郊区有雨都城无雨。一个叫申渐高的弄臣答曰,“雨怕抽税,不敢入城。”邓拓说,时代不同了,今天不需要拐弯抹角。说完,就进了牛棚。
周立波调侃上海的磁悬浮,说我们花了100亿,解决了30公里的交通难问题。随后就用招牌式的假严肃,夸奖政府眼光长远。周立波是个聪明的小丑。但这一路上,他还能走多远呢?若这时代称得上伟大,他的海派清口就有可能不像上海滑稽戏一样,“始于江湖,毁于庙堂”。
Talk show却是另一种传统,幽默之后依然直言,灵巧如蛇也锐利如刀,如旧约中先知的角色。和滑稽列传相比,是两种说话的极端。如大卫王害死了自己手下,娶了人家老婆。先知拿单来见他,先说一个故事:城里有一个富户、一个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羊,穷人除了一只小母羊羔,别无所有。有个客人来到富户家里,富户却舍不得杀自己的牛羊,去取了那穷人的羊羔,杀了给客人吃。大卫王听完大怒,说我指着神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于是先知一翻脸,指着君王的鼻子说,“这个人就是你。”
这就是先知和滑稽的区别。说到底,知识分子若不敢做先知,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小丑来赌一把?所以放下身段,欣赏周立波,笑侃30年的衣食住行,偶尔擦枪走火,放个响屁。你除了感恩,又能说什么?就如一家媒体说,人民已忘了先知是什么意思,人民需要周立波。
只是“清口”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清心、优雅,不自我贬低,二是自我阉割与审查。前者是剧场版,后者是删节版。当赵本山克隆出小沈阳后,周立波的走红,有望扭转当代小丑文化的方向,从嘲讽弱者转向嘲讽强者;从媚俗转向刺秦;从忽悠百姓转向针砭时弊;从央视的形式主义方言转向舞台的地方主义本位。
广大的民间,胜过周立波的大有人在。如西安作家狄马擅长搜罗未经删节的民歌,经他的陕西腔一唱,每每语惊四座。我爱狄马唱的一首情歌,这是自古以来不被庙堂污染的真正声音,幽默之中,有令人尊敬的价值观:
“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天上的星星成对对,人人都有个干妹妹。”这是前两段,狄马说,意思是男女相爱,天赋人权。
“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宁让皇上的江山乱,不要咱俩的关系断。”这是后两段。我说,意思是婚姻盟约,优先于一切垂直关系,也优先于国家大事。改革30年,开始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家庭复兴,现在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家庭衰败。可怜我们既缺乏聪明的小丑,更缺乏勇敢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