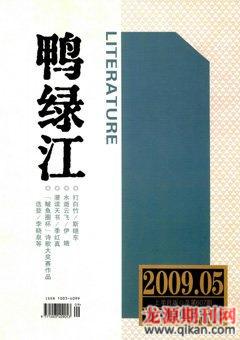肇事
李敬宇,男,1963年生于南京,现供职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在《中国作家》《花城》《清明》《长城》等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近九十万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转载。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
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的情形。
那天上午,我们接到一个电话,说二道街的南口发生了一起车祸。刘主任当即点着我的鼻子,说霞子你去,去采访一下。
又是车祸!我对车祸早已深恶痛绝。
腿脚支派脑袋,我不在乎;不能忍受的,是每天都要面对这些重复的事件。琐碎。无聊。乏味。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生活部,一个小记者,你不采访这个,又能采访什么?
我打车赶往出事地点。在赶去采访的路上,我想的就是这些。
但那天,在路上,我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吴星桥打来的。
吴星桥在电话里说,霞子,那天跟你讲的那个案子,死者家属又找来了,你上次说你可以帮忙的,你怎么帮?我说我正在路上呢,又要去采访一起交通肇事,法律方面我是外行,你自己看着办吧!吴星桥说,你那天还说你感兴趣呢,要和死者家属谈谈,帮我解脱,怎么又不感兴趣啦?我说兴趣和混饭吃相比,混饭吃更重要,我还是先完成刘主任交代的任务吧。
但是关了手机,我马上就意识到那起事件或许更有意思。我煞有介事地从包里掏出采访本,看了看一个礼拜前的记录——
吴星桥提供:去年八月,交通肇事。正乾路,晨练男子,斑马线上,当场死亡。认定司机全责。有期徒刑一年半。死者家属来交警大队闹事,理由,从刹车印迹看,向右拐,怀疑是故意谋杀。
我总是喜欢这样记录,快捷,简便,别人不一定能看得懂。
那一刻我很矛盾,我在考虑,我该不该听吴星桥的。从记者采访的角度看,吴星桥提供的线索也许一钱不值,也许价值很大,可不管怎么说,都比我们刘主任交代的任务有意思。但我同时又想,如果撇下公干,去吴星桥那儿,不用说,回单位以后肯定会遭到刘主任的一通狂批滥骂。
那天路上车辆很多,红灯也多。出租车司机是个老油子。前面是红灯,而且已经停了三辆汽车,他却轧黄线走反道,三档速度一溜烟超过去,直接开进路口,略一减速,绕过一辆横行的公交车,硬是从几辆自行车前面闯了过去。城市的各个路口,有的设了探头,有的没设,出租车司机摸得一清二楚。
老实说,我讨厌这样的司机,虽然急着赶路,我还是痛恨他们——这是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据说我们国家平均每小时就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坐在这样一个毫无安全感可言的出租车里,下一个重大车祸会不会锁定在我身上,难讲。
我当时想提醒司机别着急,开慢点,采访车祸,总不能在路上再出一次车祸。不过等我开口时,我说出的话却是:“对不起,请掉个头,去成惠街。”
司机猛踩一脚刹车,然后扭头问我,去成惠街干什么?瞧他在马路中间开车这么不规矩,我不想回答他的话,就带着点气,简略地说:“成惠街。交警大队。”
那天我去得还是迟了。当我赶到交警大队时,吴星桥提到的那几个家属,已经被他打发走了。吴星桥见了我,很诧异,说你不是说不来的吗,怎么还是来了?我说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比我要采访的交通肇事更有卖点,所以我决定赴你的约。吴星桥说,你们当记者的,一开口就是“卖点”,跟卖狗皮膏药差不多。我说我要是百万富翁,我就不干记者这个行当了,整天都是交通肇事,特没劲;不过你说的这件案子,可能是个例外。吴星桥说,你不会拿我身上的疤当成一朵花来欣赏吧?我说你身上的疤永远成不了花,你被死者家属穷追猛打,还值得我欣赏啊?
后来我和吴星桥又重温了一遍那件案子。
那起事件发生在去年夏天的某日早晨,六点半左右。在正乾路上,一辆小型货车由东向西行驶,撞上了一个晨练的男子,其时,该男子正准备过马路,被撞后当场死亡。男子是走在斑马线上的,所以交警大队在处理时,认定驾驶员观察不力,负全部责任。案件由公安局移送到检察院,再由检察院起诉到法院,结果,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该驾驶员有期徒刑一年半。然而事隔近一年,死者家属又找到交警大队来了,对案件的处理提出质疑,认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而是预谋杀人,是有人故意加害死者。此前,死者家属已经去了法院,法院的答复是,交警部门作出了责任认定,检察机关也是以交通肇事罪起诉的,法院以此为依据作出判决,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死者家属是郊区的乡下人,他们只抓住一个疑点,就是根据当时现场刹车的印迹来看,汽车在停下前,方向盘是向右打了个弯的——也就是说,出事的时候,汽车向右边的非机动车道拐了一点儿,正是这拐去的距离,致使死者不治身亡。
交通肇事的处理是吴星桥办的,所以死者家属理所当然地找了他。
“你认为,死者家属讲的理由,有道理吗?”我问吴星桥。
吴星桥的答复是:“事情都过去一年了,肇事现场也早已不存在了,你这话……叫我怎么回答?”
我说:“现场虽然没有了,可你们拍了照片,证据基本上固定了。”
吴星桥没答话,像一个闷瓜。所以我又说:“我考虑的是,如果死者家属所说的确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人家为什么要害他,又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
“你们记者考虑得就是比别人多,好像别人天生就比你们智商低似的。”吴星桥说,说得很不服气。
我开了一句玩笑,说别人智商低不低,我不知道,你吴星桥的智商肯定比我低。然后我说:“每一起车祸的背后,都会有一个或几个故事,你信不信?”
吴星桥的智商一下子就提高了,他说:“你这是废话!打个比方吧,飞机失事了,死了一百个人,我敢说,那至少有一百二十个故事等着我们去破译。”
随后,我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率性的决定,立刻动身,去郊区。
死者名叫欧贵,他的妻子叫严桂花,家里还有他的妹妹。讲明来意后,两个女人竟突兀地给我跪下了。我将她们拽起来,说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只是个记者,想了解一些情况。严桂花说她自己谈不好,官司是丈夫的本家叔叔欧凤德帮着打的。就去把欧凤德叫了来。欧凤德瘦瘦小小的,自我介绍说,是乡下的教书匠,文化不高,识得几个字。
欧凤德告诉我,欧贵在城区劳动局下属的一个服务公司工作,属于合同制工人,很能干,所以两年前提了科长。欧贵死后,单位通知家属去整理遗物,家属没有急着去,直到交通肇事的案子处理完了,才赶去。那些遗物,无非是书籍杂志,还有几件衣服。但是在一本书里,夹了一张字条,被欧凤德无意中发现了。那字条写的是:“我能要你的命,你信不信?”看了字条,他当时没敢声张,回来后才把这事告诉严桂花。严桂花一听此言,顿时手脚乱抖,吓蒙了。
我问欧凤德,字条还在吗?欧凤德说,在,我带在身上呢,我没敢给政法干部看,法院,检察院,交警大队,我都没给他们看,我怕事情张扬出去,不好办。
我说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吧。欧凤德审慎地看着我,然后才说,我也只有指望你了,我一个乡下教书匠,文化也不高,我能有什么办法?
那张字条被他夹进了一个塑料袋里,保管得很到位。打开来,果真是那些文字。只是字体过于稚嫩,蚕豆大的每个字,一笔一划,如小学生所写。我立刻作出判断,是用左手写的。欧凤德惊讶不已,显然他根本没有想到。我有点悲观,心想你还打官司呢,看你风风火火的样子,其实指望你,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我问他,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欧凤德说,看了这张条子,我就怀疑,可要我谈想法,我还真是谈不清,我不知道这张条子和车祸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但说到车祸的案子,欧凤德又信心十足了。他说交警大队拍的照片他看过了,连汽车的刹车印子都很清楚,是向右拐的,拐了五十七公分。如果不拐那五十七公分,欧贵就不可能被轧死。欧凤德说,现在找理由,别的也找不到,只能找这一个理由了。
那天从郊区回来,我有点失望。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下手。
理所当然地,我被我们刘主任狂批了一通。
我记得,批完之后,刘主任把我们几个记者叫到一起,反复不停地说,现场!你们懂什么叫现场吗?写新闻,就是要写出现场感来!
我把我去郊区的情况向他单独作了汇报,并征求他的意见。刘主任不屑一顾地说,现场!我还是强调这两个字!事情都过去一年了,早就馊了,哪儿还有现场感?
我通过我嫂子的妹妹娄芳,瞒着我们主任,独自去了区劳动局下属的服务公司。娄芳就在服务公司工作。娄芳是个直爽人,正是她在不经意间提供给我的那个信息,使我的这项近似子虚乌有的使命最终得以完成。而我去找她的时候,是不动声色的。所以在那时候,我的这项使命也可称之为秘密使命。
娄芳向我提供的信息是:欧贵曾经写过举报信,举报区劳动局前任局长马延,上面也来人调查过此事,但没有结果。为此,欧贵在单位把自己搞得很臭,人际关系很僵,连科长也被抹下来了。现如今,马局长已经提升为副区长了。
这是一条很有意思的线索。我之所以不说它“有价值”,是因为在当时,我还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价值。然后,我利用休息的时间,又赶到郊区,去乡下,去找死者的妻子严桂花,以及那个“教书匠”欧凤德。
这一次,我重点了解的是死者欧贵生前的生活习惯以及工作状况。
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了解到:欧贵在单位住单人宿舍,每个礼拜五晚上回郊区自己的家,礼拜天下午赶回单位;有早晨跑步锻炼身体的习惯;周一至周五,每天三顿饭都在单位解决;原系科长,后来被撤职了,听说是和领导过不去。
我说,我再问一个比较冷僻的问题,他早晨跑步,一般跑哪条路?严桂花说,这个我知道,有几次我进城,就住在他的宿舍里,他早晨起来,叫我跟他一起去锻炼,他一般是跑青年路到正乾路,再拐上一条什么路,然后回单位。
我问他们还知道什么,他们说别的就讲不上来了。我说那好,我暂时就向你们了解这么多。临出门,我又说,我还是那句话,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只是想打听一些情况,你们不能抱太大希望。
接下来,我又去找我的老同学吴星桥。我说星桥,现在该我给你布置任务了,这个任务不艰巨,但比较繁琐,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完成了。
我给吴星桥布置的任务是,通过交警部门的电子探头,查找以下时间及路段的车辆运行情况——
时间:去年五月至七月,每周一至周五的早晨,六点到七点之间。
路段:青年路、正乾路、虎卫街。
吴星桥说,都一年了,他们是不是保留一年前的记录,我就吃不准了,我去看看吧。
仅过了两天,吴星桥就带来了好消息。
“记录都在!你知道,我在调集资料的时候,发现什么了?”吴星桥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告诉你,重大发现!”
“一辆小货车,老是在那个时间段出现。”我平淡地说。
“你怎么知道?”吴星桥本来想叫我惊诧的,他自己却惊诧不已。
“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表情,不是全都告诉我了吗?”实际上我同样兴奋,我的兴奋绝不亚于吴星桥,但我成功地抑制住了,“我还能报出那辆汽车的车牌号,你信不信?AR430。”
“乖乖,神了!霞子你怎么知道?”吴星桥目瞪口呆。
“那是肇事汽车,我怎么会不知道?”
“可是……可……”
“你别‘可是了,我给你揭一揭谜底吧。”我终于抑制不住了,语速明显加快,“那辆肇事汽车不仅在那个时间段、在那三条路上经常出现,而且,车速也不会太快。它在等待,它要找机会,它怎么能快呢?”
“真是这样!霞子你真是神了!”吴星桥手舞足蹈,“它不仅开得慢,有好几次,都停下来了,停得莫名其妙。”
“它才不莫名其妙呢!它有预谋,当然开得慢,当然要经常停车。”我迅速冷却情绪,使自己变得矜持。
然后,我开始帮吴星桥分析,揭开谜面,解开谜底。
——这谜底,就是驾驶员对欧贵的蓄意谋杀。
当然,严格地说,这还不应该算作谜底。驾驶员为什么要谋杀,他的动因何在?这似乎才是真正的谜底。可我没有答案。
接下来,我大致做了这么几件事:向我们刘主任请公休假,谎称带儿子外出旅游。利用这段时间,“深入”欧贵生前所在单位,了解情况;去肇事者所在的劳改农场,进一步了解事件真相;去法院和检察院,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要讲透这些过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况且别人还不见得愿意听。所以,对讲述者而言,不宜追求全面。但是在欧贵生前所在单位,也即服务公司,就欧贵举报一事我作了重点了解,这倒是值得一提的。
我了解到,欧贵对劳动局前任局长马延的举报并非偶尔为之,而是不止一次地以书面方式举报,并且将举报信多方投送。叫我难以理解的是,一个劳动局下属单位的合同制工人,讲起来是“科长”,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小组长,他干吗要和一个隔了几层关系的领导过不去?
然后我又了解到,马延经常到服务公司来,每次来,公司经理都搞得很隆重,邀上副经理、会计以及几个科长,去饭店大吃一通。后来会计私下里发牢骚,说经理真是个败家子,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把应该发给职工的钱,也拿去贿赂马局长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欧贵的女儿那时候得了哮喘病,正无钱医治,欧贵想不通,一纸匿名信,就把马局长告到了市纪委和省劳动厅。
讲起来,欧贵还算聪明,不向区里告,而是直接往上告。
上面来人调查了。找人单独谈话,开半秘密性质的会议。然而,不知是工作马虎走过场,还是能力不济,总之,结果并不理想,“查无实据”,只好打道回府。
欧贵不服气,继续写信,继续多方投递,举报。
后来这事就闹开了,大家都知道欧贵跟马局长过不去,写举报信。甚至马局长在找公司经理谈话时,也说出了这样的话:“别看他隐了名,写的是匿名信,字里行间,连傻子都能看出来是谁写的!”这话通过经理之口传给大家,大家于是都警惕起来,把欧贵想象成一个隐藏在身边的狡猾的特务,或是一颗定时炸弹。
欧贵受到一部分人的孤立,同时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拥戴。拥戴他的是工人,孤立他的是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而他的科长一职,自然是被免掉了。
我想到了那张恐怖的字条:“我能要你的命,你信不信?”
但我不敢贸然下结论。我打算去一趟劳改农场,即肇事者服刑的地方。
我把吴星桥拽了去。去之前,我又收集了与肇事者有关的一些情况,并将一年前交警大队的那些原始材料作了仔细分析。我特别注意了肇事者的以下个人情况。
肖金露,男,三十八岁,无业,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出狱仅两个月,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满后学习汽车驾驶技术,自谋职业,购置一辆小型货车,车号为AR430(系二手货),上路营运。
“下面有一拼,和这个姓肖的,你信不信?”我对吴星桥说。
“你太自信了。要我看,这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交通肇事,和蓄意谋杀,怎么也不可能联系到一起啊!只是个影子,影子而已。”吴星桥显出些悲观。
“一切都有可能。你还跟我举过飞机失事的例子呢。那时候你的智商蛮高的,现在好像……又低了。”
“主要是证据不足,就怕拼不过。”
“所以才叫‘拼。”我无所谓地冷笑一声,“星桥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我哪有缺点?”吴星桥一脸无辜。
“灭自己的士气,长人家的威风——还不算缺点啊!”我态度严肃。
对我来说,那天的情形,是我此生难忘的经历。
一路上,吴星桥都忐忑不安,怕犯错误,怕受处分,怕丢饭碗。老实说,我的难题的确是出大了,叫老同学为难了,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叫你吴星桥当初处理交通肇事时那么随意、那么轻信、那么不肯动脑筋呢?当然,这也是为你吴星桥好,如果问题能查出眉目,搞个水落石出,你吴星桥不就再也没有必要灰溜溜地躲避受害人家属了吗?
劳改农场壁垒森严。幸亏吴星桥找了老熟人,不仅手续简化了,会见场所也作了临时调整,不在千篇一律的会见大厅,而是把我们单独让进了值班室。
肖金露出场时,他的长相、神态以及动作,似乎全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我的想象力和判断力,连我自己都觉得讶异。国外有“天生犯罪人”一说,认为脸上有横肉、两只眼睛之间距离较大的人,有天生犯罪人之相。我国刑法理论不同意这一观点,不过在我看来,这种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初次见面的肖金露,就让我增强了我的信念。
“你是什么人?”坐定后,肖金露看着我,一脸死气。
看得出,他对吴星桥还是有好感的。或许是一年半的刑期让他觉得满意。
我看一眼吴星桥,没有急着说话。
吴星桥说:“我们单位新来的,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似乎为了进一步赢得罪犯的好感,又说:“时间快到了吧?还有几个月,四个月?”
肖金露点头,说还有三个半月。
该我说话了。我说我们交警大队目前正在搞复查,对以往办结的交通肇事案都要梳理一遍,查到你的案子时,我们觉得有两个疑点,现在来向你核实。
然后我说:“在人行横道线上,你的车子向右拐了五十七公分,正是这半米多的距离,致使欧贵当场毙命。从道理上讲,你应该直行;如果为了避人,你该向左打方向盘,可你正好相反,向右打了——我的意思是说,从道理上来讲,说不通。”
肖金露想了想,才一脸阴沉地说:“在交警队,我都交代过了。我当时有点慌张,一紧张,就失控了。”
“你这种说法还是显得牵强。”我的话追得很紧,“你开车已经整整七年了,中途几乎没有间断过;那段路是城市道路,很平整,既不是窄道,也不是陡坡,你怎么会慌张呢?”
“这个……一年多过去了,你叫我怎么回答?”
“问题是,那时候是早晨,六点多钟,人并不多,视线也好,你不该慌张的。”
肖金露看着我,像是突然紧张了,两只分得很开的眼睛闪动着,闪出浑浊而迟疑的光。这无疑给了我某种启示。相信此刻的吴星桥,也受到了启发。
“我再提出第二个疑问:我们调集的资料反映出,在发生交通肇事前的两三个月,每天早晨,你活动的范围都是正乾路、虎卫街和青年路,线路几乎固定不变;而据我们了解,那段时间你承担的业务,是为城南的两家公司送货,与城北的这三条路相隔很远,可以说,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这段问话显然超出了肖金露的思路,他已经不是犹疑不定了,他看着我,一副惶恐的样子,嘴唇半张着,翕动着,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这样的人,也会惶恐吗?
“我……我拒绝回答。”隔了好一阵子,肖金露才像是突然回过神来,“……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还来,提问,我哪能……哪能想起来?”
“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又是致人于死命的,这么重大的事件,你怎么会想不起来呢?”我乘胜追击,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那段时间,你在为两家公司送货,一是华安集团,一是兴盛装饰城,已经送了将近两年的货了,从没间断过;可在出事之前,大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你连招呼也不打,突然就离开了那两家公司。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
“这个……”肖金露的紧张已经在脸上毕现,他似乎坐立不安,老是想站起来就此逃脱。连在两米开外押送他过来的管教干部,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
“最需要你解释的,是这两家公司给你打电话,催你去送货,并且说,还欠着你的运输费,叫你去领取,你也不置可否,迟迟不去,一直拖着。看来,你那时候特别有钱啊!——对这些,你,怎么解释?”
在我讲这段话的时候,肖金露的脸上竟然出汗了。是抑制不住的汗,细密得很,突然之间就冒出来了。这既在我的预料之中,又在我的意料之外。本来死灰似的一张阔脸,因为出了汗,像是平添了一层油彩,倒是好看起来了。
——天又不热,怎么说冒汗就冒汗了,没有一点道理嘛!
他的汗,无疑成了我灵感的源泉,使我激动,使我兴奋。
“我们逮到一条大鱼了!告诉你,我们逮到一条大鱼了!”我突然冲他大喊。
此言一出,我不觉浑身抖颤。我知道我是在冒险,在走钢丝。走过去便可安全抵达彼岸;如果过不去,我将跌入万丈深渊。
肖金露愣了一下。他的发愣,使我失望,甚至恐惧。
“我们逮到了!我再对你说一遍,我们,把他,逮到了!”我的声音,在自己听来,不仅有点变调,都有点气急败坏了。
肖金露又本能地摆出了欲逃脱的姿势。但与此同时,一句话已经从他嘴里脱口而出:“马、马局长,被你们抓起来了?……”
“对,抓起来了!”关键时刻,吴星桥帮了我的忙。
如果不是他的及时补充,我想我已经虚脱了,已经无力再讲一句话了。如果那样,我将功亏一篑,败相会突兀地显露出来。
“马局长,真被你们抓……抓起来了?”肖金露又问了一遍。
这是不打自招的问,可谓愚蠢之至。
冒险的采访到这里,算是戛然而止了。
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肖金露的确是受了马延的指使。虽然中间还有一个牵线人,但事件的操纵者,就是马延。这位昔日的局长,后来的副区长,与肇事者做了一笔金钱和人命的交易。肇事者为他干掉一个人,他给肇事者一笔数额庞大的酬金,算作灭掉一条人命和坐牢的双重补偿。
欧贵后来的举报太频繁了,已把马延推上了风口浪尖,不由马延不写那张字条,不由马延不想办法动手了。
他要借刀杀人。他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他要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
……真相一旦被揭开,后来事件的发展,包括马延的被捕、肖金露案件的再行审判,就是由司法机关启动程序来完成了。程序是复杂的,细密的,需要时间来完成,但已经没有我什么事了。
被害人家属四处打听,寻找一个叫“霞子”的记者。我对吴星桥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打发他们的事,我就交给你了。吴星桥在这次拨乱反正中功不可没,受到领导的褒奖,所以他爽快地说,好。
我们刘主任对我的态度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得都有点暧昧了。除了号召社会生活部的全体记者向我学习外,还催促我,赶快把事件的经过写出来,写成一篇大的通讯稿,在我们报纸上独家刊登。我说刘主任,这种表扬稿就不写了吧,我倒想写一篇小文章,投给内参,就怕我写出来分量不够,你要帮忙。
刘主任一听,登时来劲了。
交通肇事案的背后,是一起雇凶杀人案。而在雇凶的背后,似乎同样隐藏了一点什么。带着这个想法,在调查事件的后期,我已经把我的工作重心转移了,转移到了对另一件事情的调查上——匿名信本来是隐匿的,何至于那么公开,公开到服务公司乃至区劳动局的人全都知晓;就连作为当事者本人的马延,也说出了那样的话:“字里行间,连傻子都能看出来是谁写的。”显而易见,马延不仅掌握了匿名信的内容,就连字里行间的东西,他也了如指掌。
事实的确如此。在调查中,我惊奇地发现,有好几份告发马延经济问题的匿名信,居然就躺在马延办公室的抽屉里!换言之,检察机关在后来搜查马延办公室的时候,从抽屉里搜出了好几封这样的信。
但检察机关没有就此问题深究下去。
而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荒唐的、差不多可以称为荒诞的结果——本来是一件多么郑重的事啊,怎么会落到如此滑稽、荒诞的境地?
我所说的给内参投稿,要写的就是这件事。我们刘主任那时候还不知晓,如果知道,我相信,他立马就会泄气的。
我去了一趟省劳动厅,找纪检部门的同志了解情况。
我问他们,对于那些举报下面干部违法犯罪的匿名信,都是怎么处理的?纪检部门的同志扫一眼我的记者证,以介绍经验的口吻侃侃而谈,说我们首先是不辞辛苦,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对于查有实据的信件,就分门别类,该交公安机关的交公安机关,该交检察机关的转交检察机关,该由党内处理的,就和各市纪委联系,作出相应处理。我又问,那么对于查无实据的信件呢?纪检部门的同志说,那要分两种情况了,一种是署名的,一种是匿名的。对于署名的,我们都会亲自登门,与写信的同志交换意见,公开我们的调查结果;对于匿名的,他们自己都不敢留名字,我们怎么办?只好往下批转,由省到市,再由市到区,一级一级,交给下面,让他们看着处理吧。
我再去市纪委,接待我的同志正襟危坐,他的回答竟和省劳动厅纪检部门同志的说法如出一辙。
我不禁瞠目结舌。难怪匿名信会躺在马延办公室的抽屉里呢!原因不仅不像我开始时想象的那么复杂,并且,简单得都显得随随便便了。就是这么一个“查无实据”,使得被害人欧贵的举报信经过层层“批转”,堂而皇之地就到了马区长的手里。连匿名信的原件都落在马延手里了,还有什么情况不能被马延所掌控的呢?
这是一个弊端,显见得是我们监察制度的弊端。也就是说,由于官样的“文件批转”,一个无辜的人就这么被杀死了,死得那样干净,不留痕迹。
我把我的想法讲给我们刘主任听。刘主任听了后,神色黯然,顿时缄口,再也不提“内参”一事了。后来,他只说了一句话:“写这个,合适吗?”
责任编辑 牛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