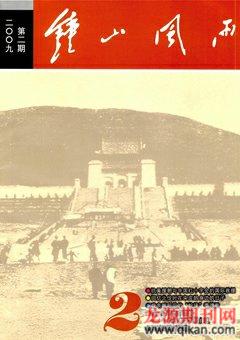我亲眼所见的“蛇侠”季德胜
徐 珣
“医术蜚声海内外,神药救命千百万。”这句话用在蛇医专家季德胜身上,一点儿也不过分。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被海内外公认为“绝代蛇侠”。
季德胜是江苏宿迁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个蛇花子家庭。所谓“家庭”,不过是荒郊一个破败的土地庙而已。他从小跟随世代沿袭的“蛇花子”父亲季明扬闯荡江湖,行医四方,不断捉蛇、玩蛇、采药草、制药丸,继承了祖辈医治毒伤的高超医术,他现场试毒、生吞活蛇的本领,令许多外国蛇医、专家学者惊叹不已,钦佩如神。
季德胜在旧社会颠沛流离,生活坎坷,饱受欺凌和嘲讽,亦因此养成反抗强暴、不屈不挠的侠义精神。建国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尊重,以自重、自强博得社会的爱戴和敬仰,打造了一代蛇医的崭新形象。
1956年,季德胜被南通市中医院聘任为蛇伤科主任医师。当年年底,他毅然将祖传六代、流传三百年之久的“季氏蛇药”秘方无偿地献给国家,成为医界的一大“义举”。
季德胜曾当选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58年9月,他出席全国医药卫生工作先进代表大会和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周恩来赞誉季德胜为“稀世罕见的蛇侠”,他当众握着季德胜的手,十分亲切地说:“你的医技和蛇药,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是谁也抹煞不了的功劳!”事后,季德胜又被中国医学科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
这位被共和国尊为医学科学一代骄子的神医一生救治了上千万名危在旦夕的国内外蛇伤患者。他的“季德胜蛇药”风靡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等许多地区和国家,成为热带、亚热带百姓居家必备的“克毒救命”神药。另外,经过世界各国临床医学验证,“季德胜蛇药”还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淤、消肿止痛等多种功效,是治疗30多种疾病的首选良药。
季德胜于1981年病逝,时年83岁。“一代蛇侠”尽管撒手西去,但英名长留人间,仅“季德胜蛇药”的销售量就达20亿之巨,国内外有关他的电影、电视、小说、传记、报告文学等竞相出版发行。有些国家甚至将季德胜奉为“克毒圣手”,日本广岛一带将他作为“蛇神”奉供,印度民间美称他为“季公蛇佛”,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都推崇他是“东方蛇仙”。
“神”也好,“佛”也罢,季德胜其实是个憨厚、谦和、淳朴的苏北大汉。他生前经常出没在苏北地区的街头巷尾、荒山野岭。用季德胜的话说,“我生是蛇花子,死也是蛇花子,风里来雨里去,不足为奇,更不足为怪”。这话说得确实一点都不假,因为本人作为一介书生就亲眼目睹过季德胜多次治病救人,真可谓:老乡见老乡,一切皆寻常。
怪病奇术

我第一次见到季德胜,是在1943年的秋冬之交。
当时我还很小,年仅13岁,由于家庭经济窘迫,加之如皋城内小学不多,只有寄宿在老表叔家读私塾。
老表叔是个老学究,常年只开一个复式班,收了七八个学生。想不到命运捉弄老实人,我那名叫英丽的表姐不知不觉患上一种怪病,双臂只能悬举,不能落垂,犹如投降的模样。表姐十六七岁了,一个黄花闺女,哪能四处张扬,老表叔请了几位名医到家中诊治,都不起任何作用,又请我父母陪表姐去上海、无锡和扬州等地大医院看病,按摩、针灸、电疗,几乎什么方式都试过了,也无济于事。
一天傍晚,我父亲领来一个头戴毡帽的中年人,此人长相很难看,还留着八字胡,身上一件邋遢的长袍子竟然用麻绳束在腰间,脚上连袜子都没穿,破棉鞋上尽是泥巴。
父亲介绍说,来人姓季,是个游医郎中,治过许多奇病怪症。
姓季的粗人粗语,很是直爽。他对老表叔说:“你就跟着乡亲称呼,叫我季侉子吧。你闺女的毛病,包你治愈,但是两包洋纱,少个子儿都不行。”
老表叔摇摇头,根本不相信。经父亲一再劝说,才让这个季侉子与表姐见了面。
岂知季侉子拉着表姐就往厢房内跑,老表叔不放心,嘱我父亲跟随着。季侉子却认真地说,治这病不能有第三个人在场,你们实在有顾虑,可派个小孩监护。
于是,老表叔吩咐了几句,我也进了房。
季侉子将房门“咚”的一声关上,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他让我站在一旁,然后围着表姐踱了几个圈,嘴里细声细语地说:“不打针,不吃药,一会儿就会好的!”
岂知话音刚落,季侉子走到表姐面前,忽地划着一根火柴。啊,一条蟒蛇从他袍兜里突然窜到表姐大腿上。
表姐瞪着眼一声尖叫,双臂落下,推脱蛇身,就往房门口冲去……
说来也怪,表姐的怪症消失了。季侉子收了蛇,扎好腰绳说:“祖传小术,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没吓了令爱便好!”
老表叔既惊喜又发愁。父亲知道他老人家平时手头就拮据,为给表姐治病,连祖传的家当都典押在当铺,季侉子索要的酬金怎么拿得出?于是,他让我到巷子头打一斤“高粱烧”,买了点下酒菜,先款待季侉子一下再说。

季侉子也真怪。他一边喝着酒,一边听我父亲诉苦,陡然长叹了口气说:“老人家早年丧妻,与女儿相依为伴,过着这么贫困的日子,实在不容易啊!”
父亲本想请季侉子减少一半酬金,岂知季侉子一拍桌子说:“你可能不知道我姓季的脾气,对有财有势的富豪说一不二,毫不留情,对你老表这样的教书先生就一切免谈了。那两包洋纱权当是开玩笑罢了。”
老表叔一听,感激涕零,对着季侉子又是打躬,又是作揖,连声说道:“我遇上菩萨了,你真是救苦救难啊!”
季侉子笑得前仰后合地说:“我哪是什么神仙,是走江湖的蛇花子呀!”
表姐直到出嫁生育后,都不好意思谈及治病的隐私。老表叔为了报恩,要季侉子每隔一段时间寄封信来,以便集聚病家一齐医治、购买蛇药。考虑到季侉子不太识字,连信封都写好,贴上邮票,交给了他。由此,我们才知道季侉子是“浑名”,他的真名实姓是季德胜!
以蛇治“蛇”
以后,季德胜每到如皋来,都要到老表叔家打个照面。老表叔也说通长巷与市巷交叉口的石家祠堂堂主,让了间小栈房给季德胜临时住下。
1945年清明节前一天,我在石家祠堂门口帮助季德胜照料药摊。也许是天气阴冷的原因,过往行人不多,生意清淡。季德胜拢着长袖打瞌睡时,来了个头戴礼帽、身穿府绸长袍的歪脖子。此人对季德胜抱拳一拱说:“久闻大名,今天能在如皋街头见到,十分不容易。”
接着,歪脖子说要找个地方和季德胜聊件大事,现在就收摊,至于蛇药,他一个人全包了买下。
季德胜尽管急等钱用,忽然间却疑惑起来,问对方是什么人,包下蛇药干什么用?
歪脖子怔了怔说,他是从沈阳来的药商,近来因春雨绵绵,毒蛇太多,被咬伤的病人急需有特效的蛇药。
季德胜心直嘴快,说非蛇医的外行投药不准,是要出人命的,何况他的药毒性强,内力大,成分也复杂。

歪脖子趁机说,他虽是外行,但早就听说季氏蛇药能治百毒,以至药到病除。说来说去,歪脖子亮了底,他想用重金来购买秘方。
歪脖子以为季德胜不相信,当即打开带来的小皮箱,露出一扎扎纸钞和银元。
歪脖子咧开嘴里的金牙,嘿嘿笑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穿了,你们抓蛇卖药,还不是为的这些!”
季德胜从未见过这么大气的阔佬,便虚晃一枪说:“你不实话实讲,就一切免谈了。”
歪脖子锁上皮箱,见四周无人,才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原来,他叫黑木三郎,是日本军医。
这个黑木满以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便道出了实话:一来日本本土腹蛇相当多,二来部队攻入中国,东三省的七寸子也十分可怕,所以甘愿以高价购买季氏蛇药的秘方。
季德胜一听,将衣袋里的酒瓶套在嘴上,一仰脖,咕咚咕咚喝了个瓶底朝天,然后“咣当”一声,将酒瓶摔得粉碎。
他板着脸冷冷地说:“我姓季的讲义气,更有骨气,再是缺钱用,也不能丢祖宗的脸。出卖秘方,便是出卖良心!出卖祖宗!”
黑木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又提出另加犒赏。季德胜恼火了,大声吼道:“老子说一不二,否则还称什么蛇林好汉!”
他见黑木还在拉扯自己的衣衫,气怒交集,将面前的那只皮箱“咚”地一下踢得有丈把远。
黑木露出狰狞面目,两眼闪着凶光,手伸到裤袋里就要掏手枪。
季德胜从竹篓子里抓出一条眼镜蛇,狠狠回敬道:“你以为中国的蛇花子好欺侮吗?你敢下毒手,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
只见那眼镜蛇喷着毒气,呼哧呼哧地窜向黑木。黑木嚎叫一声,提着皮箱,头也不回地逃之夭夭了。
事后,老表叔赶到祠堂,劝说季德胜赶快离开如城,因为黑木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季德胜余气未消,依然愤愤地骂道:“老子非得把点颜色给小鬼子看看。我反正上了年纪,半个身子下了土,但是脊梁骨是硬的,人格是响当当的!”
果然不出所料,季德胜刚被老表叔连拖带拉悄悄送上货船,黑木便领着宪兵队来抓人。他们在石家祠堂内如临大敌,找不到季德胜,却对他丢弃的一团破被絮怕得要命,吓得要死。他们先是用刺刀乱戳乱挑,见没有毒蛇窜出,还不放心,再浇上汽油烧成灰烬。临走时,黑木咬牙切齿地骂道:“蛇花子不好对付,大大的厉害!”
一条赤练
自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季德胜的身影了。起初他还带过信给老表叔,对丢了送给他的那条棉被一直耿耿于怀,还担心自己走后,黑木会对祠堂堂主报复,不知有没有连累到老表叔,再后来便断了音讯。老表叔猜揣,怕是给他的备用信封弄丢了,又忘了具体邮址。
几年后,听季德胜老家宿迁一个卖花生的小贩说,季德胜早已去了南洋,先在新加坡,后又转至马来西亚采集药草。又听人讲,季德胜被印度有关方面请去,为该国元首治蛇伤,多亏蛇药灵验才化险为夷。
老表叔是1950年病逝的。据他说,住院期间他从报纸上见到一则新闻,季德胜在香港卖药时,一个英国老板想用他的秘方“合资”创办蛇药厂,被季德胜坚决拒绝了。
之后我到青岛去求学,再也听不到季德胜的动向。我毕业后回到如皋老家,由于家庭成份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找不到称心的职业,又去北大荒支边了几年,更无心打听与己无关的人和事了。

也许应了“人尽缘未了”这句话,端端想不到事隔20多年,我又一次见到了季德胜。
当时我已回到家乡,在柴湾中学当教师。“文革”初期,我因撰写书稿惹来横祸,被造反派关在牛棚里勒令交待问题。岂知祸不单行,一天夜里我竟然被蛇咬了一口,翌日早上,左臂疼痛难忍,肿胀得如同木棍。赤脚医生没有办法,公社医院也无药可治,忙着搞“文攻武卫”的头头们总算发了善心,批准我赶快去南通市找季德胜。
听到“季德胜”三个字,我顿时眼睛一亮,内心非常振奋,立马乘上公交汽车一路赶到南通中医院季德胜的办公室,岂料竟然铁将军把门。经打听得知,近来他一直在观音山抓蛇,于是我改乘一辆三轮卡,一路飞驰而去。
到了观音山,时辰已是中午,想不到这位专家大人竟躺在破庙里的大门板上,打着赤膊,蜷缩着身子,呼噜呼噜鼾声如雷。只见一只空酒瓶倒在席枕旁,盘子里残留着的猪头肉上落着几只苍蝇。
我手臂胀得慌,实在支撑不住,只好轻声喊道:“季医生!季医生!”
多年不见,季德胜又老又瘦,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他听我自报家门后,才揉了揉眼睛,不紧不慢地问道:“小虫怎么会咬到你的?”
我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他“扑哧”一下笑得咧开了大嘴:“有意思,有意思!你从牛棚里来,是牛鬼;我抓蛇,是蛇神。咱们牛鬼蛇神凑合在一起了!”说罢,猛地一下跃起,在我伤口处比划了一阵,接着从土墙旯旮的坛子里摸出两颗药丸,顺手举起半瓶老窖酒,吹喇叭似地喝了几口,一抹下巴道:“硬要给做文章的人戴这顶帽子,那顶帽子,连我这个蛇花子也要算作什么‘权威,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了!”
季德胜将一颗药丸塞进嘴里嚼了嚼,吐在手心,用酒拌和了一下,“啪”地将一个软巴掌糊在我的伤口处,又叫我将另一颗用酒咽下,然后在肿胀处抹了几抹,风趣地说:“没啥事了,咱俩打一会牙祭,不好也好了。”
我这才套近乎地讲起多年前的那两件事来。季德胜对我的印象已不太深,对老表叔却刻骨铭心。他说我表姐那样的奇病怪症,洋专家大医院不一定治得好,偏偏三教九流的江湖郎中,依仗祖传奇术秘招,能三两下出现奇迹。季德胜谈到老表叔一心想报恩,其实是他太固执了。季氏门中,列祖列代抓蛇治病,说到底是救死扶伤。钞票是人挣的,比起人格来,算什么狗屁!这一点,连狡诈的日本人黑木都不理解,都愚蠢得可笑!
季德胜还谈到黑木是日本军医,他才那样对待的。如果真正是日本的民间医生,或是被毒蛇咬伤的日本病人,他还是会竭诚服务,友好相处的。
神药见神效。侃了个把小时,我的手臂果真全消了肿,安然无恙了。
临走时,季德胜搔了搔头顶的白发,眨巴着大眼睛,搓搓手说:“回去后,还要蹲那个牛棚吗?”
我苦笑了一下,季德胜却认真起来,他沉吟良久,从床下捧起一只用草绳绕扎着的土坛子,讪讪一笑:“老朋友,别的没啥礼物,有条小赤练送你玩玩。”
“小赤练?”我一惊,忙摇手:“不,不会玩。”
季德胜哈哈大笑起来:“物是人非哪!知道你没心思玩。小赤练带回放在牛棚里,能以毒克毒。这小虫样子可怕,实则习性挺好,一般蛇嗅到它的气味,马上就逃得远远的。小赤练不会乱游,是个有耐劲的‘看家神呢。”
我拎着这个神奇罕见的“礼物”回去了。有了小赤练,我在牛棚里有了安全感。不久,我被转送到县城里“火线”批斗,后来住牛棚的朋友也和这条赤练续上了“情缘”。
笑损浮利一鸡肋,多取清名几熊掌。年届古稀,我更加缅怀季德胜这位技高德重的“神医”。我和他既是南通老乡,又是宿迁老亲,一直想写他的传记或报告文学,但他在世时我打过几次电话,都被婉言谢绝了。总之,季德胜是位神秘而又普通、奇特而又平凡的人物,朴实谦逊,又令人难以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