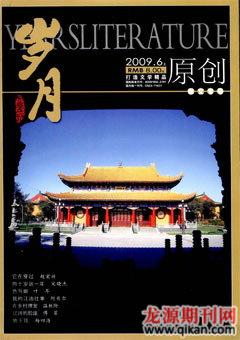在乡村理发
温新阶
人一辈子从婴儿“剃胎头”开始,大约要理几百次发的,不论你老到什么程度,很多方面不断萎缩,唯有头发却依然顽强地生长,我们今天在城市的很多“大众理发厅”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老者躺在椅子上,随着理发师刀剪的舞动,一撮一撮斑白的发须飘然而落,那老者们似乎正如一株老树,飘然而落的似乎不是发须,而是枯槁的树叶。
乡下老者的理发情形迥然不同,小时候常常目睹祖父理发(那时乡下称理发为“剃头”,这与旧时乡下男人全是光头有关)。乡下没有理发店,老人们理发是相互“帮忙”,那工具也十分简单,仅一把剃头刀子而已,即便仅有的刀子,也远没有今日的精致,都是请铁匠打的,钢火好自不必说,体积硕大,样子笨拙,似乎不是用来剃头,而是用来杀头,刀柄也是自制的,杉木,稍粗的一头钻一个眼,一根细铁丝便将刀子安了,再顺着柄凿一道槽,剃完头,把刀子折叠起来,刀锋藏进木槽里,以免弄钝了刀锋,也多了一分安全。至于围布是没有的,往往是剃头者自己带一块旧布,忘记带的,帮忙剃头的人随便找一块什么破塑料布什么的对付一下,倘是冬天,那破塑料布总是支楞着,影响着剃头人近距离作业,人一动,还哗啦哗啦地响……祖父是稍讲究些的,除弄了一块破塑料布做围布之外,还有一块半圆形的木板,漆得光亮光亮的,剃头时,本来系了围布,他还要用手举着那块半圆的木板,内圆的一侧贴着脖子,头发大多就落在木板上,剃头人在哪边剃,他就把木板举在哪一边,剃到后脑勺时,他就只能捏住木板的一边将木板伸到背后去,那样子十分滑稽,我一直搞不懂,既有围布,还要这木板干啥?有一回我忍不住向祖父提出了这个疑问,祖父说:毛发是受之父母,怎忍随便落地,与他人发须混杂?怪不得祖父剃头时木板上的头发落满了,他就把它倒在铺好的旧报纸上,剃完头必定包回来,将其撒到房顶上,头发未剃时便是顶天之物,即便剃下了也该作顶天之置。
父亲成人时,乡下的光头依然流行,但念书人或是干部却已经开始留头发了,父亲二十多岁就开始做村里的干部,自然留了分头,祖父起先不屑,后来见留分头的人多了,也就不再贬斥。不过理发却有困难,旧时剃头匠全然不会理分头,他们也没有理分头的的推子。过去每种文化的传播往往会从学校开始,果然,村小里就有了一把推子,好像是学校工会买的,本来是为老师服务的,不过仅有一把推子和一块围布,梳子和镜子是理发的老师自家的,也没有其它的刀剪,长发要剪短不好用推子,老师就拿了自家的老婆做鞋的剪子来处理,倒也没有大的问题,一个村就这么一把推子,附近的社员都到学校来理发,过去的学校不像现在同社会有些隔膜,那时一所学校就如当地的一户人家,校长也是这么看的,就准许大家到学校理发,每每放学后,学校的阶沿上就有一些理发的人,也有的等得急了,便寻来乒乓球打上一阵,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投射在土墙上,生动而有韵味。
到了我们这一代,自然极少有人剃光头了,都是短发,打理简单且有精神,可在学校却依然会看到有些学生的头发留得很长。大哥便是如此,倒不是没人理,而是他小时候不让人理发,因为他四岁时,脑袋老痒。祖父请人给他剃过一回光头,那师傅手重,刀子又钝,一个头剃下来,声音都哭嘶了,头上还留下三个口子。从此,他就有了“护头”的毛病,尽管不是剃光头,一说理发他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因此他的头发就留得老长,实在不像样子了,等他睡着了以后把他抱到板凳上,用绳子缚了,再把板凳竖起来,请人给他理,后来学校来的秦老师手轻,技术好,给大哥理了两回,再就不用缚在板凳上了,缚在板凳上理发的事,只是为后来增加了一点谈资。
留长发多的主要原因还是理发的人少了,我上小学时,同班有个叫朱玉洲的同学,请人理发请了三个周末还是没排上队,他父亲就用做鞋的剪子给他剪短了,星期一他上学时,头上一道一道的印子,大家都喊:朱玉洲脑壳上修了梯田,男同学喊,女同学也喊,朱玉洲一边哭一边找老师告状,课外活动时,我们在女班主任寝室里站了一个小时,香皂的香气弥漫了整个房间,我第一次闻到这么香的气息,正是这次罚站,使我把这种香气定格为女老师的香气,以后有女老师叫我到房间去我总是既激动又紧张。
后来我也做了老师,起初也是在乡村小学执教,像以前的老师一样,我也为附近的村民理发,不过我的工具较之过去已经进步了很多,不但有推子,刀子剪子镜子梳子都是齐全的,还有用来润滑推子的一小瓶机油,围布也洗得很干净,我还专门请人做了一只小木箱,漆了油漆,把理发的工具袋装在木箱里。我也常常在放学后为村民理发,不过更多的是别人请了我去,目的是请我吃顿饭,经常在放学以后,我拎了那只木箱跟在学生身后到村民家去理发,岔路口时,学生一个一个跟我打招呼,等他们走得看不见了,我才往理发人家走去。
在村小教了两年,我便调到镇上去了。镇上有理发店,理发工具用不着了,我把它送给了新来的老师,许多年以后,我已在市里混饭吃,回到乡下见到那位老师,他还讲起了那套理发工具,他说,虽然早已不能用了,他却没舍得丢,买了新的依然装在那木箱里,我这才记起,我老家的乡村,依然没有理发店,理发依然是相互“帮忙”,不过,理发工具已经不单见于学校,每个湾每个冲几乎都有一套。
我说:“你几时也来给我理一回发。”
“您不在城里理?”
“喝茶就喝茶,哪来这多话。”我套用了一句民歌的歌词。
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懂了,懂了。”
我不知道他懂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