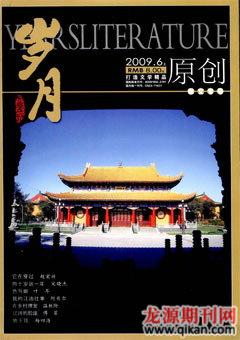墓地上空的英雄主义
葛启文,1987年生于安徽芜湖。近年来,有文学作品见于《美文》、《文学界》、《中国校园文学》、《读者》、《散文诗》、《散文诗世界》、《诗歌月刊》、《诗潮》、《当代小说》等刊物,《语文报》、《小品文选刊》等多有转载,并被收入长江文艺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编选的二十余种作品集。
墓地是一个人在生命路途中必须经过的驿站或终点。当我睁开双眼。置身于杂草坟墓的深处,它的面孔不断地涌现出来,飘忽不定,在原生态的大地上游荡,不留一丝痕迹。人生来注定要承受苦难,消耗四季轮回的时光,在生与死的缝隙间。此消彼长,完成一场悲喜交织的仪式。
天有不测风云,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平凡者的坟墓丝毫引不起我的关注,但英雄的死,意味着个体生命卸下了尘世的面具,归于泥土,是对一种英雄主义的崇拜。就像现在,我所在的海子墓,墓地内部埋葬的是一个英雄,长期备受争议,剩下一片流言蜚语的阴影。
这是一个恍如梦魇的季节,云翳灰暗,繁花落尽,墓地的轮廓、尺寸、颜色,逐渐黯淡下去,干燥,僵硬,收缩为一枚外形酷似果壳的核。对于查湾村来说,海子墓是精神的、文学的、艺术的、民族的,表现出一种英雄的氛围,超越了传统的习俗和思想观念,走向毫无顾忌的宗教境界。海子的墓不大,用水泥浇铸而成,三棱锥形,顶部长满了荒草,密匝匝的,扎根于土壤中最深厚的肥料。耐人寻味的是,在墓地之侧,镶砌着海子生前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块喇嘛经石,刻有咒语、铭文、彩色佛像图案,粗糙,灵异,不断向世人打开神圣的极乐天国的面貌。对此我不避讳。海子墓是村庄可以不被遗忘的部分,比之于豪华房屋建筑,查湾村里的人显然信奉了有点寒酸的坟冢,安安静静,沉默无语。在我看来,墓地的平凡和诗意,代表了一种高尚的精神标志,把海子的心灵和事物,心灵和世俗割裂开来。
我习惯了世界的诗意无限蔓延,从诗学的角度出发,反复地看海子墓,一个浓缩了太多故事太多忧伤、又有太多象征的角落。四周空旷得几近无人。篱笆栏内外的山冈仿似肿瘤。这里是南方以北,北方中的南方,无数孤单的树,站在远离喧嚣的乡村,茕茕孑立,从容不迫。青草、金银花、行人以及车辙的印记,在地上连成疆域。或许,离墓地最近的地方,也是离神最近的地方。
不要以为死寂的旷野没有灵魂。神在看着我。那些沉睡的亡灵,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古怪诡秘,不时向亲人们托梦、倾诉、哀怨?远或近的生者,除了泪流满面,莫名地活在现实的人世间。“我的海生(海子的本名)没有福啊,老早就死了”,老人说。她是海子的母亲操采菊,七十多岁,一个曾经的裁缝,鬓角白发如霜。在她的心里。海子不是名噪一时的天才作家,不是诗歌英雄,而是最疼爱的儿子。生命,多么的脆弱,像失手摔碎的瓷器。素来如此,我对墓地缺乏打扰的勇气,不想因为自己的行为惊醒了一些地下的亡魂。
毫无疑问,墓地是自然界动物寄居的客栈。最主要的住宿者,来源于查湾村里闲散的家畜野禽,譬如鸡,羊,乌鸦,以及各种类型的虫子。阳光照耀着大地上的事物,鲜为人知的风景倒有一番趣味。鸡,在墓地的附近,四处啄食,笨拙,活泼,瘦小的身子遮掩不住一股子疯劲,但我惊奇地看到它的背影,有我幼年一般的淘气、纯真。羊在草上奔跑,在不属于风花雪月的坟墓上奔跑,在前所未有的地平线中奔跑……蚊虫们在树丛深处飙歌,一声叠一声,嗡嗡嗡,碎玉裂帛般一齐为墓地唱歌。
同样是在墓地。十多年前的墓地,好像比现在显得更加非同寻常。死亡,意味着一场葬礼即将开始,犹如一枚钥匙,开启了通向坟墓的地狱之门。1989年的某个下午,在山海关至龙家营的一段铁轨旁,海子还很年轻,努力铺开纸片,用铅笔写下了遗言:“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当时他已经神经错乱,走火入魔了。他慢慢把身体躺在铁轨上,腰部紧挨着枕木。一列火车呼啸而过,没有恐怖,没有呻吟,只有生与死的涅槃。自杀是否有意义?我认为,生命的存在长期要饱受种种折磨,人却不能以自杀的方式告别苦难。对于海子的母亲来说,她必须承受痛不欲生的悲伤,必须将儿子的骨灰盒从北京带回查湾村,必须在风雨交加的路途中前进,或者返回。她是一个瘦弱而佝偻的母亲,有泪,不是忧郁,是真的哭泣。无言,就是悲。生离死别,莫过于回归大地,我清醒地揣测到一个英雄的葬礼——肉体与灵魂的背井离乡。可以想象:天空浩瀚,查湾村的田野之上,一百多人的队伍,肩扛漆黑的棺木,带着檀香、冥币、金色锡箔的法器等,绕过山冈,转过池塘,匆匆赶往墓地。送葬的人们,或尖叫,或烧花圈,或放鞭炮,或膜拜,一波一波,似钟鼓丝弦之声,深藏无尽情感。英雄的葬礼被精心策划成功了,因为他们相信脚下的墓坑,是命里的归宿,是传说中的风水宝地。仿佛一切显得顺理成章,一切似乎早已命中注定,都逃不脱归于无可奈何的结局。
其实,和许多平凡的人一样,海子注定有两个栖息地,生前的家,死后的墓穴。从我站立的角度望出去,便可看见不远处的查湾村以及海子的家了。四季之中,相较于巴掌大小的墓地,海子的家建在一个平坦的小山岭上,坐北朝南,是简朴的农家小院,毫无遮掩。海子生于民间几乎是必然的。他的一生,以民间为中心,叱咤诗歌风云,与查湾村的家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蕴含了亲切平易的民间色彩。自从海子死后,这栋老房子相继经历了被抢救、修葺和重建的命运历程。日益喧嚣,焕然一新,成为参观性的纪念基地。人道主义的贡献不能磨灭。幸,抑或不幸,谁知晓呢?海子的家相当素雅,大门口的顶上是一块横匾,书曰:海子故居。堂厅,地面干燥,左边墙壁上挂着海子生前的一些照片,右边墙壁上是字画、石英钟以及大大小小的斑点。隔壁的房间,属于海子生前的书房,摆放着海子生前的大量的中外书籍,一台黑白电视机,印有“查氏宗谱”的铁箱。另一个房间,则是海子父母的卧室,诸如衣柜,镶花木床,蚊帐,火桶,沙发,剪刀……它们像雕塑一样安静,陈旧,惨淡,有一股复古式的韵味。除此之外,院子里的土地空着,东一簇,西一簇,重重叠叠的。长满了芜杂的草。万物皆从海子的心灵空间中滋生出来:查湾村,是他心中的查湾村;世界,是他心中的世界。
我之所以推崇海子,是因为年轻人需要榜样的力量。我们呼唤英雄,寻找着英雄。我们需要从英雄的身上,看到人生闪光的东西,看到生命燃烧过程中光彩照人的美感。
海子是以生命为诗的英雄,向太阳奔去,灵魂催促着肉体不停地奔跑。他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渴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太平洋,西达古罗马,北至高加索山脉,南抵印度半岛。诗歌帝国建造起来了,原始,诡异,神秘的魔法使海子的肉体与灵魂都沉睡在宫殿的里面,使他永远无法走出若隐若现的台阶;咒语拒斥了现实世界耀眼的阳光,在魔法的
笼罩下,幽暗的宫殿越来越阴森,海子端坐在诗歌帝国中央,像俄狄浦斯王一样寂寞、孤独、“不被人理解”。那些令人悲痛的事件或黑色帝国,最终为墓地所掩埋。
没有人愿意惊醒海子在墓地深处的梦。坟墓,是大地上突起的碉堡。日日夜夜,草长莺飞,在墓地的内部,一个瘦弱、沉睡的英雄——海子,躺在乡村的山冈上,凝视着查湾村的农舍、田野,把无数梦想省略,不为凉风悲歌。在他的英雄史里,生命呈现出脆弱的真相。不仅如此,我想我被触动的,则是一个人的消失,像空气一样没有踪迹,仿佛那个人根本就未存在过。查湾村的人或事物,依然如旧,早已习惯了一个英雄的墓地所表现的文化魅力。海子墓的前面点缀了一些零散的菜畦,碎花点点的池塘。村妇在水里淘米洗菜,心无旁骛,一边嬉笑,一边哼着黄梅小调。同时,她们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聚集墓地,来祭奠一个自杀的人呢?
墓地的朝拜者,他们的身影隐没在坟墓周围的草木里,他们是海子生前的朋友还是敌人,谁也无法知晓,或许是农民、工人、企业家、职员、文学青年、渔夫、抑郁症患者、士兵……他们共同敬仰的诗歌英雄,海子,被掩埋在墓穴的内核,已经枯萎得不像人了,像粉灰,或者像木乃伊。然而,海子在死后是一架诗歌的播种机,广收信徒,使成群结队的崇拜者、景仰者的心灵得到安歇,仿佛江湖上一个真正的侠客,不会在意海子的躯体,更多是记得他的剑,他的诗歌魅力。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不知为何,死亡是一支没有音符没有节奏没有旋律的安魂曲,血缘中断,骨肉分离,从而加重了亲人在尘世思念的痛苦。墓地构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天然屏障。海子母亲因此承担了太多的悲欢离合。在我的整个大学时代,曾经三次乘坐“金龙”客车,左右颠簸,一路迎风驶往查湾村。每一次来,海子母亲都会用最淳朴的方式接待我,跟我说海子的事情。老人眼里常年含着泪水,没有哭。对此我从未深想。有无数理由让我牢牢记住海子母亲,操采菊,一个坚强、朴素而又伟大的女性。海子的天才与母亲有关。她凭借天生的聪慧和求知欲望,读过七年的私塾,在封建旧时代,完全属于文化程度高的知识分子。在墓地之侧,“人若老,很多汉字都不认得了”,海子母亲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跟我说起了很多海子曾经的往事,比如幼年的海子很俏皮,她只好挑选家中的旧报纸,将里面的内容编成一个个故事,讲给儿子听。她在回忆的时候,热泪盈眶,一声声泪水径直滴落,仿佛刺穿了我的内心,无比疼痛。我一直在矛盾中煎熬,因为我不忍心打扰老人,每次去,总会说起海子的死。揭开她的内心深处的伤疤。祭奠是善意的,却易伤人。十几年来,全国各地到海子家中的人不计其数,其中很多人阴险狡诈,对诗歌英雄的遗物,虎视眈眈,致使海子的私人信件、照片、手稿等大量流失,令人痛心。作为墓地的守护人,老人守着海子的遗物,坚定不移,心外无物,是需要毅力和牺牲的,由此,在我看来,这何尝不是一种英雄主义呢!
渐渐地,我感到了英雄主义的真实和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一切。显露瞬息万变的诱惑,像人类的情欲一样,在英雄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所谓英雄,通俗地说,即胸怀大志,独具正义感,能领导大众或改变历史的人。毋庸置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诗人、思想家和爱国青年的时代,是海子的时代,是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然而,那个时代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我们越来越现实起来,不会再为理想而奋斗,导致人格卑微、生命残缺,诗歌没有了思想、艺术以及冲击力。中国新诗的衰落,其实就是知识分子过分迷恋自我、脱离现实和缺乏英雄主义的结果。
英雄,没有重复。青梅彩虹,煮酒论英雄。当然,我不是英雄,当我老了,只想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超越苦难,载着贫困、羸弱的身躯,往天国的更深处飞去。愿世上所有的灵魂都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