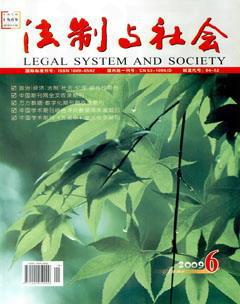青年毛泽东国家观之嬗变轨迹探析
陈 璇
摘要青年毛泽东国家观对其后来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其嬗变的历程就显得很有必要。青年毛泽东像当时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热切关注国家的出路问题,因此其国家观的嬗变能始终围绕“救国救民”这一主题展开。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剧变以及西方各种启蒙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的国家观思想几经艰辛蜕变,尤其是在具体救国救民的途径和方法上具有独特的特点。总体上看,青年毛泽东的国家观经历了从启蒙阶段——“忙乎未定“国家观阶段——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确立的几个阶段。从这一历程,我们可以发掘出毛泽东的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国家观救国救民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182-03
一、毛泽东的启蒙国家观历程
和许多革命家一样, 毛泽东也是在萌生出爱国、救国的思想感情基础上开始构建自己国家观的。直到1910年秋他去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前,少年毛泽东一直在韶山地区边读私塾边从事劳动。一方面,通过劳动实践,他发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并开始热爱劳动人民,同时他对于劳苦大众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抱不平的思想感情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阅读使他接触了许多爱国主义的书籍,受到巨大教益和启迪,并逐步树立起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观。十几岁时他便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顾炎武的《日知录》等等。1936年他回忆说: “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豍在东山学校读书时,毛泽东通过借阅梁启超等人主编的《新民丛报》,首次接触到了关于西方资产阶级学术与政治思想以及维新变法的思想。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关注他们的思想。1900年-1910年这一时期,由于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的限制,当时的毛泽东并不反对皇权,反而还倾向于支持君主立宪,他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当然他也毫不例外地头上蓄有作为拥护清朝统治标志的辫子。豎可以看出,少年毛泽东由于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因此有着当时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忠君的爱国主义国家观念。其原因主要在于古代传统爱国主义的思想未形成完整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观,有的只是传统的王朝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王朝被混同于国家,君主成为国家的代名词,爱国必然表现为爱朝廷,忠君。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国家观导致了多数中国人爱国主义内涵的错位甚至扭曲。但是,聪慧而一生充满机遇的毛泽东很快迎来了另一个更好的求学机会,同时也促使了其国家观的第一次蜕变,也就是从传统国家观向现代化的国家观转变的起步。1911年春,经原东山学校的老师推荐,毛泽东进入省会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就读。他一面刻苦学习,同时“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他很快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反对清朝政府的救国宣传所吸引,卷入辛亥革命的浪潮。通过阅读《民立报》豐和其他一些革命宣传品,他了解到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并开始支持革命纲领,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同时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带头剪掉发辫。辛亥革命爆发后,充满革命热情的毛泽东还加入湖南湘军,参军半年。于是,在辛亥革命潮流的激荡下,毛泽东国家观思想就从拥护康梁的“君主立宪”,转变为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张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新政府”的国家观。
二、毛泽东的“茫乎未定”国家观阶段
将1913年—1920年这一阶段作为毛泽东国家观“茫乎未定”的阶段,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多种国家观思想互相交融、渗透,同时又是他对各种思想进行比较和选择的时期。由于其年龄和阅历以及其所处时局的复杂性和异常变动性等诸多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国家观显得易受影响而又“茫乎未定”。根据其思想特点的不同,可以将这一时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913年——1918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就读时期
自1913 年春直到1918年夏, 毛泽东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求学,师范五年半的学习生涯对于毛泽东国家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毛泽东读书涉猎广泛,他读了许多反映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成就的代表作,特别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社会进化改良的思想和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的温和的“观念造文明”和“哲学革命”的思想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国家观影响颇深。年轻的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并联系社会实际,获得了大量的新知识,受到了空前的新启示,培养了他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
首先,读书使他接受了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时在他的国家观中充满了唯心史观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要改造国家从而改变中国的危境,就必须首先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当毛泽东痛心地看到中国落后,民智淤塞的景象时,他认为民智不开才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他分析说:“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有大哲学家,大伦理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1917年8月1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人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形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这里的大本大源是指宇宙真理。”这就是说,救国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人心,要用“大本大源”去从根本上变换国民之思想,如此人民才能幸福,国家方才能实现强盛。
其次,毛泽东不满足于书本知识,他认为自己阅历较少,对于社会、国家真正的理解还很欠缺,因此他决定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中国问题的真正症结之所在。他以游学的形式了解社会,同时也从这项实践中了解到了社会上许多不公平的事情,他说: “照我自己的经验看,联系在湘乡、韶山一带看的,一般人的生活都过的不好”,这是“不合理的现象”。这时毛泽东的国家观表明了他已然能通过掌握资产阶级学说的积极思想来反观中国社会现实,他看到了不合理的现象,但遗憾的是他还未懂得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释这些不合理现象,当然也不会看出隐藏在不合理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阶级压迫。
因此,这一时期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运用哲学革命和教育普及作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这时的他认为国家的本质是宇宙真理,最深切的表现便是他主张“观念造文明”,认为观念是历史的动力,历史只是观念的实现。要改造社会必须从观念革命的点滴教化入手,只有通过这样一种途径才能建构新国家。总的来说,由于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的这种国家观还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国家观。特别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渴望“巨夫伟人”来拯救国家,这一点也表明了他尚未形成运用人民力量建设国家的观点,从中还透出其对人民群众创造力的忽视。当然,我们不应苛求年轻的毛泽东,这也许是他出于对人民迷信、愚昧、落后、麻木的忧虑,故而在谁担当建立国家的重任上更倾向于英雄,显现出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的特点。
(二)1918年夏——1919年春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1918年6月下旬,已调往北京的杨昌济先生来信劝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学习,促成了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在北京期间,他广泛接触到各种新思潮,其国家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他的国家观思想也表现出混乱矛盾的一面。
首先,这种急剧变化表现在他的政治思想越来越走向激进,沉迷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国家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很有市场,还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派别。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期间,也读到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这时的他正适逢年少轻狂的年纪,又具湖南人正直刚烈的秉性,由于他看到和接触到了不少的社会黑暗,对当局政治也倍感失望,而盛行的无政府主义在反对强权方面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很能振奋人心,因此毛泽东很快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度很是热衷。
其次,这次北京之行使他开阔了眼界,读到了许多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思想。这时的毛泽东虽没有完全认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思想,但是他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思潮是历史的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 “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豓同时也许是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思潮“软化”的缘故,毛泽东国家观思想中亦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特别重要的“民众联合”的思想,这时的他对于国家主体力量的认识发生了新变化,开始了由英雄史观向人民观的转变。1919 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民众大联合》的文章, 表达了他关于改造社会和国家的基本设想以及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国家与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应该是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真正力量,是决定一切社会变革成败的关键。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方法,毛泽东认为要先从小联合入手,由许多的小联合进而为一种大的联合,在各阶层人民利益联合的基础上,逐渐实现民众的大联合。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他后来提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家观思想的最初萌芽。
这次北京之行,并未使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真正转变,但却使他踏上了由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道路上。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条转变道路中,尽管他肯定社会主义思潮,且承认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主张民众联合起来反抗暴政。但是他却又直接表明自己在建设国家的方法上,不赞成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在打倒强权、建设国家的问题上,他也倾向于“无血革命”的民众大联合。 显然,这时毛泽东的国家观思想更钟情于克鲁泡特金温和的、非暴力的不流血革命的观点及无政府主义观点。
(三)1919年冬——1920年秋期间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和湖南自治运动
如果说第一次北京之行,毛泽东的国家观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吸收和探讨的时期,那么,第二次北京之行和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则是毛泽东的种种国家观思想接受实践验证的阶段。第二次北京之行是为了进行“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则是为了“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豖。1919年冬至1920年秋所进行的这两次运动,使得摆在他面前的不仅有一个同“武装到牙齿”的军阀张敬尧的斗争问题,还有一个驱张之后如何建设湖南的问题。面对种种严峻的现实考验,毛泽东的国家观又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毛泽东逐渐认识到任何无政府主义的空谈都是无济于事的。另一方面,他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又成为了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拥护者,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纲领,要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这次运动奠定了毛泽东国家观向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转变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第二次北京之行期间,一方面,毛泽东带领驱张代表团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在短短数月内,他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苏俄情况的书刊、文章。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他去《平民通信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就发现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右边还有其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豗尽管第二次北京之行期间,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仍采取比较和研究的态度,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信中所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豘但是无政府主义在他的脑中已经开始动摇。一是毛泽东此次“赴京驱张”已表明了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不同。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从事任何实际的政治运动,而他则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反动统治者作斗争。二是当他投入到实际的斗争中之后,更是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无用。在1920年3月12日,他寄给黎锦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中,他不仅承认“省长”、“县知事”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承认“军队”和警察存在的必要性。豙这些都是属于无政府主义绝对不能认可的法定之权利范畴。因此,这些都标志着毛泽东从反对强权且否定国家,到赞成强权且肯定国家的重大转折。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在发动湖南民主自治的运动中提出了“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中提出,以推倒武力及实行民治为两大纲领;以废督、裁兵,达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银行民办、发展交通、教育独立、地方自治及保障人民权利,达到实现民治之目的,创建一个人民自觉、自治的国家体制。首先,毛泽东在分析湖南和全国的政治形势时指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放环伺欲来”,“中国的民治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内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有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因此,拯救湖南的惟一方法不是维护军阀统治的政治体制,而是实行“各省自决主义”,重组政治机构。其次,毛泽东对未来的“湖南共和国” 作了具体构想: 第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湖南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是实现“人民的民主”的国家。第二,建立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民主共和政体。第三,国家公共管理权力由执政党和在野党相互制衡。第四,国家必具有一定数量的、只作为维护“湖南共和国”主权统治的军队,而非统治人民的暴力机器。由此可见, 毛泽东所构想的理想国家,在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方面体现了国家权力是由人民掌握的,人民有了普遍的选举权,可以视为他日后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萌芽。但是,在国家政权组织方式上,年轻的毛泽东选择了西方的议会制和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这样的国家权力运转机制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权力机制的翻版,他所构想的“湖南共和国”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模式。尽管“湖南共和国”(下转第191页)(上接第183页)的模式没有超出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理论范围而且失败了,但它在毛泽东早期国家观思想中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之确立
1920年冬,在深刻反省了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后,毛泽东的国家观也随之很快发生了质的转变。湖南自治的经验和教训,使他认清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认识到了只有接受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树立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并通过群众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才能对国家和社会实行真正的改造。
从1920 年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到1921 年春这一时期,毛泽东与远在法国的蔡和森、萧子升鸿雁传书,探讨了国家暴力革命等问题。毛泽东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的信件中的言论,不仅是他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标志,同时也是其崭新国家观思想确立的标志。在信中,他支持蔡和森的观点,主张用暴力和阶级斗争推翻反动统治以改造国家社会。肯定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思想的确立,基于他拥有以下几种主张:首先,毛泽东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才能指导中国革命和未来的建设。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决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豛要“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必须“固然要有一斑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而且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豜其次,毛泽东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 才能担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建立和建设国家的重任。蔡和森多次鼓励毛泽东“我愿你准备俄国的十月革命”,“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毛泽东完全同意蔡和森的意见,“先要建立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豝最后,毛泽东主张只有用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只有采取“阶级战争”、“劳农专政”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
青年毛泽东国家观嬗变的历程,是他接受多种国家观思想,同时又对这些思想进行艰难甄别的历程。毛泽东为探寻救国之路,“他走完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世界上许多探求真理的思想家,特别使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所走过的路程。从孔孟儒家、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从赫胥黎、斯宾塞尔宣扬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至托尔斯泰主义和日本的新村主义,他都有深浅不同的接触和研究”,豞他在接受任何一种思想时,都不会完全地继承,而是对照现实反复地思考、甄别,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