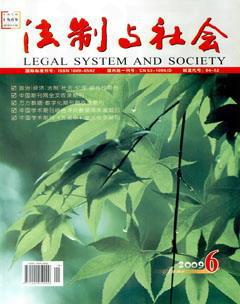比较法方法之辨析
刘芝秀
摘要比较法研究中,根据研究目的裁减研究对象的现象很突出,不利于深入了解比较对象。比较法中的功能比较和文化比较两种基本方法都有其弱点:功能比较易于流入形式化,文化比较则容易陷入对象的迷阵中。本文指出必须取长补短,采取一种“整体观下的目的性”,统率功能比较和文化比较,以一种有选择、有重点同时又兼顾大局的态度进行比较法研究。
关键词比较法方法功能比较文化比较目的性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001-02
与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中的比较研究不同,比较法研究是“一项规范性和政策导向的事业”,①不可避免地采纳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如同德国一代法学巨匠耶林(RudolfvonJhering)在其巨著《罗马法精神》(GeistdesromischenRechts)中所言:“外国法制之继受与国家无关,仅是合乎目的性及需要之问题而已。如果自家所有的,同属完善或更佳,自然不必远求。惟若有人以奎宁皮药草非长于自己庭院而拒绝使用,则愚蠢至极。”②——可以说,一种合乎目的性的“拿来主义”研究方法已经成长为比较法学研究的主流。
然而,比较法学因此陷入困境:一方面,目的是比较法学中不可或缺的指导,如果没有目的性的指导,如何知道比较什么?为什么而比较?但是,另一方面,过强的目的预设又损害研究的真实性,因为其一,目的性容易将研究对象削足适履;其二,过于坚持目的很容易忽略研究对象的细微精奥。本文认为这种困境正是比较法方法中主客体二元紧张的难题,即比较法研究者主体的主观目的性与研究对象客体的客观实在性之间存在对立和紧张。本文将粗略思考这样一种解困之道:在一种整体观下的目的性的指导下,结合文化比较与功能比较两种方法,缓解主客体二元的紧张。
比较法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文化比较和功能比较。这两方法各有其优长和缺陷,在具体研究中应当得到小心对待。
文化人类学者对比较法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法律的比较研究路径]还能变成,从稍具实践的角度看,一种在某一更集中的问题上(比如规范之根据与事实之说明间的关系,或者规范之说明与事实之根据间的关系)完成这种阐释学的大努力(grandjete)。”③
对于强调文化是一种“意义之网”的人类学家而言,比較研究所关心的意义,是通过把行动置于更大的“分类甄别意指系统”中进行的观察,在这种观察中,不是削足适履地“解释”研究对象,而是“理解”其自身所处环境的意义。
这里以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的一项研究为例说明文化比较的意义。安守廉教授指出,长久以来,学者们都错误地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的一些禁止盗印官方文书、盗印他人典籍的法令当成现代知识产权的萌芽。事实上,如果充分考虑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可以发现,上述所有的禁止法令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即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而实施的,虽然现实中也起到保护作者的版权、创作等等作用,但是制度设计绝对没有在这方面的初衷;而且,同样只要充分考虑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会发现古代文人对知识的继受,重视的是薪火相传的传统和过去(past)的圣贤之言,丝毫没有标榜自我创新的意思,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保护作者的知识创新似乎是没有必要的。因此,所谓“现代知识产权在古代中国的萌芽”这个命题没有太大的学术意义④。安守廉教授的这项研究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文化研究的极佳实例,即将视野放进研究对象所处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中,充分理解其自身的逻辑,绝不能削足适履地“剪裁”对象,更不能为了现实的目的任意给研究对象附加一些“意义”。
不过,必须注意,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应用于规模小、同质性高、共识未遭破坏的村落共同体与应用于幅员广阔、变动频仍、难于形成共识的社会,其效果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即使在村落共同体中,人们的认识也可能千差万别,比如,对“革命党”的认识,阿Q与“假洋鬼子”不一样,和吴妈也不会一样。所以,坚持文化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很有可能只满足于给读者展现一幅生动复杂的生活活剧,不能够给出一个相对明晰的指导路径,当为了“学习和借鉴”而进行比较法研究时,文化比较所从事的工作只是第一步而已,更艰巨、更有实用价值的分析工作还远远没有展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帕森斯创造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方法用以分析社会,提出适应环境、实现目的、达到综合、维持结构四个基本功能要件(AGIL)的系统分析框架⑤。利用由此发展起来的方法,通过功能性的比较,分析中介、媒体的作用,寻找功能替代项,似乎可以超越无法作结论的价值评判,同时能够给工作的改善提供指导。在中国学者中,季卫东教授对功能主义方法有着深刻的体会,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研究简约观察功能主义方法的优长和局限。法律试行的作法一向被认为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种独特作法。由于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的举措是史无前例的,一切改革都处在摸索过程中,为市场建设提供制度根基的法制建设也不得不在摸索中前进,于是立法上有“成熟一部,制定一部”的指导思想,现实中有法律试行、暂行规定等等措施。这种与“法治系统工程”相悖的作法,引起许多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现实的作法,应该得到重视,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作法,会损害法治的权威。季卫东超出这些有关“法治价值”、“权威”的争执,应用功能主义的方法,比较中国立法中法律试行与美国试验主义法学的异同,从现实的作法中提炼出中国法律体系的反思性因素,尤其是从功能的角度看待试行机制对构建法治秩序可能具有的优势和可能产生的危害,强调法律试行中的试错机制、民主参与机制等,最后主张在程序理性的框架之内整合法律试行的反思因素,将恣意转化为自由选择⑥。应用功能主义理论分析现实,他的研究显得相当细致,深入了对象的机体之内,而且有导向、有批判,并不以“存在即合理”为原则。
当然,功能比较也不是万全之策。功能主义将整个社会视为一个体系来看,然后通过将这个社会化解成部分对整体、整体对目标的功能作用,力图确定一套函数或指标以比较各个不同的社会,这种方法有极大的局限性。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是美国惟一的一门社会理论,指导着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这套理论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态当作了可以普适化的真理,所确定的社会功能分项几乎都着眼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情况,忽视了多样性发展的可能。同时,功能主义进路倾向于静态地描绘社会,将其用于指导第三世界的法制现代化改革时,无法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外国资本和本国政治、军事力量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运行的复杂动态⑦。
比较法研究必须综合文化比较(侧重于理解客观对象)和功能比较(侧重于调试主观目的)两种方法。
比较的方法无论是历史的比较,或是横向的比较⑧,都存在一个如何安排主客体关系的问题:要么主体支配客体,使得对客体的研究合乎自己的需要(用比较法哲学家格雷·多西的术语讲,这是一种“认知控制”的比较方法),要么听任客体支配主体,使得客体神圣化,成为反过来宰制主体的支配性话语。在这种艰难的比较中,既不能过于突现目的的作用,又不能将目的完全抛弃。有限制地使用目的,或许不失为一种良策。问题是用什么来限制目的?我们发现,文化比较方法的难点在于,文化研究首先要求深入研究对象的内部,然而进入内部之后却发现,该对象各部分对整体的认知存在千差万别的差异,从而造成“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尴尬局面;功能比较的难点在于,无法保证参照物的整体性,要么流于泛泛的横向比较,要么将参照物化整为零,丧失整体性。这二者的缺陷正好都与一种整体性的概念有关,可以将之与目的导向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有限制的目的论:“整体观下的目的性”(holismofpurpose)。
在主观者目的和研究对象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影响了比较法方法的应用,法国社会学家路易·迪蒙对此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与被观察的社会都可能有A和B两种因素,但是,在一个社会里是A从属于B,在另一个社会里则是B从属于A,于是进行简单地对应比较就会不妥,必须将之与各自的等级系列整体相联系,并且保持事实与价值的整体联系性,才能做出有益的比较⑨。这就是一种“整体性”的比较思路,即将主体的目的和研究对象分别放在各自的等级序列里,不是将个别元素挑出来作比较,而是用整体与整体进行比较,目的在其中是作为切入口,也是作为重点指引。按照这样的比较思路,比较法的任何课题都是文化价值、历史传统、现状认识、未来预想的综合比较。同时,由于有目的的存在,这类比较又不会落入空泛,而是围绕着中心进行的思维发散式的比较。就目的观念在整体环境中的地位而言,社会哲学家温奇更明确地指出:“观念和处境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关系。观念是通过它在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来获得意义的。”⑩依此说法,目的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参与整体环境的塑造,在指导认识整体的同时也接受整体的修正。可以说,整体性的目的观打破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将一切有形的、无形的、文字的、行动的、思想的元素都纳入比较之列。
就此而言,首先,整体观下的目的性是为了突出重点,可以突出研究对象的某个方面,将其定为重点,从而防止文化研究在深入对象内部之后迷失在对象中的无所适从。
其次,整体观下的目的性是开放的、流动的,可以加强研究者的自主性,能保证有相当针对性地切入研究对象的内部,同时又通过整体性敦促主体对目的进行自我反思,不断地调试目的的指向,从而防止功能比较在将参照物化整为零之后形成不了系统的看法。
再次,文化比较因为在对象的意义系统中作业,反过来可以修正目的性裁减对象的弊端;功能比较因为分拆整体成为部分,又以功能性将部分与整体紧密联系,反过来可以避免目的性忽略对象细节的不足,然后将这两种方法得来的结果,重新放在整体性的关照下检查,从而得出比较全面、踏实的研究结论。
最后,在整体观下的目的性的领导之下,我们看到文化比较的意义甄别系统和功能比较的功能要件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即将研究对象的内部认知、共识、结构、功能统合在研究者的主观需要下,形成了一个兼具动态变化和静态功能的综合体,为法律制度的比较和学习借鉴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