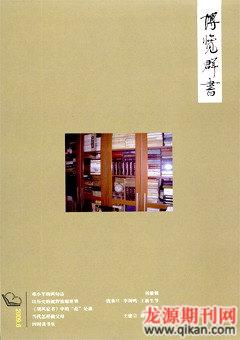朱家溍:“蜗居”中的人生
陆 昕
我祖父陆宗达和朱家济先生(文物学家、书法家)民国时在北大为同学,志趣相投,感情甚好。并由家济先生而与他的弟弟们也相往来,即二弟家濂,三弟家源,四弟家溍。家济先生后来去了浙江杭州,很难见面,只好书信往来。以后朱家浯先生和祖父过往较为密切,所以我也对家溍先生较为了解。今将闲言琐事笔于纸上,以为纪念。
我去朱先生家时,朱先生兄弟三人共居于南锣鼓巷的炒豆胡同,居所东边墙上挂一块牌子,上书“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僧王府”。与朱先生闲聊时,朱先生说他1914年出生于北京东城西堂子胡同,九岁时,迁居帽儿胡同,朱先生对帽儿胡同的房子印象很深。他说,那所院子共有房屋百十来问,五进院落,并有一个大花园。此宅原是同治年间大学士文煜的府第,民国初年,文煜的后人将它卖给了当时的代总统冯国璋。再后来,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从冯的后人手中租住了这所宅子。朱文钧祖籍浙江萧山,其曾祖朱凤标由翰林历官至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人称“萧山相国”。朱文钧光绪末年游学英法,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归国后,历任财政参事,盐务署厅长。因他酷爱文物且收藏极富,从故宫博物院创立之初便被聘为专门委员。
朱先生字季黄,行四。1937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当时祖父正在辅仁教音韵训诂之学。朱先生曾回忆说:“陆宗达和大哥家济是同学,又是极要好的朋友,对我也很好。我的关于小学的基础全仗陆大哥当年打得好,受益匪浅。”抗战爆发后,朱先生不愿在沦陷区读书,于是携夫人经过一段千难万险并险些遇难的旅途,来到后方重庆参加抗战的实际工作,在粮食部任专员,具体工作在粮食部储备司,后来又由粮食部借调到故宫帮助做展览工作。抗战胜利后,由四川归来,便直接去故宫上班,南马衡院长分配到古物馆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算个老故宫了。
闲聊往事,朱先生说,解放初期,“三反”运动开始,故宫博物院全体职工一律不准回家,接受审查。那时阶级斗争讲究家庭出身,而解放前能进入故宫的人又不可能有工农家庭劳动人民,于是故宫当时所有职工都先被假定为有问题,于神武门广场集合,事先已经准备好大卡车,由公安人员点名押送上车,分为两队,一队开往白云观附近的公安学校,另一队开往东岳庙的公安学校。八人一间宿舍,交代历史和“三反”问题。从2月底到5月底,大多数人作了结论释放,而先生却不在此列。原来,在东岳庙期间,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交代自己从故宫中“偷”了什么,没有可交代的就被看作“拒不交代”。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家知道只要“就坡下驴”,低头认罪,也就“过关”,并不真要如何。但先生较了真,认为自己没干过的事儿怎能承认,不能自己给自己栽赃。再说如果承认偷了,交不出来怎么办?于是不肯“认罪”。这样过了两个多月,他和另外“态度不好”的7个人被关进看守所,每日作些轻微劳动,听候继续调查。这样又过了一年十个月,1954年4月1日才被释放回家。这期间,先生说:“有一天我正在拘留所干活儿,有个一块儿的神神秘秘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有个穿军装的点名道姓地要见你,是个年轻人。我一听也有点害一响,心想是不是要关监狱了。等那人来了,一瞧,原来是你父亲。他那时在北京公安学校当校长秘书。他见我就说,今天特意过来看看我。还关照说虽然他不相信我会有什么偷盗行为,但这回上边决心很大,别太较真儿。后来我想想也是,当时那形势,用现在的话说,叫‘顽抗下去,死路一条。所以后来我也就不那么‘顽固了。我还记得我到家那天已经是晚上,我在外头一打门,有个表姐来开门,门缝一瞧是我,并没马上开。我们都好京戏,她在门里头唱了一句《打渔杀家》的戏词,‘你退后一步。我退了一步。她又唱‘你再退后一步。我又退了一步。她还唱‘你再退后一步。我已经退到对面墙了,于是也用戏中词回唱‘后边已经无有路了。她这才把门打开,说‘我就知道,不撞墙你是不回头。”
先生“文革”中从干校回来后,有两年奉命“退休”。那时我祖父正好也从干校返京,奉命编词典,空闲时间也较多。先生常来我家,和祖父谈天说地,谈些旧人旧事,印象中,谈京剧昆曲的时候不少,还总评议过去那些演员的技艺和佚事。有时说得高兴了,先生还会站起身,摆个姿势。他们都酷爱抽烟,先生一来,家里就烟雾迷漫,不抽烟的人在旁边呆一会儿也就会满身烟味儿。
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导演李翰祥到北京拍电影《垂帘听政》。对于当时“八个样板戏”过8年的中国百姓来说,算个文化大事。李翰祥聘请先生作顾问,请教有关历史及故宫的知识,并将先生的名字打在片头。电影一出,轰动天下,先生也随即广为人知。不过电影毕竟与历史不同,引起争议也就颇为不少,有些议论认为先生没把好关。
社科院文研所的吴晓铃先生和祖父也是老朋友,家住得也近。他每天早晨起得早,从校场二条的家出来,过宣外大街,一蹓趾就是西琉璃厂西头我家,所以有段时间,常过来和祖父聊天。有天早晨,我和祖父刚起,吴先生就来了,聊了一会儿,他说:“季黄(朱先生字季黄)这是怎么顾的问,您看那《垂帘听政》拍的,尽胡编乱造。李翰祥外行,他可不外行啊……”祖父从来不看电影,也随着哼哼哈哈。正说得热闹,没想到朱先生也来了。因为是熟人,所以直接登堂入室,正好从外间听见。于是一掀帘子进了里间,对吴先生笑道:“大哥,这事可不能怨我,我说人家得听呀!我看他不怎么听我的意见,就说,那你把我这顾问的名字撤了,可人家还是不听,我也没办法!”吴先生搞民间文艺研究,与戏剧、相声演员来往十分密切,尤其和侯宝林先生过从多。有次朱先生和我闲聊时说:“他(指吴先生)跟我见面时,老说宝林这,宝林那,跟宝林又去了哪儿哪儿。我还奇怪,我们这些熟人里边,没有叫宝林的啊。一问,原来是侯宝林!”
先生时有外出交流的时候。他去香港,别人说,那时去香港一趟不容易,一块儿的人都抓紧时间逛街购物,惟独先生并不怎么上街,只在宾馆房间休息。我问为什么,先生一时间还被我问愣了,想了想,说:“香港有什么可看的?除了楼就是楼,没什么古迹。要说购物,我是一点兴趣没有,所以也就在宾馆里呆着,看看书。”
先生的兴趣主要在文物和图书上,他认为自己最成功的一件事是编了《国宝》这部文物图集。这部图集由先生主编,费了很大心血,出版后深得好评,并被国家领导人选作馈赠外国首脑的礼物之一。不过除了研究传统文化,先生的生活和乐趣也非常丰富。
先生晚年自己所居的两间小屋应该是西边正房的两间耳房,穿外间小屋而过,是西南角的一块空地,方圆二十多平米,是个小小天井。里面栽花种草,植树架藤,有豆架,有虫鸣。若从里屋的窗户向外望,刚好面对这一小小庭院。春花秋月,雪夜霜晨,
时时观赏,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先生说:“故宫也给我分了单元房,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儿方便好多,起码卫生设施全。可我还舍不得离开这儿,就为了这个小角落,可以跟自然沟通。”
其实,我倒觉得先生还没说出另一半,那就是里屋的陈设。中间一张四方桌,紫檀的,临窗一张长条形书案,红木的,桌上陈设有明代理学家陈白沙的砚台,清刘墉亲自刻铭的紫檀笔筒以及纪晓岚的笔搁。先生逐样介绍后,特意强调,“紫檀也分不同等级,我这个笔筒的紫檀最好,比桌子的紫檀可强。”因为我家有个红木桌,先生又教我,“买个猪毛刷子天天来回蹭,又光又亮,保护木头。”说着,他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猪毛刷子,一来一回在桌子上蹭起来,还说:“我每天也拿蹭桌子来活动身体,挺好。”坐于窗前,眺望庭院,真感到外边春风桃李,里边几案精严,称得上天造地设。
先生为人甚随和,人来求字,很少拒绝。若是熟人,往往“立等可取”。不过先生写字时,不能旁边有人看。有次我去找先生写字,说完告辞,准备过几天来。不料先生说:“你要没事儿,坐这外间等会儿,我去里间写,一会儿就完。不过我写字时旁边不能有人,旁边人一围,我就写不好。”
先生外间屋里有书柜,柜中有许多善本古籍,墙上有字画和先生的戏装照。其中一张启功先生题的“蜗居”引起我的兴趣。先生解释“蜗居”的含义时,说:“这不仅仅指表面上我的居室,而是我这样认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窝在这儿了,也就快乐了。”
转眼之间,先生下世已多年,而音容笑貌,恍在眼前。其所居南锣鼓巷,已被规划为一片旅游文化区。前不久,我去那儿,特意到先生家门口,见两扇斑剥锈蚀的木门依然如旧,小小门铃也一如既往,恍惚中竟又似多年前按响右侧门铃,不久便听见先生时时夹杂着咳嗽的脚步声及看见开门后的笑容。
徘徊在先生门口,我思绪纷飞。我没有按门铃,是因为我不想再进先生的“蜗居”。然而我不想进的原因,除去睹物伤情的常情外,还因为我此刻想好好琢磨先生曾经的教诲。
先生对“蜗居”的解释是“如果你认为自己‘窝在这儿了,也就快乐了!”
“蜗居”是方寸之地,而人生由于种种不可逆料的情境,也常常会在某时“窝”在某个“方寸之地”。自然和社会就是这样互为启示。如果能看清楚,便可顺势而为,不会徒增烦恼。再者,海阔天空固然可以鸟飞鱼跃,方寸之地就不能腾转挪移?海阔天空也好,方寸之地也罢,还看人如何运用。高明的人,无为变做有为;愚笨的人,有为化做无为。即便平平如我者,由此而明晰人生后,也会得到那种超出红尘之外的快乐,那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