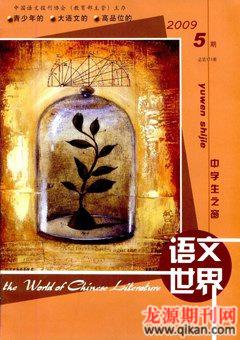获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的作家:陈染
张荣民
作家档案
陈染,1962生于北京。幼年学习音乐,18岁兴趣转向文学。198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曾在北京做过四年半的大学中文系教师,后调入中国作协作家出版社做编辑。曾在澳洲墨尔本的英国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等旅居生活和讲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诗、散文,以小说《世纪病》在文坛脱颖而出,被视为“纯文学”“先锋小说”严肃文学女作家中的最新代表。重要作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代表作《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私人生活》等。她以强烈的女性意识,不懈的探索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独特而重要的女性作家代表。曾获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等。她的小说在英、美、德、日等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均有出版和评介。根据她的小说《与往事干杯》改编的同名电影,被选为国际妇女大会参展电影。
作品选读
城市的弃儿
陈 染
不知不觉又是夏天了。仿佛是柔和晴朗的细风忽然之间把全身的血脉吹拂开来。我是在傍晚的斜阳之下,一低头,猛然间发见胳臂上众多的蓝色的血管,如同一条条欢畅的小河,清晰地凸起,蜿蜒在皮肤上。
夏天的傍晚总是令我惬意,在屋里关闭了一整天的我,每每这个时辰会悠闲地走到布满绿阴的街道上。我一会儿望望涌动的车流,一会儿又望望归家心切的人们在货摊上的讨价还价。我的脚步在夕阳照耀下瞬息万变的光影中漫无目的地移动。
一只猫忽然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是一只骨瘦如柴的流浪猫,它扬起脏脏的小脸用力冲我叫。我站住,环顾四周,发现这里有个小自行车铺,过来往去的人们司空见惯地从它身旁走过,没人驻足。而这只猫似乎从众多的人流里单单抓住了我,冲我乞求地叫个不停。
我觉得它一定是渴了,在要水喝。于是,我在路边的冷饮店给它买了一瓶矿泉水,又颇费周折地寻来一只盒子当容器,给它倒了一盒水。猫咪俯身轻描淡写地喝了几口水,又抬起头冲着我叫。我又想它可能是饿了,就飞快跑到马路对面一个小食品店买来肉肠,用手掰碎放在盒子里,它埋头吃着,吃得如同一只小推土机,风卷残云。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它,直到它吃饱了,才站起身。然后,我对它说了几句告别的话,转身欲离开。可是,它立刻跟上来,依然冲着我叫。
一个溜狗的妇女牵着她家的爱犬绕着猫咪走开了,那只狗狗皮毛光洁闪亮,神态倨傲,胖胖的腰身幸福地扭动。
我再一次俯下身,心疼地看着这只又脏又瘦干柴一般的猫咪。我知道,它对我最后的乞求是:要我带它回家!
可是……
我狠了狠心,转身走开了。它跟了我几步,坚持着表达它的愿望,我只得加快脚步。终于,猫咪失望地看着我的背影,慢慢停止了叫声。直到另一个路人在它身边停下脚步,猫咪又扬起它脏脏的小脸开始了新一轮乞求的叫声。
我走出去很远,回过头来看它,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对不起,猫咪!非常对不起!我无法带你回家!
天色慢慢暗淡下来,远处的楼群已有零星的灯光爬上人家的窗户,更远处的天空居然浮现了多日不见的云朵。晚风依旧和煦舒朗,小路两旁浓郁的绿叶依旧摇荡出平静的刷刷声。可是,这声音在我听来仿佛一声声叹息和啜泣,我出门时的好心情已经荡然无存,完全湮没在一种莫名的沉重当中。我情绪失落、忧心忡忡地走回家。
第二天黄昏时候,我又鬼使神差来到自行车铺一带。
我先是远远地看见车铺外边的几辆自行车车缝间的水泥地上丢着一块脏抹布,待走到近来,才看清那块抹布就是昨天的猫咪,它酣酣地睡在不洁净的洋灰地上,身子蜷成一团,瘪瘪的小肚皮一起一伏的。它身边不远处,有几根干干的带鱼刺在地上丢着。
我心里又是欣慰,又是发堵。想起我家那备受宠爱的爱犬三三,经常吃得小肚子溜圆,舒展地睡在干净柔软的席子上,甚至我不得不经常给它乳酶生吃,帮助它消化,这时我忽然发现:
这个世界别说是人,就是动物也无法公平啊!
我没有叫醒猫咪。只是厚着脸皮上前与车铺的小老板搭讪,也忘记了应该先夸赞他家的自行车,就直奔主题说起这只猫咪。小老板看上去挺善良,热情地与我搭话。他说,每天都给它剩饭剩菜吃,不然早就饿死了。说这只猫已经在这一带很长时间了。我诚恳地谢了他,并请他每天一定给猫咪一些水喝,我说我会经常送一些猫粮过来。我们互相说了谢谢之后,我便赶快逃开了。
街上依旧车水马龙、人流如梭。猫咪就在路旁鼎沸的噪声中沉沉酣睡,热风吹拂着它身上干枯的灰毛毛,如同一块舞动的脏抹布,又仿佛是一撮灰土,瞬息之间就会随风飘散,无影无踪,被这个城市遗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想等它醒来,让它再一次看着我无能地丢下它落荒而逃。
流浪猫已经成为众多城市的景观。负责环保的人们,你们在忙碌大事情的间隙,可曾听到那从城市的地角夹缝间升起的一缕缕微弱然而凄凉的叫声?
折断的时间
陈 染
早年,我曾在多处画册中看到过达利的《记忆的残痕》这幅画,画面上是三只时间完全停滞的柔软扭曲的钟表。记得当时我每次看到这幅画,内心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矛盾感,至于怎么个矛盾法,我一直没来得及深思与沉淀,匆匆忙忙地就被新的事物所冲刷和覆盖了,就像一朵浪花撞击另一朵浪花,转瞬之间便归复于平静,涌动的暗流便潜藏于深水之下。
据我对画面的表层理解,我想,达利似乎在倾诉一种对“原始记忆”的闪现和拉回的渴望;倘若再往潜意识深处探寻的话,根据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手表或钟表是一种规律和纪律的象征,那么也可理解为达利对现实秩序以及现实规则的一种破坏的欲求。
回忆起来,在我反复观看现代派画册、画展的那个时期,也正是我叛逆情绪最为饱满的青春期。那个时候,我对现实说“不”,对约定俗成的观念说“不”,对所有的束缚人精神的条条框框说“不”!按说,以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对于达利的《记忆的残痕》描绘出的弯折扭曲的钟表所蕴含的精神指向,是不应该感到别扭的。但是,我就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别扭。
随着岁月的流逝,更随着我对自己的本质的日渐清晰的理解,我恍然知道了这种内心的冲撞发生在哪里了——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我始终是一个不喜欢墨守成规、人云亦云的逆向思维者;但是,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常态下,我又是一个喜欢遵循秩序、规则和纪律的人,这种遵循甚而到达刻板的程度。比如,我喜欢恪守时间的朋友,并要求自己守约守时;我喜欢购物环境是明码标价的场所,不喜欢那种谁有本事谁砍价的浮动价格的游戏规则;习惯日常起居的规律化,不习惯恣意妄为、任性散漫;喜欢社会各种秩序的规范化、法律化,不喜欢见人行事的随意化、人制化……总之,我依赖于有“纪律”的日常状态,而这种“纪律”完全来自于一种自我的意愿和自我的束约。
一方面,是喜欢思想意识上的不安分和自由感;另一方面,又倾向于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上相对的秩序化和规范化。我想,现在回忆起来,早年达利那幅画带给我的内心冲突大致源于此吧。
其实,秩序和规则从来不是自由的对立面。所有的自由都是仰仗一定的制约而得以实现的。也可以说,没有制约,根本就没有自由!
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叫斯科特·派克,他曾说,“纪律是解决人生难题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有四点:不逞一时之强,承担责任,忠于真相,保持平衡”。青春年少之时,不懂得节制的我们也许会对此嗤之以鼻;时过境迁,当我们拥有了足够的岁月积淀之后,当铅锭一般沉甸甸的思绪堆在心头时,我们便恍然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超级链接
人民网与陈染关于文学的对话
人民网:《私人生活》一直被中国当代文学史誉为女性主义文学经典之作,它的广泛影响和所引发的激烈争议也使你成为“私人化写作”的肇始者。到了今天,你怎么看?
陈染:《私人生活》是我青春期时候的小说,青春是激情的敏感的也是痛苦的,有太多的忧戚与深思。此书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出版后,也有很大反响。
人民网:你怎么看待时下所谓的美女作家这个称呼和她们的写作?
陈染:这个话题可以从两方面说:第一,美女作家这个提法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而我是80年代出道的作家,所以从辈分上讲应该是“老前辈”大姐了,和她们的写作姿态也完全不同,真正文学界的作家、批评家们以及负责任的媒体记者,没有人把我纳入美女作家的行列。一些不大清楚文学发展脉络的媒体有时候为了炒作新闻,对稍有点姿色的女性作家统统推入“美女作家”行列,对大众造成了一些误导。第二,美女作家从事的是时尚类写作,而我对时尚一直是心怀警惕的人,时尚中有优秀的东西,也有糟粕的东西,良莠不齐。总之“美女作家”是新生事物,是我从事写作十余年后出现的,我不在这个群落中。而且,我一直觉得,是否漂亮与写作无关,请媒体不要再误导。
人民网:你觉得文学创作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是财富、名声还是其他的什么?
陈染:首先是我内心的一种喜爱,一种满足。当然,它也会带来一些财富。我觉得我现在过着一种感恩的生活,我希望人们不要在生活中总是怀揣着刻薄、仇恨、敌意等心理。“感恩的生活”不是肤浅怠惰,不是廉价的知足常乐,而是一种大气的从容的深刻的感情。
人民网:你怎么评价文学界的浮躁?你怎么看待各种文学奖?
陈染:文学界的确存在浮躁。但现在胡乱写书的并不见得是真正的作家。我不大介入文学界和文学以外的是非问题。关于各种文学奖我一直不想说什么,因为也许有的好作品歪打正着被评上奖了,不好乱说。但是现在的国内评奖内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不必看得过重。我最近看到李国文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要想获奖你得付出的各种奖级的(银子)价位,我觉得李国文前辈真是太幽默了。评奖问题我觉得有三点:一是主旋律作品,二是评委的文学价值取向和审美尺度,三是(也许还有)参奖者的十八门武艺,这几乎是最重要的,中国是一个“关系学”大国,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关系学如中国这样普及和发达。人家也很不容易啊,我心里很平衡。
人民网:与铁凝相比,你似乎是游离于体制之外,这对你的生活与写作有何影响,或者这仅是你的某种生活选择?
陈染:有不少作家都有官职,比如王蒙,他曾经出任中国文化部部长,女作家当中比如铁凝、舒婷、方方等等也都担任某些官职,这些作家都是我喜欢的朋友,他们说的都是“人话”,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我的情况是,我对人群有恐惧感,不太会交际,总有一种逃避感,这其实不是什么选择,是我的性格弱点使然吧。
人民网:最近在写作什么?
陈染:写得很少,总想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这很难。现在,写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我感觉,岁数越大,想说的话越少,经常是想一想之后,觉得不说(写)也罢,算了。也许是我提前“老了”,越来越理解张爱玲晚年只字不写、闭门索居。宏观上我对自己的未来是悲观的。虽然理论上讲,今天活着,还是笑着活是比较聪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