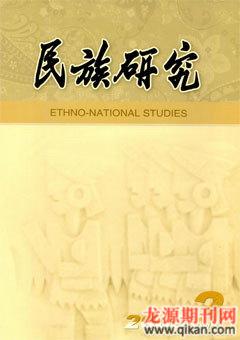汉赵国胡与屠各分治考
陈 勇
汉赵国高度军事化的政治组织,为十六国北朝军国体制之滥觞。汉赵国政治组织的军事化,又是脱胎于匈奴五部社会组织的部落化。汉赵国宗室诸王、司隶校尉、内史与单于、左右辅、都尉系统相配合,构成其军事化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对“胡汉分治”这一概念,则应作进一步的分析。汉赵国单干台所辖六夷之胡,其实是匈奴五部以外的杂胡。汉赵国两套军政合一管理系统并立,不仅是将六夷与汉人分治,也是将六夷与匈奴五部分治。汉赵国分治政策的推行,保证了入塞匈奴帝国核心部族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匈奴五部与六夷携手,一度形成震慑中原的强大武力。屠各刘渊之所以能够在五胡中率先建国,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原因。
关键词:汉赵国胡屠各匈奴
作者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一、汉赵国胡与屠各的区别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载:“元海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聪为大司马、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西。”唐长孺先生说:“这个单于台之台即台省之台,乃是与统治汉族之尚书台并列的统治六夷机构。”《晋书》卷102《刘聪载记》载:以皇太弟义“领大单于”,“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可以为唐说之据。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载:“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前赵国单于台“主六夷”,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胡、羯、鲜卑、氐、羌”被纳入六夷之中,是不言而喻的。前赵国六夷之中有胡,《刘曜载记》此条所言甚明。问题在于,汉赵国的屠各是否也称胡,被纳入六夷之中而归大单于管辖?
陈寅恪先生说:“汉国(前赵)以单于台管领胡人,单于台下有左右单于辅,单于辅分主六夷部落。”又说:“六夷部落因为要用于作战,往往被集中于京邑单于台下,特别是要充当禁军的本部人,更非集中于京邑不可。”就是将“胡人”、“六夷部落”乃至汉赵国的“本部人”等量齐观,我们知道,汉赵国的“本部人”正是五部屠各。
另如周一良师说:刘氏倡大单于制,石氏因之。“以弟或子领大单于,专总六夷。其下所属官亦用杂种,自成系统,与皇帝系统下之汉官不相杂厕。以五胡豪杰统领,故能慑服诸部,获其拥戴。不与汉人杂厕,故得保持其劲悍之风,以供征战”。也是以“六夷”、“五胡豪杰”与“汉人”、“汉官”对举,认定屠各在五胡、六夷之中,归大单于及其本族豪杰统领。
周伟洲先生说:“六夷中的‘胡,具体指匈奴,主要是那些仍保持着游牧生活,汉化不深的匈奴部落。如……黑匿郁鞠部等。至于早已入居内地,汉化既深,且已从事农耕的匈奴,则不在此列。”是一项新颖的见解,可他接下来又说:“汉赵的军队大部分出于单于台所统之六夷之中,故大单于基本掌握了汉赵的军队。”却令人困惑。因为我们知道:汉赵国军队的核心正是五部屠各。周氏又说:“单于台统治的人民,是‘六夷,即除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而且主要是以游牧或畜牧业为生的、以部落为组织形式的少数民族。”“六夷中的‘胡,具体指匈奴及其相关的诸杂胡(卢水胡、铁弗、独孤、赀虏等)”。单于台的职责,就是“专门管理国内除汉族(晋人)之外其它少数民族”。更是明确将当时的匈奴全部归入单于台所领六夷之中,与其前说有所抵牾。
事实上,至迟到西晋末年刘渊起兵前夕,匈奴五部与胡已有区别。《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刘宣等“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引者按:指成都王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晋书》此条以“五部”与“宜阳诸胡”对举,不仅表现二者地域的差异,而且说明“五部”并不与“宜阳诸胡”一道称“胡”。
曹魏末年五部都尉所统约三万落,一般估计有二十万人以上;晋武帝元康九年(299)江统撰《徙戎论》,又称“五部之众户至数万”。可是,按照刘宣等人的说法,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刘渊策动五部起兵时仅有二万多人,与曹魏末年及西晋中期的五部人口相差甚远。汉国建国之际的“屠各”,究竟是指“五部”全体,还是仅指其核心的部分?尚难断言。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屠各刘氏与南匈奴贵族,即那批见于记载的“屠各”族人,正是五部的骨干。如五部已不称“胡”,则屠各也不会称“胡”。
《魏书》卷23《卫操传》载操为桓帝所立颂功德碑文,有“屠各匈奴,刘渊奸贼”两句。《魏书》卷95有《匈奴刘聪传》及《聪父渊、子粲、渊族子曜附传》,同卷又有《羯胡石勒传》及《勒子大雅、从子虎、虎子世、遵、鉴附传》。可见在与汉赵国邻接的鲜卑拓跋部的印象中,刘渊一族是匈奴,石勒一族则是羯胡而不是匈奴。匈奴本部的屠各与别部的羯胡及其他各种杂胡,是判然有别的。
《晋书·刘曜载记》“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两句,《魏书》卷95《匈奴刘聪传刘曜附传》作“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杂种为之”;《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两句,《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元熙元年,304)又作“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杂胡”。《魏书》中“胡”与羯、鲜卑、氐、羌并称“杂种”,是相对于匈奴本部的屠各而言的。换言之,魏收视为“杂种”的“胡”,应该就是杂胡。《通鉴》以“五部”与“杂胡”对举,断定“五部”不在“杂胡”之列。在司马温公看来,宜阳“诸胡”与“杂胡”也是一回事。
《晋书·刘曜载记》又载:“石勒遣石季龙率众四万,自轵关西人伐曜,河东应之者五十余县,进攻蒲阪。……闻季龙进据石门,续知勒自率大众已济,始议增荥阳戍,杜黄马关。俄而洛水候者与勒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曰:‘大胡自来邪?其众大小复如何?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曜色变,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南北十余里。”周一良师说:“此大胡谓石勒,乃与石虎相对而言。”刘曜称石勒为“大胡”,则刘曜本人不会以“大胡”自称。刘曜一族的刘渊、刘聪乃至其屠各族人,也不会以“胡”自称。谭其骧先生指出:“勒、虎诸载记辄称其种人曰胡,而前赵……诸主之载记则不然。”是一项敏锐的观察。
《晋书·刘聪载记》载:“时……客星历紫宫人于天狱而灭。太史令康相言于聪曰:‘……月为胡王,皇汉虽包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汉既据中原,历命所属,紫宫之异,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尽言。……”康氏为证明“胡王”与“皇汉”、“太阴之变”与“汉域”之间的联系,竟然要追溯南匈奴“世雄燕代,肇基北朔”的历史,显得颇费周章。究其缘由,就在于汉国本部的屠各已不称胡。这类事例证明:汉赵国的屠各与包括羯人在内的诸胡,此时有着确定的分野。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载:“勒伪称赵王……号胡为国人。”同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载:“太武殿画古贤悉变为胡。”又云:“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谭其骧先生说:“细玩文义,可
知凡此之谓胡,其义至狭,既非诸夷之泛称,即匈奴亦不在内,乃专指形状特异之后赵国人即羯人而言。……石勒统号胡为国人,既未尝分别是羯非羯,故史籍或曰‘胡,或曰‘羯,或曰‘胡羯,究其含义,亦无二致。”后赵之“胡”是否专指羯人,似乎还可以讨论。但谭先生上述意见,仍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笔者进而怀疑石勒、石虎载记所言之胡,“既非诸夷之泛称,即匈奴亦不在内,乃专指形状特异之后赵国人即羯人而言”,是沿袭汉赵国的观念;其“辄称其种人曰胡”,石勒并“统号胡为国人”,正是由于后赵“国人”的身份复杂,出自不同的部族或部落。这也衬托出一个重要事实:汉赵国中称胡的杂胡,与屠各(即谭先生所谓匈奴)并不相混。据此可以认定:汉赵国重建大单于制度,就是要将屠各与杂胡乃至六夷加以区分,纳入不同的行政、军事管理系统。
魏晋时的匈奴与杂胡,一般是不难区分的。《魏书》卷1《序纪》以“匈奴”与“杂胡”对举,就表明双方的部族迥然而异。《魏书·序纪》又说猗卢国内“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引者按:指石勒)种类”。另据《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载:“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谭其骧先生指出:“羌渠”是康居的新译,羯人则是“康居之居民降附匈奴”者。石勒一族是“匈奴别部”,这些“匈奴别部”又是“匈奴杂胡”或“杂胡”。“匈奴杂胡”或“杂胡”除“勒种类”外,还应该有其他种类,羯人与各种杂胡的界限,看来已相当模糊。唐长孺先生说:“晋人称羯常常泛指杂胡,并非专指羯室之胡。”原因也在这里。
西晋的“胡”与“杂胡”往往已无区别,我们对此也需留意。《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录郭钦晋武帝时上疏曰:“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曰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可与前引《刘元海载记》参见。郭氏以平阳、上党“胡骑”与“杂胡”互换,说明在晋人的眼里:平阳、上党之“胡”就是“杂胡”。《通鉴》将宜阳诸“胡”称为“杂胡”,也是言而有征的。
《晋书·北狄·匈奴传》又载:“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前引郭钦所言平阳、上党一带的“杂胡”,可能包含晋初归化的大水,塞泥、黑难诸部。大水,塞泥、黑难诸部人塞后,最初被安置在“河西故宜阳城下”。刘渊酝酿起兵时,告刘宣等“引会宜阳诸胡”,“宜阳诸胡”中也有大水,塞泥、黑难各部的后人。他们与扩散到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等地的“杂胡”,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部族或部落降晋时统称“塞外匈奴”,具有确定的匈奴身份,而到郭钦上疏时,他们却改称“杂胡”,失去了匈奴的资格。大水,塞泥、黑难诸部称谓的变更,揭示一个规律:魏晋时代称胡的部族或部落,大都经历了由匈奴到杂胡的异化过程。而《晋书·刘元海载记》以“五部”与“宜阳诸胡”对举,也就是以“匈奴”与“杂胡”对举,又表明刘渊建国前夕,屠各与“胡”或“杂胡”,在名义上已划清了界限。
《晋书·刘曜载记》载:“初,靳准之乱,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惊,资给衣马,遣子送之。曜对胤悲恸,嘉郁鞠忠款,署使持节、散骑常侍、忠义大将军、左贤王。”另据同书《北狄·匈奴传》载:太康八年(287),“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来降。”“育鞠”即“郁鞠”,疑“大豆得一育鞠”与“黑匿郁鞠”本为同部。大豆得一育鞠降晋而称“匈奴都督”,此人及其部落当时是被视为匈奴的。前赵“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桀为之”,已见前引,黑匿郁鞠任左贤王,其为“六夷”之“胡”无疑。前引周伟洲先生说,汉赵国六夷之胡主要指“那些仍保持着游牧生活,汉化不深的匈奴部落”,举黑匿郁鞠部为例,不详何据,但此事或许可以为魏晋匈奴到杂胡的异化,提供一则旁证。
《晋书·石勒载记上》载:“进据襄国。……上表于刘聪,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刘聪署勒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冀幽并营四州杂夷、征讨诸军事、冀州牧,进封本国上党郡公,邑五万户,开府、幽州牧、东夷校尉如故。”及石勒平幽州,刘聪又遣使“持节署勒大都督陕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侍中、使持节、开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钲黄钺,前后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刘聪所授诸官号中,“杂夷”、“东夷”及“东单于”的称谓涵义微妙,值得推敲。其中“杂夷”是相对于匈奴,即汉国本部的屠各而言的;“东夷”则是指幽、营两州的“杂夷”,主要是乌丸与鲜卑,也就是所谓“东胡”。与此对举的冀、并两州“杂夷”,主要又是指该地的杂胡。“东单于”是相对于“西单于”而言的,“西单于”即汉国单于台。我们说单于所辖杂胡与汉国本部的屠各分属不同系统,这也是一项重要证据。
二、汉赵国胡与屠各的分治
以往史家普遍认为:汉赵国恢复匈奴传统的单于制度,开十六国“胡汉分治”之先河。而在“胡汉分治”的政策之下,汉赵国的汉族人口归司隶、内史系统管理,其他少数族人口归大单于、单于辅、都尉系统管理。然而,本文上节已经说明:汉赵国单于台所辖六夷之胡,其实是屠各以外诸胡,也就是诸史称作“匈奴别部”或“匈奴别种”的杂胡。如此说不误,则我们对汉赵国的“胡汉分治”,就需要重新审视。笔者的想法是:汉赵国司隶、内史与大单于、单于辅、都尉两套系统的并置,不仅是将六夷与汉人分治,即史家常说的“胡汉分治”;而且是将六夷(包括杂胡)与匈奴(五部屠各)分治,比照“胡汉分治”的提法,也可以称为“胡胡分治”。
陈仲安、王素先生提出:汉赵国内有“三个相对独立的不同族属的集团”,即刘聪“本族”、“汉族人民”及“六夷部落”。其中刘聪“本族的军队”,是其“本国的核心力量”。吕一飞先生又提出:汉赵国的政治结构由三部分组成,“核心力量”是“南匈奴五部之众”,“准核心力量”是“其它胡族”,外围是“晋人(汉族)”。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近似,都是颇具启发性的。依陈、王之说,“汉族人民”与“六夷部落”(即吕氏所谓“晋人”、“汉族”与“其它胡族”),分属左右司隶、内史和单于左右辅、都尉两套系统。但刘聪“本族”(即吕氏所谓“南匈奴五部”)的行政、军事归属,陈、王、吕诸氏却未作解释。
另据黄烈先生说:“五部民不应属于单于左右辅所管的六夷范围,而应属于左右司隶所管的民户范围,与汉族人民同属编户齐民。”高敏先生又说:刘聪即位时“确定了两种形式的部落兵制”,其皇子所任大将军各配营兵,是“匈奴贵族、皇族”统领“匈奴本部”的部落兵形式;单于左右辅各主部落,则是“以六夷部落酋豪统治各少数民族的部落兵形式”。黄、高两说都认为汉赵国匈奴或屠各不归单于台管辖,但缺乏充分的论证。
以往已有史家注意到:汉赵国的行政机构,呈现出一种军事化的面貌。如唐长孺先生说:
“刘聪在其直接控制区域内建立了胡汉分治的军事化的制度以控制人民。”吕一飞先生又说:刘渊置单于台是“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用部落军事制的方式来管理六夷”。依循这样的思路:刘渊、刘聪所设大单于、单于辅、都尉系统,在行政管辖的同时,又发挥了军事管辖的职能。谷川道雄先生说:汉赵国的单于制与魏晋时期的五部制“颇有相通之处”,大概也是着眼于此的。魏末五部帅更名都尉,汉国六夷万落置一都尉,似乎并非巧合,此例证明魏晋时五部的屠各与汉国的六夷,同样具有军人身份;魏晋的五部与汉国的单于台,都是“军事化的制度”或“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然而,汉国的屠各是不是具有军人身份?与单于台并立的司隶、内史系统是不是“军事化的制度”或“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却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永嘉三年(刘渊河瑞元年,309)初,刘渊迁都平阳,其本部的屠各与陆续归汉的六夷及汉族人口,随之移居该地。汉国单于台设于平阳西郊,六夷二十万落也应在附近。另据《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刘和嗣位,卫尉西昌王刘锐、宗正呼延攸进言曰:“先帝不惟轻重之计,而使三王总强兵于内,大司马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为寄坐耳。此之祸难,未可测也,愿陛下早为之所。”此处“大司马”即大司马、大单于、楚王刘聪,周一良师解释说:“近郊指平阳西之单于台,十万劲卒则兼苞匈奴及以外诸种姓也。”大单于刘聪统领“匈奴以外诸种姓”即六夷,是可想而知的。但大司马刘聪麾下的“十万劲卒”之中,是否也有五部屠各即匈奴,却无从查考。
《晋书·刘聪载记》载:“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骑二万,屯于并州,以怀抚叛者。……河东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埋之……后乃钻土飞出,复食黍豆。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石越招之故也。”《通鉴》卷89系此事于晋愍帝建兴四年(刘聪麟嘉元年,316)七月。平阳的饥荒,导致司隶部民二十万户出逃。这些司隶部民此前聚居在平阳一带,毋庸置疑。《刘聪载记》又载:“(石勒部将)赵固、郭默攻其河东,至于绛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骑兵将军刘勋追讨之,杀万余人,固、默引归。”《通鉴》卷90系此事于晋元帝建武元年(刘聪麟嘉二年,317)底。右司隶部民“盗牧马”者三万余骑,其中显然包含大量游牧人群。但我们绝不能仅据此条,就说这些游牧人群都是屠各。事实上,按照刘宣等人在刘渊起兵前夕的估算:当时五部屠各的兵力仅有二万余人,已见前引,与刘聪时司隶部民四十万户所能提供的兵力,差距颇大。
《晋书·石勒载记上》载:石勒攻靳准于平阳,“准使卜泰送乘舆服御请和,勒与刘曜竞有招怀之计,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内无归曜之意,以挫其军势。曜潜与泰结盟,使还平阳宣慰诸屠各。勒疑泰与曜有谋,欲斩泰以速降之,诸将皆曰:‘今斩卜泰,准必不复降,就令泰宣汉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诛靳准,准必惧而速降矣。勒久乃从诸将议遣之。泰入平阳,与准将乔泰、马忠等起兵攻准,杀之,推靳明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传国六玺送于刘曜。勒……进军攻明……石季龙率幽、冀州兵会勒攻平阳。刘曜遣征东刘畅救明。……靳明率平阳之众奔于刘曜。”联系上下文可知,刘曜使卜泰“还平阳”的平阳,指的是平阳“城中”,此处为刘氏本部“诸屠各”所居之地。“靳明率平阳之众奔于刘曜”,《晋书-刘曜载记》作“明率平阳士女万五千归于曜”。“平阳之众”或“平阳士女”未必都是屠各,但应是以屠各为主的。汉国的屠各居于平阳城中,六夷居于平阳郊外,这种局面的形成,又与司隶、内史和大单于、单于辅、都尉两套系统并置,有着密切的联系。
《晋书·刘曜载记》载:石虎败前赵军于上邦,“执其伪太子熙、南阳王刘胤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入、秦雍大族九千人于襄国,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黄烈先生称文中“郡”为“部”字之讹。唐长孺先生则谓“五郡”系“沿用汉代五郡塞外之称”。《通鉴》卷94咸和四年(329)胡注曰:“五郡屠各,即匈奴五部之众。”说明这批被石勒坑杀的屠各,在名义上无论是“五郡”还是“五部”,其源头都出自五部,都是“匈奴五部之众”。黄烈先生说:“刘曜将相王公中最主要的是刘氏宗族,都遭到了屠杀和坑埋;五郡屠各也受到同样的待遇。”这是不错的。但他又说:五千屠各“只是屠各中的少数,主要应是指在刘曜朝廷中当官的”。所据却不详。唐长孺先生说这些遇害者“可能是刘曜带人关中的并州屠各”,更为可信。
《晋书·刘曜载记》中的五郡或五部屠各,与其他“关东流入”并举而有所不同,反映了汉赵国的族群划分,以及当时通行的族际观念。“刘曜带人关中的并州屠各”遭石勒集体屠戮,可信他们此前是聚族而居的,但这是否为汉国遗存的制度,还无法确定。《晋书·石勒载记上》载:靳准作乱,石勒发兵讨之。“据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万余落。……攻准于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联系屠各在前赵集中居住又被集体杀害的例子,笔者怀疑平阳居民中的“杂户”是与五部屠各相对而言的。汉国的“杂户”与巴、羌、羯不同,显然不属于六夷的范围。而在汉国的司隶部民之中,五部屠各与其他居民的身份也有差异。石勒“号胡为国人”,“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已如周知。前赵亡国之际,屠各被石勒大批坑杀,相信后赵国人之“胡”,是不包括屠各在内的。本文推测汉赵国六夷之胡不包括屠各在内,这也可以作为一项旁证。
前引《刘元海载记》刘锐、呼延攸所言“三王”,指大司徒、齐王裕,尚书令、鲁王隆,抚军大将军、领司隶校尉、北海王义。“三王”所总“强兵”是否为五部屠各?尚不清楚。陈寅恪先生说:“汉国的匈奴,本部人并不多,但为主力,力量很强。胡人统治中国,全凭武力。单于台所在即本族主部所在。主部所在,即武力所在。”汉国的“本部人”或匈奴“本族主部所在”即五部屠各,为其“武力所在”,例证甚多,无须怀疑。陈寅恪先生又说:“六夷部落因为要用于作战,往往被集中于京邑单于台下,特别是要充当禁军的本部人,更非集中于京邑不可。”这项意见同样值得重视。《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载:永兴二年,司马腾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讨刘渊,次于离石汾城。刘渊“遣其武牙将军刘钦等六军距瑜等”。《晋书》卷102《刘聪载记》载:刘聪署其卫尉呼延晏为使侍节、前锋大都督、前军大将军,“配禁兵二万七千”,自宜阳人洛川,命王弥、刘曜及石勒“进师会之”。按《宋书》卷40《百官志下》禁军之职皆单列,自领军将军至武骑常侍,凡十五项,前军将军也在其中,与左军、右军、后军将军并称“四军”。范晔说:“晋武帝初,置前军、右军。”《晋书》卷24《职官志》文略同。前军将军西晋时为禁军之无疑。呼延晏由卫尉改授前军大将军,前军大将军就是位从公的前军将军。《晋书·职官志》又载:“大司马、大将军、太尉、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开府位从公者为武官公。”“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秩第一。”呼延晏所任前军大将军,当在开府位从公之武官公之列。我们看刘聪所置十六大将
军名号中,前、后、左、右、上、中、下军将军,都是传统的禁军官职,镇、卫京将军不见于旧史,但由其名称推测应该也是禁军官职。由此可见,这些由刘聪诸子担任的杂号大将军,以及他们名下常设的三万二千兵力,同样是禁军的重要部分。前引高敏先生说,刘聪为诸大将军所配营兵,为“匈奴贵族、皇族所统领的匈奴本部兵”,具有禁军的性质,也是类似的观点。但要证明汉国禁军由其“本部人”、“本部兵”充当,却是相当困难的。谷川道雄先生说:“两赵军队的构成如何,还不清楚。”可见,他就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态度。
汉国行政系统中司隶校尉、内史等职的选定,为解释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后汉书·百官志四》“司隶校尉”条本注:“掌察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司隶校尉就其传统职掌而言应属文官,但《晋书·刘聪载记》又载:“愍帝即位于长安,聪遣刘曜及司隶乔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长安,命赵染率众赴之。”《通鉴》卷88系此事于愍帝建兴元年(刘聪嘉平三年,313)四月。考诸史所见刘渊、刘聪两朝领兵官,除刘氏诸王外几乎都是各色将军,乔智明与车骑大将军刘曜、虎牙将军李景年一道发兵,表明其所任司隶校尉又是军职。至于乔氏所发之兵,可能就是其此前管辖的司隶部民。
刘渊称帝,“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刘聪即位后,沿用此项制度。谷川道雄先生说:汉国“手控军队的诸王虽带中国式将军号,却让人联想到塞外匈奴国家的军事体制。在此之前,单于子弟带左右贤王以下诸匈奴式王号,并且以单于为中心统领着各自的部落联盟。单于与子弟间的血缘纽带既是部落联盟式匈奴国家的支柱,同时也构成了后来两赵国家的军事体制。如果将这一结构的重现求之于两赵国家的话,与其说它见之于受到限定的大单于的行政体制之中,不如说它见之于以皇帝为中心,由皇太子、诸王所实行的对国家军队的管理之中。”又说:“在两赵政权中。体现塞外匈奴国家骨骼的不是大单于制,而是以中国式官制为基础的帝国军事组织,这就是新建的匈奴国家所具有的特异性。”此说对于我们认识汉赵国的军事组织,尤其是宗室诸王在该组织中的作用,不无裨益。
《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十年(289)十一月,“改诸王国相为内史。”同书卷24《职官志》“王”条:“改太守曰内史”;同《志》“郡”条:“诸王国以内史掌太守之任。”刘聪在分封宗王的同时,又选择内史即传统的王国相作为汉国主要的行政官员,我想是有其特殊考虑的,此举或许就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分封制度。
唐长孺先生说:“左右司隶自然是沿袭汉魏司隶校尉治地称为司州之旧称,可是这里却不说统郡多少,而是统户多少,户又没有郡县统属而以一万户为一单位,设立了四十三个内史。我们知道内史也是秦汉官号,即以后之京兆尹或河南尹,这里以万户设一内史以致有四十三员之多,显然没有当作首都长官,其所以号为内史之故,只是表示四十余万户都在刘聪直接控制的土地上,亦即平阳及其周围地区。按《晋书·地理志上》司州平阳郡户四万二千,整个司州包括洛阳在内也只有四十七万五千七百,现在左右司隶的范围一定小于晋之司州,又经过大乱,而仍有四十余万户之多,显然是从各地迁徙来的。”又说:“司隶所属户口是刘聪直接控制的人民,其按户计算的制度与下面单于左右辅所主六夷以‘落计算相同,可以证明其为部落制度。”司隶系统下按户计算的人口可能也是部落民,这样一种认识,对于本文的讨论极具启发性。
《晋书·刘聪载记》载:“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通鉴》卷89系此事于晋愍帝建兴二年(刘聪嘉平四年,314)正月。唐长孺先生解释说:“从俘虏得来的六夷与汉族人民,刘聪以胡汉分治的方式管理,在其中抽取丁壮当兵,分立各营,以之分配给他的儿子。虽然记载上不明确,我想一定也分配人口。”陈仲安、王素先生说:刘聪时杂号大将军“都以诸子为之,显然用以统率本族的军队”。高敏先生又说:“这是匈奴贵族、皇族所统领的匈奴本部兵。”@唐长孺先生将“六夷”与“汉族”并举,表明他所采用的“六夷”概念,包括匈奴即五部屠各在内。据此又可知,唐说与陈、王、高诸说,其实是相通的。
前引刘锐、呼延攸谓“三王总强兵于内”,“内”指平阳城内。刘渊时宗王之兵在平阳城内,刘聪时诸大将军营兵估计也在平阳城内。刘曜使卜泰“还平阳宣慰诸屠各”,表明五部屠各同样是在平阳城内,尽管我们对他们与诸大将军营兵的关系,还不了解。
汉国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单于左右辅各领“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已见前述。司隶、单于两套系统,分别以“万户”、“万落”为单位,是仿效匈奴旧时“万骑”的规模。“万骑”最初又是诸王别号,唐长孺先生关于“分配人口”的猜测如能成立,则刘聪或许就是以“万户”为单位向诸王分配人口;而内史统领“万户”,可能实际上就是为宗王管理其分配的民户。
另如《晋书》诸刘载记所载,汉国主要的中外军职多由宗室诸王担当。何兹全先生说汉赵国兵权“在刘氏子弟手中”,言而有据。内史战时是否转为诸王的偏裨,不得而知,但“万户”为诸王提供了基本的兵力,则是可以肯定的。
内史领“万户”,一户出一兵也有万人的规模。刘聪诸子所任各色杂号大将军仅各配兵二千,在数量上与“万户”之兵存在显著差距。究其原因,在于“万户”之兵平时处于预备役状态,战前由诸王或其他领兵官临时征调。刘聪为诸王所配营兵,则是带有护卫性质的常备武装,因此,其数量大大少于“万户”所能提供的总兵力。换言之,“万户”可能是诸王在名义上获得的人口,“万户”储备的丁壮是汉国的重要兵源,刘聪分配给诸王的营兵则是诸王的护卫。三者身份的异同,是我们观察汉赵国社会、政治结构的一个特殊切入点。
《晋书·刘聪载记》载,建元元年(晋愍帝建兴三年,315),“雨血于其东宫延明殿,彻瓦在地者深五寸。刘义恶之,以访其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遐。志等曰:‘主上……置太宰、大将军及诸王之营以为羽翼,此事势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测之危厄在于旦夕,宜早为之所。四卫精兵不减五千,余营诸王皆年齿尚幼,可夺而取之。相国轻佻,正可烦一刺客耳。大将军无曰不出,其营可袭而得也。殿下但当有意,二万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云龙门,宿卫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马不虑为异也。义弗从,乃止。”此事发生在刘聪以诸子为各色大将军的次年,“诸王之营”指各色大将军营兵无疑。刘聪“置太宰、大将军……之营以为羽翼”,可知太宰、河间王易与大将军、渤海王敷也有营兵。
然而,“余营诸王皆年齿尚幼”,表明当时担任杂号大将军的多数宗王,既无能力控制其营兵,也无能力管理分配到的人口。《刘聪载记》又载:刘聪麟嘉三年(晋元帝大兴元年,318)三月,“所居螽斯则百堂灾,焚其子会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刘聪子会稽王衷等二十一人,与嘉平四年任杂号大将军者是否重叠,已无从考辨。不过,此前刘聪署河内王粲使侍节、抚军
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河间王易车骑将军,彭城王翼卫将军,并典兵宿卫;高平王悝征南将军,镇离石;济南王骥征西将军,筑西平城以居之;魏王操为征东将军,镇蒲子,粲、易、翼、悝、骥、操六王均已成年无疑。相比之下,“刘聪子会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尚与其父共居,而且并未担任各种中外军职;螽斯则百堂遭遇火灾,他们又不及逃脱而全部罹难,可信也是“年齿尚幼”,同样无力掌管营兵及其他人口。笔者怀疑汉国内史一职的选置,与封王的安排有关,多数宗王需要他人代理民事或军事职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晋书·刘曜载记》载:“曜遣刘岳攻石生于洛阳,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卫精卒一万,济自盟津。……季龙执刘岳及其将王腾等八十余人,并氐羌三千余人,送于襄国,坑士卒一万六千。曜至自渑池,素服郊哭,七曰乃入城。”石氏坑杀的“士卒一万六千”,应该包含刘曜为刘岳所配“近郡甲士五千”与“宿卫精卒一万”,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士卒都是五部屠各,但石勒相继坑杀刘曜麾下“士卒一万六千”与“屠各五千”,两件事很可能是有联系的。
《晋书·刘曜载记》又载:“刘岳与凉州刺史张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茂临河诸戍皆望风奔退。扬声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凉州大怖,人无固志。诸将咸欲速济,曜曰:‘吾军旅虽盛,不逾魏武之东也。畏威而来者,三有二焉。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刘曜所谓“三有二焉”只是大略的估量,与这批“畏威而来者”相区别的自愿追随者,主要指从汉国故都平阳一带西迁的刘氏旧部,其中可信就有“刘曜带入关中的并州屠各”。
更重要的是,汉赵国宗王所任诸大将军,属于大单于以外的军事系统,我们很难想象,汉赵国本部的五部屠各尽归大单于管辖,而与数量众多的宗室诸王、杂号大将军无关。周一良师推测,刘渊去世前夕大单于刘聪麾下有匈奴与六夷两种兵力,是不无道理的。刘聪当时的身份是大司马与大单于相兼,这样也便于统领匈奴即五部屠各之兵。
总之,汉赵国诸王与司隶校尉、内史两套系统配合,构成与单于、左右辅、都尉并立的另一种“军事化的制度”或“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包括五部屠各在内的司隶部民,平时隶属于司隶校尉、内史的系统,其中的丁壮,战时转换为军人的身份。这种高效的民政与军事管理机制,造就了强大的少数族武力,并为汉赵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谷川道雄先生说:北魏的“部族制度并非有着如塞外部落联盟国家那样纯粹的形态,而是以国家军队的形式出现在统一了中原的国家形态之下。”又说:这种“宗室的军事封建制”,体现了“对日常战斗共同体的部落联盟国家的继承”。此说用以分析汉赵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也是恰如其分的。
三、结语
汉赵国六夷之胡,是诸史称作“匈奴别部”或“匈奴别种”的杂胡,而不是匈奴本部的五部屠各。汉赵国并设司隶、内史与大单于、单于辅、都尉两套体制,就是要将五部屠各与杂胡乃至六夷加以区分,纳入不同的行政、军事管理系统。汉赵国在将六夷与汉人分治即“胡汉分治”的同时,又将包括杂胡在内的六夷与匈奴(屠各)分治,或可称之为“胡胡分治”。汉赵国选择内史作为主要的行政官员,大概是为配合当时的封王制度。内史所领“万户”,可能是诸王在名义上获得的人口;“万户”储备的丁壮,构成汉国重要的兵源;刘聪分配给诸王的营兵,则是诸王的护卫。司隶所辖五部屠各与单于台所辖六夷,都是按照部落制传统组织起来的少数族群体。在汉赵国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他们都具有兵民合一的身份。
这些意见如能成立,也许可以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观察汉赵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入塞匈奴国家的兴衰变化:匈奴本部的五部屠各与非本部的六夷,在汉赵国内摆脱了以往的奴隶或依附民(如田客)地位,获得了自由民(后赵确定为“国人”)的身份,这是他们支持刘渊、刘聪、刘曜政权的终极动力。匈奴与六夷的分治即“胡胡分治”政策的推行,则进一步保证了五部屠各作为汉赵国核心部族的凝聚力。于是我们看到,以五部屠各为主干的中外诸军,在汉赵国与西晋及其他胡汉政权的对抗中,持续提供了强大的武力。而当五部屠各的部族势力在长期征战以及各种内乱、迁徙中消耗殆尽之后,前赵政权也就难以为继,不得不将中原的统治权让给杂胡首领石勒及其后赵政权了。
[责任编辑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