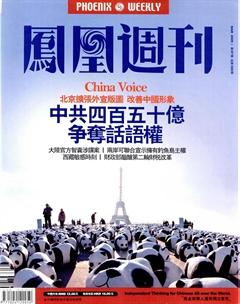七十年代的“局”
梁文道
《七十年代》
北岛、李陀主编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一般以为,现代知识界是现代传播方式的产物。比方说你在报纸杂志上写评论也不知写给谁看。但不知怎的,有人响应了,指出你的毛病缺漏,然后又出一人,替你说话,把指责逐条批驳回去。事情渐渐热闹起来,说话的人多,看的人更多那批说话的再加上那批听话的,就可以叫做知识界了。在这个“界”里头,大家关心同一件事或者话题,人人有想法,人人有立场。但是要是没有杂志,没有书报,没有电台电视互联网,这些人如何晓得谁写过什么?谁画了什么?谁的新书怎么样?谁的思想精深广阔呢?又比如一个诗人大家公认是好,那个‘公认指的是什么意思?口耳相传吗?
北岛和李陀主编《七十年代》,请来30人一起回忆自己的70年代怎么过。为什么是70年代,那个夹在60与80年代之间特别模糊的夹缝般的10年?李陀说,那是因为“七十年代和一个特殊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所遇到的成长环境实在太特殊了,他们的成长经验也实在太特殊了”。我想其他读者一定能比我看出更多更有意义的“特殊”,反正我最关心的,就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那就是这代人联系结友的方式。而单就这一点看来,这代人确实是很特殊的。
北岛在1970年春天和几个“老泡”(借病泡在北京的知青)游船颐和园,其中一人挺立船首诵诗,是首现代诗:“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后来的大诗人当时立刻感到某根神经被触动了,马上探问作者是谁,答案则是郭路生。没有诗刊的年代,原来是这样的。
出版物不多市面流通的更少所以当年流行黑市换书。韩少功说:“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没想到那竟然还是个以物易物的年代。尽管如此,价值判断也还算准确,子弹壳的确没法和舒伯特练习曲相比。
我还注意到闲聊的重要。这代人都爱聊,那不是无谓的Idle Talk,而是真能长见识的讨论。正如韩少功所言:“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
这是人类史上罕有的现象。明明已经进入了电子化的大众传媒时期,可有一个国家的一大批人集体回到口述文明的状态。这个时期不像宋朝那么久远,所以很能为我们提供材料与活生生的见证,了解口耳相传的网络怎样建构出一种知识界的雏形。
我想起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对查建英说的话:“……知青的交往是非常摆谱的,很挑人的,就是知青之间,一开始就想:我看不看得上你啊?你到底行不行啊?”初见面,如何得知对方的分量呢?原来,“……有一个口耳相传的圈子的,会越传越多的,你在这里,别处人家会知道你,很微妙。流传实际上是很广的,可以传得很远的”。所以人物还真的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不一定是写了什么很厉害的文章,而是说过些令人叫绝的话,人家记住了一传十十传百,有时就会变成全国知青皆曾听闻的角色。
然而,我始终不懂,那些闲聊的局是怎么开起来的呢?地下沙龙又要如何组织?当年住在北京的李零也是搔破了头也想不通这个谜:“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没有电话,“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前阵子和陈丹青夫妇吃饭,我也提起了这个问题,陈夫人说他们用走路骑车的办法亲自挨户约局。李零则对此半信半疑:“总之,大家都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能把消息传到……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