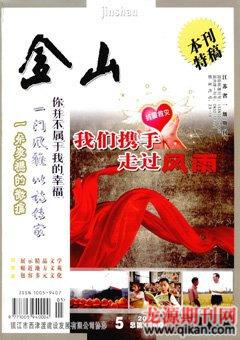文字情人
张明军
很久没有写作的冲动了。并非生计艰难,亦非心情无绪,只是生活需要淀积。一如清水注矾,净后去品,方识滋味。于是,在窗外的白蝴蝶翩然起舞,添香红袖酣然而眠的深夜,方提起笔来,去约会我的文字情人。
中国的文人是浪漫的,风流才子们大多是精神的富翁,但他们大都又生活得坎坷。在留下的流光溢彩的文字中,浸渍着太多的可悲与可叹。司马迁是屈辱的,《史记》虽然被颂之为“无韵之离騷,史家之绝唱”,然其获刑后的创作却充满着悲伤与忧愤;屈原是刚毅的,当《九歌》的乐章化着无奈的碎片飘入汩罗江时,滔滔江水已悲痛得苦涩不堪;苏东坡是豪迈的,可他冲天的才气掩不住天真的“短板”,一贬再贬,用余秋雨的话说“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杜工部是老实的,他不像柳屯田那样张狂,破罐子破摔,摔得但凡有井水处便有柳词。他谨小慎微,却依然不能避免潦倒一生的厄运。还有,醉酒的刘伶,哭穷的孟浩然,乃至被砍头还故作潇洒的金圣叹,他们的生活中有着太多的失意与辛酸。文人们浪漫而优雅,但他们只是经受而不懂得经营。无论是仕途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文化的巨人执著成生活的弃婴,真不知是本领的弱智还是社会的脑残。面对无辜、无奈和无助,文人们又露出了天真的本性。于是,聪明的陶渊明一心一意去经营他的桃花源,醉卧菊丛以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有着“一官归去来,三绝诗书画”之称的郑板桥干脆装起了糊涂,到处宣扬“吃亏是福”。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无论怎样抉择,只要他们不改变自己的精神特质,春风得意永远不会与他们沾边。
“国家不幸诗家幸”,文人们又是认真的,尽管仕途的不顺,抑或生活的窘迫,却动摇不了他们对文字情人的忠贞。于是他们倾其所有,以才气为针,用精神作线,织就了一件件华丽的羽裳,把自己的情人们打扮得明艳多娇,芳气四溢。中国文化的百花园里,莺歌燕舞,春色无边。他们无憾了,春秋笔法植下的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荫泽着历史与现代。无论是在地狱还是在天堂,若有灵知,他们不知该作何想,是自悲?自卑?还是自豪?自嚎?文章千古事,自有后来人。流沙河先生自称“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老夫子是清高的,清高得让人肃然起敬。也许时下所谓的纯文学已没有了市场,但文字的魅力会失去时尚?不!只要我们那份执著不褪色,追求不停滞,文字情人便永远年轻、美丽而摩登。
“伤心花信从来急,愤世文章自古沉。”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延续自然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平台。几家欢乐几家愁,委实有着不同的标准。自古而今,或许有着完美的意境,但决不会有完美的环境。活着真好与活着真难,完全取决于不同的心态。不需要把慎独看成一种境界,其骨子里透着自卑;更无需把随遇而安当着一种追求,它和随波逐流没有太大的区别。诗人云:“委屈的时候,请说出来。愁,固然是一种思考;哭,也不失为一种痛快。”因此,大胆而坚决地去约会自己的文字情人吧,困惑她能了解,惆怅她能理解,痛苦她能排解。她温柔而贤淑,优雅而宽容。不是吗?你看,无论是刘禹锡的桃花情人、周敦颐的荷花情人,还是陶元亮的菊花情人、林和靖的梅花情人,她们无不忠诚而靓丽,解语而浓烈。
今夜有雪,今夜无眠。不想挥别,也无法送别。灯下相拥,缠绵温馨。眼观如羞羞答答的含羞草,手捧似清清泠泠的解语花。噢,我的文字情人,你已青春永驻在我多情的笔下,你已根植于我温暖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