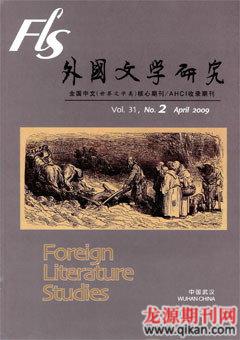解构批评的洞见与盲区
内容提要:解构主义是当代中国理论批评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讨论它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其中大多数成果都着眼于它的理论思想观念,很少涉及它的文学批评方法。本文借分析解构批评的一项代表性的成果《小说和重复》具体考察了解构批评方法的成败得失,指出解构批评在充分揭示文学作品的无限丰富复杂性和异质性的同时却完全忽略了它的统一有序性和同质性,既新颖深刻又极端褊狭。从文学话语的角度看问题,一部文学作品既有复杂多元的一面,亦有明晰一致的一面,两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关键词:希利斯·米勒《小说和重复》解构批评异质性《吉姆爷》
作者简介:肖锦龙,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西方文论和莎士比亚。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意识批评、话语分析、行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解构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坛上的一个热门话题。当前,尝试用解构主义方法阅读中外文学作品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解构主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局限?如何克服?过去人们探讨这类问题多是从分析阐发解构主义的某种理论论著出发的。本人在此想换一个角度,拟借考察解构主义的一部批评论作即希利斯·米勒的《小说和重复》对之加以论述。
一
《小说和重复》是希利斯·米勒的代表作之一,也是西方解构批评的扛鼎之作。此著共8章,第1章主要阐述了解构文学观念和批评理路。接下来的7章用解构理论方法解读了维多利亚时期的7部小说作品。《小说和重复》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作品的异质性问题。米勒在该著第一章中开宗明义指出:“文学的特殊性和奇异性,每一部作品中那能使读者产生惊奇感的潜能(如果读者预备好准备接受此种令人惊奇的东西的话),意味着文学可持续不断地突破任何批评家用以界定它的程式或理论”(Miller 5)。“这本书中各种文学阅读的首要动机亦是我研究文学的初衷:设计一种方式以体察文学语言的怪异性,并尝试着解释它”(Miller 20)。这即是说出人意料、令人耳目一新的怪异性或者异质性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该著将着力解释它。
米勒对文学异质性问题的论述是从一个关键词“重复”开始的。所谓“重复”,是指“一种东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另一种状况下重新呈现出来”(Miller 1)。重复从形态看有横向的和纵向的两类。横向的重复,指的是文本内的因素的一再显现,如“词语因素的重复”、“事件或场景的复现”、人物的重复、题旨的重复等。此类重复将作品内部各种不同的因素如词语、符号、事件、场景、人物、题旨等编织到一起,组构成一种“线形序列”,使之成为一个整体(Miller 1-2)。纵向的重复,指的是文本“外部的东西”在文本中的复现。这些“外部的东西”包括“作者的大脑意识或生活”(Miller,1)。此类重复将文本外部的所指内容和文本内部的词语形象连接起来,使之合为一体。“任何小说都是重复和重复中的重复的编织物”(Miller 16)。纵向的重复将外在现实和作家的大脑意识转换成书本上的各类词语形象,横向的重复将这些词语形象连接为一体。小说等文学作品是由上述两类不同形态的重复的交互运动组构成的。
重复从性质看,主要有“柏拉图式的”和“尼采式的”两种。“柏拉图式的重复”和“尼采式的重复”两个概念最早是德鲁兹在《感知的逻辑》中提出来的。前者指的是同质性的重复,“此重复基于某种固定的为重复的效果触及不到的原型式的模子之上,所有的其他的事例都是此模子的副本”,它是异中见同式的重复。后者指的是差异性的重复,此重复基于事物问的差异运动之上,在它那里“每一种事物都是独特的,它本质上不同于其它任何一种事物”,它是同中见异式的重复(Miller 3)。事物无法直接呈现出来,只能借人的大脑反映出来,只能呈现在人的记忆中。对事物的重复实际上是对人的大脑记忆的复现。德鲁兹所说的“柏拉图式的重复”和“尼采式的重复”实质上就是本杰明在《普鲁斯特的意象》中所说的“白日理性的、意志的、有意识的记忆”和夜晚梦境中“无意识的本能记忆”(Miller 7)。它们之差别是理性和非理性、逻辑和修辞、白日和夜晚、意识和无意识、回忆和遗忘、建构和拆构之差别。
文学作品从构成因素看是由内在的和外在的各种不同的成分编织成的,从构成方式看是由同一和差异、理性和非理性、有序和无序等两种相反的运作方式组构成的,由此而言其内在机制自然非矛盾异质莫属。所以异质性是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
文学作品的内在机制问题是人类文学领域里的核心问题,也是历代思想家文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过去由于人们为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所囿限,一贯认为文学作品基于某个中心点之上,是一元的、有机统一的,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多元性、矛盾复杂性和异质性差不多视而不见。基于德里达的反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思想之上,米勒在《小说和重复》中一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学有机统一论理论,从对关键词“重复”的分析人手深刻阐发了一切文学作品都基于丰富多元和矛盾自反的因素之上,都是异质的文学观念,充分揭示了文学作品机制中曾被遮蔽了几千年的一种重要属性即矛盾异质属性,展现了文学作品的无限丰富复杂性,这不能不说是空前新颖的,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
米勒的文学异质性理论完全基于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的语言符号观念之上。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人类世界是由语言主体“书写”成的;一个语言主体在使用某种语言符号前不能不先进人到该语言符号系统,不能不先将它的词法、句法、程式、规则内化在自己的精神机制中,语言主体是由语言符号结构铸造成的;语言符号内在既包含所指观念成分又包含能指形式成分,是矛盾多元的、多义的,如词语“你真好!”就有夸赞和贬斥两种意味;所以基于语言符号之上的语言主体以及由之所“书写”成的整个人类世界自然是矛盾多元的。语言符号是这样,作为人类语言符号之一种形式的文学自然不能例外。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此习用语指的就是文学符号之意义无限多样、不可穷尽的状态。从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结构建构世界的观念出发看问题,米勒的文学异质性理论自然无懈可击。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看,语言符号是由语言主体制作的,是为语言主体服务的,离开语言主体,语言符号不可能存在,也无存在价值。一种具体的处于流通状态的鲜活的语言符号无不承载着语言主体的思想信息,无不为语言符号主体所操控,无不深深打上语言主体的烙印。人们通常将现实中的这种活生生的“处于实际应用中的语言而不是作为抽象体系的语言”称作是“话语”。如果我们不是从语言符号结构的角度看问题,将语言符号看成是一种独立自主的系统,而是从语言符号应用的角度看问题,将之看作是由语言主体所操控的、用来传达和交流其思想意识的言说方式(或言话语)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它并不是多义的而是具有单义性,不是矛盾自反的而是内在统一的。因为为了明确表达自我,语言主体在使用词语时无不对语言符号的多元意味进行严格筛选过
滤,无不极力从中撷取某一种适于表达自己思想意识的意味。这样,处于流通状态的活生生的话语无不是单义的、明晰的。以词语“你真好!”为例,在前应用的层面上它的确包含着夸赞和贬斥两重矛盾的意味,但当它被某个主体所应用、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中被说出来时,便只能有一种意味,即夸赞某人,或贬斥某人——否则它便是无意义的,便是无稽之谈。一般语言符号是这样,文学符号自然也不例外。在具体的作家手中文学符号无不被后者所统摄,无不被赋予这样那样的序列,无不是统一的有序的。从人说语言的角度看,解构批评家米勒只注意到了语言符号的结构性和客观自律的一面,而未意识到它的实用性和主观自为的一面,因而只看到了基于语言符号缔构自律性之上的文学作品的异质性的一面,而完全忽略了基于语言符号现实自为性之上的文学作品的同质性的一面,他的语言文学观的偏误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二
既然文学作品是矛盾自反的、异质的,那么对它的解读自然当以揭示和解释它的异质性为重心。正因此,米勒在《小说和重复》中一开篇就宣称:“本著的七种阅读拟辨析各种状态中的不规则性,并试着去解释这种不规则性”(Miller 5)。他在此著中集中分析阐述了维多利亚时期一系列重要的小说作品的矛盾异质性。下面我们就以他在第二章“《吉姆爷》:作为对有机形式之颠覆的重复”中对《吉姆爷》的异质性的分析阐述为例来看看他的解构批评的风貌。
在此章中米勒首先指出,文学作品并不像柯勒律治等西方形而上学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基于某个中心之上,是有机统一的,相反它“没有始发点,没有外在基础,而仅仅以自发的网络形式存在”(Miller 25)。“我们很难说由纺织机所纺织的布匹是有源头的,因为那机器所编织的东西就是它自己,编织器和被编织物共同制作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既无始端,亦无终端,一直处于自我生成中”(Miller 25-26)。康拉德的小说就像无头无尾的编织物,压根是多元的、异质的。《吉姆爷》就是典型的例子。
《吉姆爷》主要描述的是吉姆的生活经历。主人公吉姆的形象是作品的核心因素之一。吉姆出生于英国乡下的一个牧师家庭,是在英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崇尚荣誉,渴望有一番作为,令人刮目相看。在“帕特纳号”上当大副时,有一次他所在的船漏水下沉,船长和几个船员不顾乘客性命,狼狈逃命,他见了非常鄙视,不屑与他们同伍。在帕图森岛上,他不顾个人安危,与当地的恶势力和海盗进行殊死斗争,无私地保护当地的土著人,为他们谋取自由和幸福。他高尚、“谦逊、冷静忠诚、朴实勇敢”(Miller 27),是一个优秀的英国青年。不过这只是他性格的一方面。与之完全相反的是,“他的大脑中深深积结着阴暗的东西”(Miller 27),在“帕特纳号”下沉时,他虽然看不惯同伴们贪生怕死、狼狈逃命的行为,但在关键时刻也抛弃了需要保护的乘客,卑鄙地跳上了救生艇逃走。帕图森岛上他与恶棍布朗斗争,愚蠢地相信了后者的承诺,从而导致瓦里斯被杀害。他的性格中有胆怯、理想化、自负等缺陷,其形象明显是内在矛盾的,是二重的。
马罗对吉姆形象的解释也矛盾自反。一方面他认为吉姆抛弃“帕特纳号”上的乘客、仓皇逃跑的行为是由求生的本能导致的,情有可原:“也许他可以被原谅”(Miller 29)。另一方面,“马罗暗示,尽管如此,吉姆的性格有很多致命的弱点”(Miller 29),如在关键时刻靠不住、对自己存有一种“幼稚的幻象”、以“英雄”自居,等等。
就叙事形式而言,作品中有很多叙事视角。如前四章主要是由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叙述的,第五章之后主要是由第一人称叙述者马罗叙述的,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类的人物的叙述等。这些叙述者对事件的看法大为相异,以至相互矛盾。所以“在《吉姆爷》中没有什么观点是完全可靠的。此小说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大脑意识的复杂的合成体”(Miller 31),其中没有统一的观点和明确的思想。
作品的结构也复杂多样。一方面作品写的是吉姆的一段奇特的生活经历,展现了吉姆从最早在海上漂泊,到最后在帕图森岛牺牲的经历,总体上是以时间顺序安排材料的,是线形的。另一方面,“当那一连串生活事件之线形序列由各类叙述者呈现给读者时,它却完全被重新安排”(Miller 35)。作者着意“颠倒时序”,借重复、强调、省略等方法重新组织吉姆所经历的生活事件,使它们与生活中的序列大相径庭,从而给作品打上了显著的空间立体特色。
从艺术境界看,作品一方面取材于生活事件,是以发生在1880年8月8日的一则欧洲白人船长和船员在知道他们的轮船出了故障时便抛弃船上的乘客而仓皇逃命的丑闻为素材创作出来的,“小说背后的依托是历史事件”(Miller 36),它的境界是真实的可信的。另一方面,它是“康拉德通过虚构借迂回之途理解现实的一种尝试”,是康拉德对历史的“解释”,是一种“文献”(Miller 36),已与实际的历史事件拉开了相当的距离,是一种历史文本,它的境界是虚拟的、不可信的。
此外作品大量应用了隐喻手法,意象很醒目,其意象也是内在矛盾的、二重的,“明亮和阴暗意象的网络明显地组构了整部小说”(Miller 37)。如白与黑、明与暗、白天与夜晚、闪电和乌云、可见与不可见之类的矛盾意象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它们相辅相成,永远盘缠在一起,相互促发,也相互消解。
《吉姆爷》从横向看是由无数种各不相同的因素组构成的,从纵向看每一种因素都矛盾自反、自我解构,所以它在根本上是多元矛盾的、模糊多义的,是无法穿透的。《吉姆爷》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被编织在一个词语的网络中,它无法被明确解释,无法被作为某种固定的意义模式理解”(Miller 31)。
康拉德的《吉姆爷》作为西方小说史上的一部由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跨时代的杰作曾受到了人们密切的关注,解读和评论它的研究成果可说是层出不穷。不过总体而言,由于受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圈限,通常人们在解读中一开始就认定它基于某种中心点或核心因素之上,因而将注意力完全放在探讨它的中心点或核心因素上,并用后者来界定整部作品,将之建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结果完全忽略了它的其他成分或因素,忽略了它的多元性和内在矛盾性。如诺曼·谢里认为《吉姆爷》是在改编1880年8月8日欧洲白人弃船逃跑之事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所以认定该事件是作品的本源,他详细考察了那事件,并用之解释作品,以那事件为核心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统一的《吉姆爷》文学世界。伊安·瓦特认定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产生的,因而深入探讨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借之解释作品因素,将它们统一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思想状态上。但尼尔·R·施瓦兹认定它基于作者的精神心理之上,因而集中探讨了作者的精神心理,用之解释作品因素,将它们紧紧链接到作者的精神心理上。很明显,他们各自只注意到了《吉姆爷》文本中的某一种因素,而遮蔽了其它因素,只注意到了它的统一性、一体性,而忽略了它的矛盾性、开裂性。
米勒的上述解读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它一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一元化、求同式思想方式,采用全新的多元化、辨异式思想方式解读作品,深刻发掘了《吉姆爷》的多元因素及其矛盾自反性,打开了其中的许多新层面新品格,揭示了它的无限丰富复杂性,给人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作品图景。
不过应当看到,由于米勒一贯认为《吉姆爷》是由文学语言这台编织机自动编织成的、此编织机中的引线是多重的、弯曲的、由它所编织出的作品是多元的、芜杂的,所以他把批评重心完全放在了分析作品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上。他对该作品的另一面即它的主观创造性以及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作品独特的结构和它的统一性差不多视若无睹。这样他所呈现给我们的《吉姆爷》世界,除了是一座看不透、说不清的极为复杂多样的迷宫外别无他物,我们从他那里除了了解到它的无限丰富复杂性这一状态外差不多一无所获。作为一个文学接受者我们当然有必要知道文学作品是多元异质的这一原理、有必要了解文学世界的丰富复杂性这一重要属性,但同时更有必要了解它是怎么制作成的、有什么独到之处、艺术思想何在等信息,可惜米勒的这种旨在探求文学作品异质性的理论方法对解决上述问题差不多毫无帮助,而上述问题无疑是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根本性的问题。由此可见,米勒所创立的旨在探究和开掘文学作品的异质性的解构批评方法是一种艺术和思想功效极有限的批评。
三
就《吉姆爷》作品本身而言,它的多元复杂性的确不可否认。对此西方很多批评家都做过明确阐述。塞莱指出:“论及《吉姆爷》,我们不能不同时关注双面的康拉德”(seeley496)。斯塔普断言:“文体的多元声音、时序的错乱、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是这部作为戏剧、自传、历史记事的杂糅体的小说的突出特征”(66)。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吉姆爷》的多元矛盾性并不像米勒所认为的那样基于脱离文学主体的客观自律的文学语言之上,而是基于由文学主体掌制的鲜活自为的文学话语之上,因而不是失控的、无序的、不可读的,而是受控的、有序的、可读的。
正像西方学者斯塔普所说,康拉德的《吉姆爷》沿承了西方18、19世纪“教育小说”传统(63-64),主要写的是吉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不同之处仅在于:1,它不是用一种叙事声音而是用多种叙事声音叙写的。西方的“教育小说”,无论是18世纪的《汤姆·琼斯》,还是19世纪的《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情感教育》等,一般都只有一个叙述者、一种叙事声音。而康拉德的《吉姆爷》中却有多个叙述者、多种叙事声音。2,不是用同质叙事法而是用异质叙事法叙写的。所谓同质叙事法就是叙述者在描述主人公时紧紧跟随主人公的思想情感逻辑,如《红与黑》中的叙述者乐于连所乐,悲主人公所悲,与之同呼吸共命运。所谓异质叙事法就是叙述者在描述主人公时有意跟主人公的思想情感保持一定的距离,如《吉姆爷》的叙述者,从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到第一人称叙述者马罗以至其他人物,都用冷静疑惑的眼光看待吉姆,不是将吉姆当作欣赏和效仿的对象,而是当作审视和评判的对象。
《吉姆爷》中的叙写话语从功能看主要有两类:一是客观描述吉姆生活经历的话语,它们陈述了主人公的所见、所想、所做,展现了他的思想个性;二是主观评判吉姆所作所为的话语,它们解释和点评了他的思想言行和性格特点。
详细追踪和展示吉姆的生活经历和个性特点是作品的重心所在。“吉姆原本生在一个牧师家”(《吉姆爷》2),他的父亲既慈善又严厉。严格严肃的家庭教育将他培育成了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严肃认真,具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性。后来他阅读浪漫传奇文学,生发了一种漂洋过海、成就一番伟大事业、做一个人们所仰慕的英雄的人生梦想。之后他毅然离开故乡,出海冒险。在“远洋商船指挥员训练舰”上接受培训时遇到了一个出风头的机会,但因恐惧心理作怪错过了那次良机。后来在“帕特纳号”遇风暴注水下沉时,他本来准备挺身而出,彰显英雄本色,可在关键时刻又为一股无名的恐惧心理所驱使不知不觉地跳下大船仓皇逃生。这“一跳”不仅粉碎了他日思夜想的英雄梦,而且将他抛向了他所鄙夷的那一群贪生怕死的懦夫之中,他羞愧难当。此后为了逃避这种不光彩的记忆,他不断地变换环境,更换工作。最后他在斯坦因的帮助下来到帕图森小岛,终于从过去不光彩行迹的阴影下走了出来,走上了通向人生梦想的大道。在那里他领导当地的布吉斯人与强盗阿里警长和恶霸阿朗酋长进行殊死斗争,最终将阿里赶出了国界,使阿朗俯首贴耳,给当地的土著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平,他成了帕图森土著人的救世主,人们称他是“Lord”。正在这时,一个十恶不赦的白人布朗闯进了帕图森,吉姆天真地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结果给当地的布吉斯人带来了重大灾难。顷刻间他在布吉斯人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从过去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伙同白种人出卖朋友和伙伴的小人。为了挽回信誉和声望,他最后献出了生命,以死抵偿了自己的过失,为自己赢回了荣誉,圆了自己的英雄梦。
吉姆就是这样一个一生坚定不移地行进在自己建立功勋、成就英雄大业梦幻的道路上的理想主义的人物。他虽曾经退缩过、失败过,但经过严峻的磨练,终于克服了自身的性格弱点,大无畏地走向了建功立业之途,成就了一番功勋,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英雄。他从不完善走向完善的人生历程正是西方18、19世纪的“教育小说”中大部分主人公所走过的路。他憧憬、投入、受挫、失败、磨练、成功、自我完成的个人奋斗历程可以说是一个青年走向成功、实现个人梦想的必由之路,无疑很值得借鉴和效仿。单就作品对吉姆的生活经历和思想个性的描述和展现而言,《吉姆爷》无疑是一部典型的“教育小说”。
不过,《吉姆爷》的内容远不止于此。除了描述和表现吉姆的思想言行外,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线条,就是借各种各类角色的话语对吉姆的思想言行进行了多角度的解释和评判。《吉姆爷》一大半的篇幅是解释和评判吉姆思想言行的文字。《吉姆爷》中解释和评判吉姆的思想言行的言说者很多,其立场和观点也很复杂。如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者、法国中尉、伊塔姆、斯坦因、马罗等同情吉姆,认为他高尚可敬;彻斯特、柯涅柳斯、布朗等鄙夷和仇视吉姆,认为他愚蠢可笑;布莱尔利蔑视吉姆,认为他天真幼稚;珠宝怨恨吉姆,认为他自私无情。不过,总体而言他们的姿态和格调完全一致:都是从经验、现实的角度来审视吉姆的,都认为他一直沉湎于自己的人生理想中,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如斯坦因、马罗等认为,吉姆“追求梦境,再追求梦境——就这样——永远——直到最后”(152),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乞丐”(57),“随时准备忠心耿耿地为了他那个阴影中的世界主张牺牲自己”(302)。柯涅柳斯、布朗称“他是个大傻瓜”(236),一个自命不凡、“徒有其表”的笨蛋(249)。布莱尔利认为吉姆太理想化了,应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就让他往地底下爬二十英尺,呆在里面好了!”(46)珠宝埋怨他“没有真心实意,没有古道热肠”(252)。如果说吉姆是一个生活在幻想中的理
想主义者的话,那么他周围的人则多多少少都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由于《吉姆爷》自始至终贯穿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相反的基调,所以其格调压根是矛盾自反的,是反讽式的。
多元话语和二重基调是《吉姆爷》叙写话语的基本形式。正是此形式使《吉姆爷》跨越了西方18、19世纪“教育小说”的传统,步入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行列。人们普遍称康拉德是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过渡性的小说家,《吉姆爷》是“现代主义的范本”(seeley 495),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吉姆爷》的这种多元叙写话语和二重思想基调。
康拉德的父母曾是激烈反对沙俄统治的激进的革命理想主义者,而他的舅舅则是诚心拥护沙俄统治的保守的温和派务实主义者。康拉德早年由父母养育,后来父母受沙俄统治者的迫害亡故后,由舅舅抚养,他既受过父母理想主义精神的熏陶,又为舅舅的务实态度所深切浸染,他的精神心理一开始就是二重的。《吉姆爷》的多元矛盾性明显与康拉德精神心理的二重性深刻联系在一起。另外,康拉德一方面十分喜爱司各特、库柏、雨果、狄更斯、司汤达等充满幻想、激情、仁爱思想和革命精神的理想主义作家的作品,另一方面又对极力倡导客观、冷静、科学、切实文风的自然实证性作家福楼拜、左拉等的作品情有独钟,他的思想中同时兼容了19世纪前期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19世纪中后期的自然主义、实证主义两类思想理念。《吉姆爷》的异质性自然也与康拉德思想理念的矛盾性不无关系。
《吉姆爷》中的理想主义者吉姆年轻、毛糙、幼稚,事业处处受挫,现实主义者马罗老成、持重、成熟,事业一帆风顺。作品的思想意向显而易见,即深刻怀疑旧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精神理念,倡导新的现实主义和科学务实的精神理念。由此可以看出,康拉德更为赞同新兴的现实主义、实证务实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态度。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以下现象:在很多作品中康拉德都是让老练稳重的马罗代自己叙事、让他做自己的代言人。《吉姆爷》整体上受制于作者的精神心理和思想理念,很明显是一元的、统一的、一体的、有序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正如米勒所说,《吉姆爷》的确极为丰富复杂,是异质性的,不过它不是基于非主体性的文学语言的自律运动之上,而是基于主体性的文学话语的自为创造之上,是由各种不同的叙述话语编织成的,最终受制于作者的精神思想,因而在根本上是统一的、有序的、可读的。米勒从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观念出发,只注意到了《吉姆爷》中脱离主体的文学语言的层面,而没有注意到由主体操控的文学话语的层面,只看到了《吉姆爷》多元矛盾和模糊无序的一面,而未注意到它的多元性中的一元性、模糊繁杂性中的明确有序性,因而是狭隘的片面的。
总之,米勒的《小说和重复》一方面以德里达等人的矛盾差异论理论学说为基础,深刻揭示了文学作品中过去一直为人们所普遍忽略了的一种根本属性即异质性,为人们全方位开掘文学作品的无限丰富内涵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启开了一条新途径,其思想理念和视野的新颖程度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从后结构主义语言说符号观念出发,只注意到了文学活动的语言自律的一面,而忽略了它的话语自为的一面,只注意到了文学作品的多元矛盾性,而完全忽略了它的一元统一性,因而不仅在理论上是片面的褊狭的,而且在实践中无法为人们深入考察文学作品的制作过程、探究它的艺术和思想价值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帮助,其批评思路和方法有严重的局限性。《小说和重复》是西方解构批评的经典之作,它的成就和不足是西方解构批评之优劣得失的结晶。近年来西方的新生代批评家们在普遍接受解构主义的文学理念和思想视野的同时却纷纷扬弃了它的符号学批评理路和方法,转向了文化话语批评。很明显,解构主义本身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