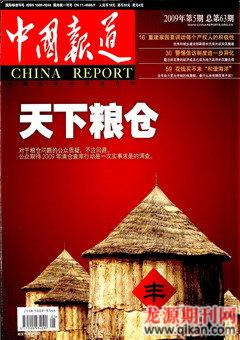危机时刻的文化凝聚力
提起历史上的危机时刻,人们的脑子里总是离不开一些定格的印记。比如,想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总是离不开黑色的记忆:资本主义的无序发展,导致股市动荡,生产凋敝。然后总难免会出现拯救斯民于水火的英雄人物:政治家罗斯福以及理论鼓手凯恩斯。
然而,这终究是大历史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痕迹。那些日常社会片断则被光芒璀璨的大人物模糊为惨淡的背景。文化和日常的层面,以及不同层面的中间地带,被忽略不计了。
其实,当政治家、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们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体系而绞尽脑汁的时候,普通人的日子并没有因为制度的失败而终止,重塑对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的信念也从未停止。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经济的颓败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繁荣,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经济危机,紧衣缩食总是难免。但由于失业或者工作量减少,闲暇时间却大大增加。如何填满这些时间成了困扰大众的重要问题。这样的背景下,更为廉价的大众娱乐和信息传播载体,在经济颓败的时刻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繁荣期。
最典型的例子是好莱坞电影的普及与发展。如今的好莱坞当年只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地方电影联合体。1929年明,当大萧条即将席卷美国及全球时,好莱坞举办了第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好莱坞电影业本身也和其他产业一样,遭遇了经济衰退带来的巨大冲击,好莱坞的债务在上世纪20年代末翻了三倍。为了应付危机,各大电影公司和院线推出各种措施吸引顾客,降低成本。但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每周依然有6000万至8000万美国人去电影院。后来的史家们认为:面对蔓延无期的债务危机和绝望,电影作为一种现代大众文化快餐的先驱形式,对维持国家和人民的士气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资本主义挺过危机而得以新生的伟大成就,除了罗斯福新政的宏大叙事,作为大众抚慰的电影也功不可没。
如何解释这种巨大的反差?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典型的逃避主义。越是危机的时刻,人们越需要—种温暖的安慰剂来调节高度焦虑的神经,逃避无法忍受的现实。电影正好雪中送炭,通过温情脉脉的或者诉诸感官刺激的小故事,不断转移着人们对重大制度和政策问题的注意力,强化着传统的价值观和社会秩序,为不断高涨的激进诉求降温。
这种阐释似乎极大地简化了现实。实际上,绝大部分大萧条时期的电影多多少少都反映了时代背景,并不是简单地奉行阿Q主义。
如今人们熟悉的好莱坞式乐观主义,是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才得以确立的。早期美国电影充满了黑帮、匪徒、好色之徒、政治腐败、商界黑幕等形象和情节,既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一种煽动性和感官性诉求的市场策略。彼时刚处于发展初期的好莱坞,还像一头桀骜不驯的烈马,由着性子奔驰。但由于内容与人们的既有价值观出现冲突,引发了宗教和道德团体的抗议,在社会上出现了针对电影和其他早期大众文化的“道德恐慌”。1933年,罗马教廷甚至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号召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净化”电影业。
为了避免陷入被抵制的危险,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电影业加强了自我管理,大量可能引发过分消极情绪的内容基本上被过滤掉了。一种被理想化的美国人的自我想象开始出现了,活泼、可爱、勇敢、富有激情,但也可能会有点轻率和单纯。一个普通人的英雄梦开始作为经典的主题被反复讲述。人们认为,正是这个被反复讲述的梦想,帮助美国人渡过了难关。
可见,作为“抚慰剂”的电影其实是宗教、政治、道德、市场、大众需求等不同社会力量的中和物,而不是来自某个社会力量的粗暴操纵社会心理的过程。
与电影同期出现悖论式繁荣的还有广播、小型游戏、公共图书馆等其他各类文化载体。其中,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更以广播时代的政治公关经典案例,成为广播黄金时代的标杆。
显然,一个危机中的市场体制需要这种文化载体来帮助人们重建已经破碎的意义世界,从而保持信心和勇气。
这或许可以给今天同样面临危机的我们一个启示:除了关注那些宏大的制度和政策,也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连接制度和人们的信念层面的文化建设。无论这个以市场为基石的制度是好是坏,无论应该如何惩罚那些欺世盗名的投机家,无论完美的制度设计是否真的存在,也无论危机时刻的大人物们如何灵光闪现、智慧无穷,能够保持沟通的能力并且给人民以希望和信心,而不是简单地操纵社会意识的人和制度,将是最终的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