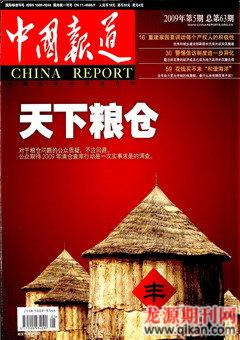王蒙妙谈文人与政治家
于 歌
从存在中获取最大成果和最大乐趣的秘诀,就是过危险的生活。这曾是尼采的心得。
王蒙对此应深有体会。什么是危险的生活?远离传统和惯例,非常规,无秩序,或可算是一种。王蒙,19岁时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成名;22岁时因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随后,边疆16年。
按照王蒙在《老子的帮助》序言中推算,他在14岁时便接触《老子》,皓首穷经,至今60余载。年轻时的王蒙肯定没注意,或者注意到也并没有在意老子的这句话: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为何不敢为天下先?据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守藏室之史”,相当于周王朝政府档案馆馆长。深谙历史的老子早已经看透了盛衰兴亡。如学者鲍鹏山所言,人类集体的经历和创痛成为老子个体的感性体验,生在那么多既经的历史之后,他仿佛一个晦气重重的遗腹子。
那些既经的历史就是老子所体验到的“危险的生活”。 而与西人尼采般主动撞击生活以体验毁灭不同,后人从中获取的最大成果与乐趣,正非《道德经》莫属,而这“五千余言”之精要所在,是治国无为处世养晦,是教我们如何避险。
读王蒙的书,和他聊天,感觉他很少离开“自己”。他读老子亦如是,“证词一说使我满意至极。我曾想说是理解、是心得、是发挥、是体会,都太一般化了。我,不是可以拿出来与老子对证查证掰扯一番吗?”
王蒙的“危险的生活”,无论来自自我选择还是被动接受,都与王蒙的哲学相互产生,相互交织。二十载遥望京畿,忧心如炽,何时升杲杲红日?那么多年里,对于王蒙,生活这个词脆弱而盎然的核心,只是“眺望”两个字。
所以,大道何所言?真正最高的本质概括,即便有经历、有修为,也是难以言说。
梅洛·庞蒂说得对,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锚地。王蒙有幸“天假其手”,能看穿自己七十余年的所见所闻、所泣笑、所思悟,深深介入并畅快直言这“锚地”上的万般悲喜,在那么多突然的感触、内心的颤抖、不知来自何方的启示和抒情爆发中与灵魂终获相通,并久远回味。
他人难以揣测。所以,还是看王蒙的书,听他说话。
中国报道:最近很多人在读您的新作《老子的帮助》。之前您出过三本自传。能否说,《老子的帮助》是您对人生经历一种哲学化的总结?
王蒙:《老子的帮助》和那三本自传,从我自己写作角度来说,并没有刻意追求他们之间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必然会有联系。《老子的帮助》是我70岁以后写的,有70岁以后的特点。如果把《老子的帮助》和《我的人生哲学》对照起来读,更容易看懂。例如书里面谈到的“无为”的问题。
老子的话是很精练的,侧重谈治国。他的理论也非常高深。但可以说,古今中外很少能找到按照他的理论来治国成功的例子。历史上的大多数都是按儒家理论来治国的,起码口头上是这么标榜的。按法家治国的也有,比如秦朝李斯,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喜欢读老子著作的人倒是很多,但他们往往并不以此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读了《老子的帮助》以后,人们的胸襟或许会变得开阔,它至少可以让你减少荣辱得失感。
中国报道:对于儒道释三家,南怀瑾先生曾有个比喻:儒家像粮店,决不能打,否则我们就没有饭吃。佛家是百货店,随时可以去逛逛。道家则是药店,没病的话,一生可以不必去理,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王蒙:这个说法跟我的意思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完全相似。老子的话不能当饭吃,但可以当茶喝,当饮料喝,当清凉饮料喝,发高烧的时候可以降温。还可以当仙丹吃,吃完以后可以超凡脱俗。当饭吃的东西需要实用性更强,这个方面道家不如儒家。例如儒家讲“吾日三省吾身”,这个你马上就可以用。道家的东西让你清醒,让你升起很多幻想,但遇到实际问题,你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中国报道:为什么71岁的时候开始写自传?
王蒙:其实很早就有很多人约我写传记,包括一些外国的出版社。但我想70岁以后开始写。70岁是一个门槛,走过来,可以说就是真正老了。50、60岁的时候,似乎还缺少一些沧桑感与回顾感。过70岁了,人的内心才可以更平静。
中国报道:写这几部自传时,有没有不平静的时候?如果是别人来写您的传记,您觉着会怎样?以后还会继续写吗?
王蒙:当然是有的。比如写到童年的家庭纷争,我父亲当时众叛亲离,心情还是有些沉重。但总体来说,是回忆的心情,不再烦闷、苦恼、愤怒了。对于过去的很多事情,已经超越与化解,没有那么多未了之事和未了之悲,只是从中可以体验到一些经验教训。
整个的写作过程,还是有很多愉快的。我不是在苦苦挣扎和遭遇灭顶之灾的境况下来回忆,而是在一个相对稳定、镇定、还带几分自信的状态下来回忆的。尽管在自传里,好事、坏事、光彩的事、不光彩的事情都有,但都走过来了,没有对我造成根本上的挫折,没有那种苦主、债主的情绪,没有觉得社会欠我、上帝欠我的。
任何传记,都是作者在表达自己对于周围一些人和事情,以及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我的传记,别人肯定是写不了的。别人只能根据他们的经验、揣测和判断下笔。有些人在写我的传记,比如武汉大学的余可迅教授,已经写了好几年,非常认真。
至于以后是否还继续写,要看身体状况。已经完成的自传一直写到了2007年秋天。到2012年,也许我再写写这五年以来的事情。如果身体健康,会再经历一些事情,没准就再写本书。
中国报道:自传中的小标题,是编辑还是您自己加的?文中经常会看到插叙,从一个朋友联想到另外一个朋友,一个事件联想到另外一个事件,您如何来掌控自己讲述的欲望和秩序?
王蒙:小标题都是我自己加的。自传当中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有时候讲到某段经历,又顺便提到有关的另一件事情,这是我的叙述方式。有时,我也羡慕那种埋头书斋、深居简出的生活,只是我的经历不是那种类型,比较复杂。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案头工作。有时候写作时,要理清条理,会感觉非常困难,所以不能完全按编年的硬性节奏来写。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我时常还会采用“预告性”的写法。这和我写惯了小说有关系。自传也不会用史书笔法,还是文学性比较强。
中国报道:您的自传中的某些文章,谈到一些经历时,叙述节奏明显加快,密度也加大,文字对于您来说,是否是一种最重要的释放途径?
王蒙:我已经形成了一种自己工作的方式、感情的方式、生活的方式。不管是高兴的事情还是遗憾的事情,一下子就可以变成许多许多的语言和文字。有时候这并不都是优点,我深深感觉到自己有时候话太多。
2008最快乐的一件事,是CCTV9约我进行英文采访。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虽然主持人问的那些问题已回答过上百次,但从没用英文说过。比如问我,认为自己是不是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一个作家为什么参加这么多政治活动?其实我在自传里也写过,说自己不适合做政治家。我常常举一个例子:任文化部长期间,去听过一回李世骥等演出的京剧《哭塔》,讲白娘子的儿子长大成人后,到雷峰塔前痛哭母亲,感天动地。这个故事和精妙的唱腔让我想起多少人生的痛苦无法解释,忍不住竟然涕泪交加。当时周围都是我的属下,完全是失态。
所以,我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我讲话太多,太容易动感情,真正的政治家不会这样,政治家都是有话也不说,还故意让你摸不着头脑。到现在为止,我坐在电脑前写小说、写自传,包括写信,话也特别多。
中国报道:这就是文思泉涌,所以有人说您是“语言英雄”。
王蒙:我也不好意思说是泉涌,但至少是喷涌。像一个20万字的稿子,我要是改上两月,就变成25万字的稿子了,又改一次就变30万字了。对于参加政治活动,我有一定的积极性,因为政治可以影响更多的人,一个政策或许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但要到政治家的高度,我觉着自己不是。但是,我写东西也并非只是情绪发泄,还是要表达一些想法。
中国报道:您的第二部自传,宣传词这样写道:人生苦旅劫后余生的巅峰表演。书中,多次提到“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八个字。该怎样理解其中“要快乐也要小心”这个标题?读完您的自传后,有人说您通达了,也有人说在有些字里行间看出来您并没有通达。您怎么看?
王蒙:那个“颠峰表演”的标题,是出版社给加的,我自己不会这么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是写我人生当中最不幸的20年。那20年,被剥夺了许多公民权利。但在不幸和艰难的情况下,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改变了很多。我本来属于那种比较敏感、小资情调比较多的人,但是在新疆这20年,在那么荒凉的地方,人变得粗糙了,皮实了。
写《要快乐也要小心》的文章时,“文革”刚刚过去,岂敢大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通达,绝对通达的人是不存在的。我所能做的不是不在乎、不计较,而是我有所在乎、有所计较,同时有所消化,有所超越,能把不幸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验。我会调节自己的情绪,生气、愤怒、伤心,在我这里不会超过48个小时。有时候换个角度、换个思路,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中国报道:从历史上来说,从隋唐开科取士起,中国的文人集体登上庙堂,参与国家大事。您怎么看待历史上的文人从政?
王蒙:历史上好的文人大多不是政治家,文人有时候话多。说得上既是文人又是政治家的,曹操算一个,毛泽东算一个。中国有很多大政治家“厚重少文”,比如邓小平。他不会用很多词,说话言语直白,但他意志坚定,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判断。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人都想从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社会资源都在皇帝国君身上,不给皇帝当差,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你想赚钱,得给皇帝当差;你想推行一项事业,也得从皇帝那里得到支持。一个人的生活资源可能包括物质、财富、手段,也包括权力。所以,中国的士人把入仕作为唯一的选择。
中国报道:您的意思是,要想兼济天下,文人只能选择从政这条路?
王蒙:别说兼济天下,就是独善其身,你能够脱离这个王朝吗?当然,你要是选择饿死首阳山,那也是可以的,像伯夷叔齐那样。
中国报道:您对李商隐非常有研究,曾评论他是中国文人怯懦、热衷功名的典型,说“在他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男人的志大才疏,顶不住命运,放不开功名,梦想着富贵,忍不住寂寞,憋不住牢骚的毛病”。为什么这么评价他?
王蒙:许多特别好的文人,比如李商隐,他作为文人是无与伦比的,那种深情与纯粹,他是在享受语言,能看出来。但是越读他的诗,越觉得他不像个政治家,他不是在官场上能够左右逢源、当机立断、软硬兼施的政治家,不是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甚至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自我保护的政治家。
政治和文学有时候是有关联的。尤其在革命、战斗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爱好文学的政治家。没掌握政权,就会幻象着推翻现有政权的黑暗,进入光明的未来,这就是革命和文学天生的血缘关系,革命需要煽情,而文学是具有这种煽情力量的。文学在批判和煽情产生的能量甚至超过它的建设的力量。越激烈的政治斗争下,越容易产生文学。比如萨达姆就是个小说家,而且写得还不错。另外,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跟第一世界的不一样。第一世界中,政治本身是一种职业。在英国,有专门的机构从小就训练人们怎么当议员。所以相对来说,越是充分多元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学就越是各走各的路。
中国报道:自古以来,文人和官场总是有些格格不入的品质。您体验过这种纠结吗?您说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会让您觉得自己更像一个男人,而文学与艺术更多是女性的事业,这是您对个人性格与经历的总结吗?
王蒙: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视舆论和群体的社会。不管你是多么伟大的知识分子,你搞得太“脱离群众”就不好,办什么事都不方便。所谓投入政治会让你更像一个男人的说法,主要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有更多的承担。说文学更接近女性的世界,这个话也是有点半玩笑的,也就是说文学更感情化,更带有释放性。文学不像发个文件,发个文件要对它负责任,文学没有那么大的责任。
中国报道:但从历史上来说,取得巨大文学成就的还是以男性居多。
王蒙: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但从实践性和责任感来说,搞文学的体验不会很深刻或者直接。比如做一个商人,会更加直接地体验到成败、荣辱和责任。优秀的作家,可以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男性,但如果一辈子除了写小说、写诗,别的什么都不会的话,还是缺少了点刚烈。
中国报道:谈谈您的信仰?
王蒙:70岁的时候我讲老子,就带上了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文化一直寻找的是一个“概念神”。宗教往往是通过一个有特殊功能的人建立起来的,比如,基督教是通过耶稣,佛教是通过释迦牟尼,而道教里,“道”的概念本身就确定了世界的起源和终极。“道”是一个概念,严格地说,上帝也是一个概念,上帝是没有形象的。在这点上,伊斯兰教很先进,它否定一切形象,认为神就在人的心里。依我的看法,如果你是无神论者,那无神就是你的神。你是唯物论,物质就是你的神。你是唯心论,那绝对理念就是的你的神。你认为世界是一塌糊涂,是痛苦,是地狱,那么这些就是你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