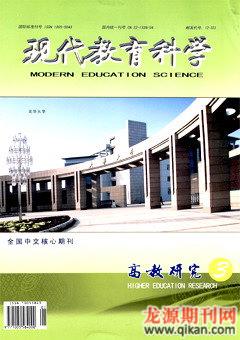阻抗与策略:大学组织学习能力
胡仁东
[摘要]本文在分析影响大学组织学习能力阻抗因素的基础上,探讨提升大学组织学习能力的应对策略,指出大学应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科学定位,通过加强与外界的沟通和合作取得制度的创新,从而促进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
[关键词]大学组织学习能力阻抗因素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3-0005-05
一、大学组织学习能力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是所有组织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换代升级,知识的寿命周期也在缩短。一个组织的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就在于其更新知识的速度,对组织学习能力的考量是越来越严酷。有研究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不断努力改变或重新设计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过程,是组织的创新过程”。以此为基础,我们认为,组织学习能力就是组织在对自身进行适应性变革过程中获取新知识、开展组织创新的能力。大学组织今天面临着十分激烈的竞争,我国正在努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其实质就是要提高我国大学组织的学习能力。大学教育质量的优劣、科研水平的高低、社会服务能力的强弱一直在检验着大学组织的学习能力,因为这些方面反映了大学组织不断变革以适应环境的能力。我国高等教育处在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转型的过程中,高等教育质量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此阶段大学的科研能力却反映着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科技水平,用知识服务社会的能力突出的是从高级知识到中间知识的转化水平。终归一点,大学组织学习能力是关键。构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引进重量级学者只是一个条件,大学自身如果没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是无法维持学校持续竞争力的。在知识高度分工的社会里,学习能力尤显重要。知识需要不断地更新,而知识更新的过程就是对学习能力的检视过程。大学组织的学习能力关涉到组织本身的多个主体:教师、管理者和学生。笔者认为,大学组织学习能力是在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变革中,大学组织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获取、创新知识的能力。
二、影响大学组织学习能力的阻抗因素
1.大学组织定位不准
大学定位不准导致大学行动上的摇摆不定。一所大学的使命是什么,其目标又是什么,应该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稳定性。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呈金字塔型,每所高校都有其合理的位置,其价值取向各有不同。但随着资源争夺的加剧,大学有“攀升”的趋势,初级院校有向名牌大学看齐的办学趋向,却不注重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从而导致目标错位。大学总是要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其存在的合理性理由之一。而大学对社会需要的满足是有限度的,“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它的欲望”。大学自己能做什么应当有一个合适的判断,大学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剑桥大学一位名誉校长曾说过一句极其类似的话:名副其实的大学应以它选择不去做某些事情和它要做某些事情同样知名。大学定位不是一个简单的位置在哪里的问题,而是涉及大学是什么和大学能干什么的问题,正如有人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大学定位是一个体系,它应当包括:目标定位、类型定位、层次定位、学科定位及服务面向定位。大学定位不准,很容易使之迷失方向,缺乏一致的目标,造成资源的浪费,难以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形成强烈的学习动机,从而阻碍学校学习能力的提高。
2.学科间的分割
自康德和哥德之后,自然科学与其他学科就分道扬镳,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学科。在自然科学家看来,自然科学的“法则性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随着知识的不断增加,人们研究的领域将会是越来越细,越来越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可能在当今这个知识激增的时代出现。我们看到的是学科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大学生活显然丧失了它们以往具有的城邦式的各方面学科的有机联系,而愈益像一个搭载乘客的轮船,人们是些偶然相逢的旅行者,不久又下船去,各走各的路”。学科间缺乏有机联系,其后果是学者之间的壁垒越来越厚,隔行如隔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学生在学科的孤岛中穿行,各走各的路,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缺乏融合的组织,其学习能力是有局限性的。学科的发展总是在学科边缘处,而边缘处又总是和其他学科相毗邻甚至交叉,学科要发展,不越过那道分割的界限是无法做到的,因而,知识的过度分化将会导致新的知识生长点缺失。学科间的割裂是大学学习能力的阻抗因素之一。正由于此,人们又强调知识的综合,那些曾经分化的学科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合。
3.学术与行政的二元对立
大学组织是一个学术组织。在这个学术性组织里,学术机构是其核心机构,“院校中每一个学科单位都在第一线工作中拥有不证自明的和公开承认的首要地位”。个体和群体的权威性存在于大量的知识领域,而每一个知识领域都在教学、研究和其他运用知识的活动中扮演着第一线的角色:在大学里,“知识权力”这种魅力型权威应该占据主导地位,行政管理机构应当处于从属的地位。但大学组织的管理者形成了特定的自我利益,以“创造和传播某种正规意识形态”或以某种方式“挤压”学术群体。“教师作出的大多数教育决策,都是经过高等学校的院长、校长和评议员复审的”。另一方面,大学是以学术行会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很容易带有某些弊端,如散漫、偏执保守、排斥改革等等,因此在19世纪,英国和美国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来打开自治的高等学府的铁门,让新的学科进入课程,其中许多学科与人类利益休戚相关,而学阀们却顽固地将其拒之门外一。当学术权威变得根深蒂固时,就会形成以某一个学术贵族为中心的封闭型体系,“由于来自外部的监督被拒之门外,特权就形成了。这样,改革的动机就式微了”。这种学术与行政的二元对立,容易导致学术机构与行政机构的“相互不买账”,形成一种“窝里斗”现象,难以自省,限制了大学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
4.科层管理在大学组织中的异化
传统的教育管理是一种科层化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注重的是正式权威。“权力中心”是科层管理的典型特征,在权力等级这个链条上,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规章制度是维系科层制的重要纽带。超越科层管理则是要清理这一自上而下的操控制度,因为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创新性,那种以“服从”为天职的等级制度扼杀了人们的创造冲动,如果人们有“越矩”行为,就会受到惩罚或处置。在传统的科层式的教育管理中,尽管组织目标的实现是人们表面追求的东西,但它是以权力(或职位)为其价值取向的,个人所关注的是职位的升迁、权力的大小,而不是自己为组织做了什么,也就是说,不是以“创造了什么”为价值取向。所以,这种异化了的教育管理模式从根本上严重束缚了个体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却
开发了个体的“奴性”这一向度。确定性是科层制管理的又一特征,因为科层制正是通过封闭的、“确定无疑”的等级链来实现组织目标。在一个正式的组织体系中,每一道指令的发出和接受必须是“准确无误”的,确定性的后果就是以固定的结构固化人在结构中的角色。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来看,权变性才是当下组织的内在特性,格林菲尔德认为:“人不是在组织当中生活,相反却是组织生活在个体当中,通过个体而存在。”这瓦解了传统的确定性结构,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差异性特点,要求教育管理要尊重人的个性,即个体的非理性维度对组织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人本管理”的模式受到重视,在教育组织管理中愈来愈重要,因为教育组织中,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是从事学术工作的个体的灵魂,而且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恰恰是学者们追求真理过程中“天马行空”所必持的两把“利剑”。如果丧失了这两把剑,学术追求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创新也只是挂在嘴边说说而已。异化了的科层管理限制了大学组织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5.功利主义对学生的影响
在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科学和技术已经被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技术理性时刻影响着我们。学生来到大学,其目标是学到以后对就业有用的知识。通识教育缺失,使现代大学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单向度的人”。在当今社会,人们所专注的领域是专业教育。艾伦·布鲁姆把美国康奈尔大学在专业教育上的态度描述为:“专业教育的繁忙使他们无暇去思考一下,他们的辛苦与努力是否有价值。只重形式和表面规范,而不重内容和实质。在处理通才教育方面,康奈尔大学的计划是要压抑学生渴望通才教育的热情,鼓励他们从事专业的敬业精神和追求,以这个大学的财力和声望去塑造专业和职业第一的精神,这就是该大学的宗旨。”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职业教育。实用主义盛行,学生的关注点不是自身的全面发展,而是钻进一个狭窄的学科,甚至是一门技术,过早地窄化了自己的发展基础,学习能力有很大的局限性。“职业教育主义会导致浅薄和孤立。它贬低了课程和教职人员的价值。它剥夺了大学唯一的生存理由,即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的情况下,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艾略特时代哈佛大学的文理学院哲学思想的关键是肯定塑造“整个学生”比传授特定的知识更为重要。
三、提升大学组织学习能力的应对策略
1.大学组织自身的科学定位
科学合理定位对高校的学习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大学发展目标为员工指明大学要到哪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愿景。“一所办学有成效的大学负有明确的和极其重要的使命。全校的行政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对于学校所要追求实现的目标都有一个共同的见解。这样的目标来自于社会的需要,也来自于寻求教育的人们的需要。。科学定位就是各类学校要找到自己发挥合理作用的位置,“在组织规模日益庞大,组织内部学术分工日趋精细的情况下,明确院校一级单位的职能似乎是主要的解决办法。职能含糊的学校是否能向职能明确的学校转变,关键在于是否能使不同类型的学府的作用合理化”。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每一种类型、层次的大学,都有它各自的“生态位”,越位、错位都不利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稳定和发展,无序的竞争只能破坏高等教育生态系统,而不是促进其发展。英国许多类型的院校冲破原来等级森严的高等教育结构,纷纷朝大学地位靠拢,尤其是向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特色的标准靠拢。技术学院特别容易发生职能变化,一旦成熟,它们就会努力争取获得大学的地位。而这时它们就会放弃原来的服务内容,而这些内容又由其他高等教育部分来完成。澳大利亚学院职能的更替情况也是常常发生。由此我们发现,国外大学也有趋同的现象,它们的大学职能更换特点是:当一所大学争取到了研究型大学的地位时,它就会放弃其原先的职能而不是贪大求全,而它放弃的这些职能又会由其他大学来完成。科学合理的大学定位为组织及其个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个体的学习能力会在“集体行为”一致的情境下得到提高。
2.强化大学组织核心精神
大学的精神是重要的,它使高校不偏离其发展方向。失去了精神就失去了灵魂,何谈学习能力?所以大学精神不能丢弃。追求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探究高深学问,对社会保持批判的能力,始终是学者们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今天,有良知的学者对大学精神的失落深感忧虑,社会对大学精神的失落慌恐不安,公众对大学精神的失落莫名惊异,国家对大学精神的失落危机感陡增。大学精神的失落不能说不是影响今天大学组织学习能力弱的重要原因。“大学特权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它们能招纳富人的子弟并使它们无害于社会,或招纳穷人子弟并教会他们如何赚钱,而在于它们不断地在我们眼前呈现对人类最高能力持久的信任的教育机构时所体现出来的永久价值。”大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高扬其核心精神,核心精神一旦丢弃,人们的追求就缺少了动力,动力的弱化自然会使人们无法集中精力学习;而大力倡导大学组织的核心精神则会形成一种凝聚力,会带动组织成员的学习能力的提升。
3.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与合作
大学适应能力的增强与它的向外界学习的能力强弱分不开。19世纪牛津和剑桥大学的保守使它们面临生存的危机,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它们缺乏一种向外界学习的能力,而伦敦大学则在适应产业革命的迫切需要中诞生。所以,哈罗德·珀金一语中的:“如果社会不能从原有机构中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它将导致其他机构的产生。”伯顿·克拉克在对大学组织转型的研究中发现,大学组织向创业型组织转型不能少于五个要素:一个强有力的驾驭核心,一个拓宽的发展外围,一个多元化的资助基地,一个激活的学术以及地带,一个一体化的创业文化。由此,在提高大学适应能力的过程中必须做到两点:首先是强化管理,在运作上使新的管理价值观和传统的学术价值协调起来,瓦解学术与行政的二元对立格局,形成一种相互包容的环境,增强组织的学习能力,以更好地适应外界的变化。其次要意识到组织其实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组织边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模糊态,而不是去划分明显的界线。法国组织社会学专家埃哈尔·费埃德伯格认为:“外部的世界总是在一个组织的内部展现,因为构成组织的人,也是社会的成员:他们隶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职业种类,以及各种不同的宗教团体,而且他们的行为将这些根本不同的社会影响转变为组织环境。”所以,非要把组织的边界分出个子丑寅卯来,看来也只是徒劳。打破封闭的教育管理模式正是对模糊组织边界理论的一种积极回应。
4.着力于大学组织制度创新
一个好的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潜能。组织的学习能力是存在于个体的学习能力之中的,个体的学习能力又是由组织所激励的。组织学习能力的动力来自组织的制度的激励,建立有效的动力机制对于促进高校学习能力具有很大的推动作
用。“如果在个人利益和共同责任之间保持平衡,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强大的学习社会。我们认为,对大学提出如下期望也许并不过分:大学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习社会,能成为一般社会的典范。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目标与公共的也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创建学校学习共同体,在系统思考的基础上,鼓励个体自我超越,建立学校共同愿景,不断促进心智模式,提倡反思分享学习文化,进行组织学习,不断促进学校真正的持续发展。制度创新首先是要突破原有的管理范式,实现几种管理范式的统一:封闭管理范式与开放管理范式的统一、经验管理范式与专业管理范式的统一、政府控制范式与学校自主管理范式的统一、计划管理范式与市场管理范式的统一。而在这一过程中,将会影响一些群体的既得利益,所以会招致反对。亨利·罗索夫斯基提出的原则为大学组织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第一,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可用更加民主的方法来改进。第二,在一个国家里,公民的权利与参加一个自愿组织所获得的权利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别。第三,在大学里,权利与责任要反映该校承担义务的时间长短。第四,在大学,只有有知识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较大的发言权。第五,大学中,决定的质量是通过自觉防止利益冲突而得到改善的。第六,大学管理工作应当为增进教学和研究能力服务。第七,要使管理的等级制度运转良好,就需要有明确的协商机制和责任制度。
5.重视大学组织文化的培育
大学组织文化是一种粘合剂,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可以将组织凝聚成巨大的合力,增强组织的学习能力,因为它是带有支持其特定使命的价值体系。当文化已经演化到一个团体的共同的体验核心并建立起所谓正确共享背景时,文化就成了一个组织的财富。组织需要学习共同体,需要不断在一起工作和学习,需要建立起强烈的真诚的同事关系,需要养成互相信任和共同尊重的气候,需要拥有分享反思的组织学习文化。大学组织是围绕一门门学科确立起来的,“学者们的最大相同之处就表现在他们都一心一意地钻研学问。但是,他们的最小的共同之处是那种对他们来说都是共同的知识,因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都是专门化的、互相独立的”。学科壁垒是客观存在的,但可以通过文化这种粘合剂来弥合它们之间的裂痕,拓宽视野,消除误解与隔阂,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组织文化的作用在于建立起各种组织行为和组织过程得以发生的边界范围。组织文化有助于创造组织的共同象征、神话和现实世界,有助于参与人员理解模凌两可的事物,形成关于适当行为的一致意见。”其实,培育大学组织文化,就是培育组织共享的信仰、种种期望、价值观以及组织成员行为的规范,在文化上达成一种共同意识,提升组织学习能力。
四、余论
大学组织学习能力的提升必将促进其发展,但大学组织应当对自己做反省研究。组织学习的背后其实是了解环境的变化,学习以适应外界变化。Anron公司的破产引发了人们对组织建设的深思:组织的剧烈变动不容易消灭一个组织,悄悄的变动则容易吞灭一个组织(这符合“煮青蛙原理”)。大学组织不能丧失自己的核心精神,要始终关注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在那里。大学需要迫切反思自己的学习能力,作为一个组织,目前大学的学习能力是无法和企业组织相比的,其危机意识并不强。要改变现状,大学就应当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科学定位,将其核心精神置于中心地位,加强与外界的沟通和合作,力求制度的创新,同时着重培育高校组织文化。
(责任编辑:刘新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