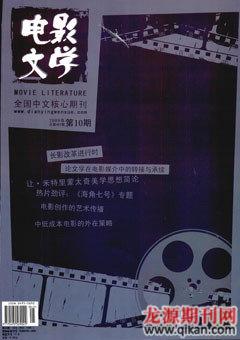探索者的足迹
刘涵华
[摘要]在新潮散文作家中,钟鸣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实验意识。这种实验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具有清醒的文体意识。他主张随笔从散文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二,较为鲜明的文化批判色彩。三,想象力的驰骋和语言狂欢色彩。
[关键词]文体意识;文化批判;想象。语言狂欢
在新潮散文作家中,钟鸣的创作是最具实验意识的。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城堡的寓言》《畜界·人界》《徒步者随录》《旁观者》《秋天的戏剧》等多部散文集,并引起较大反响。北京大学的余树森、陈旭光在《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就曾给予高度评价:“钟鸣的随笔体散文异军突起,融贯中西散文随笔传统而又有自己独特的发挥与创造,他为随笔作为独立文体所作的理论思考和努力实践,在散文史上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样的评价过高,并认为其作品无异于“天马行空的语言自恋”。这种各持己见而又相去甚远的评价,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钟鸣散文的某种意义和价值。本文拟就钟鸣散文的特点做出简要分析。
一、清醒的文体意识
所谓文体意识,是指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艨胧的心理把握。钟鸣的散文创作一开始就具有清醒的文体意识。他极力主张将“随笔”当作一种独立的文体,从散文中分离出来,并且认为“随笔已由于它传统的使命感和在现实中逐渐成为‘一种非语言的反论符号而成熟起来,以至于成为知识分子的文体或知识分子的写作风格”。这种清醒的文体意识使得钟鸣的散文创作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处于懵懂或自在状态的写作活动。
作为一切文章的母体,散文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分崩离析:通讯、报告文学、自传、回忆录等等陆续分解了出去,而随笔。作为一种亚文体,目前正处于即将走向成熟并脱离母体的状态。而“知识分子写作”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由一群年轻诗人提出的与“民间写作”相对立的创作口号。他们认为诗歌的创作首先是一种对艺术负责的写作态度,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对诗歌语言的精密处理,充分发挥各种写作技术的艺术效果,从而准确地表达诗歌的主题。作为诗人的钟鸣,将诗歌界出现的“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概念平移到散文界,主张以知识分子的姿态进行散文创作,并进一步以自己的散文——或随笔创作实践这一主张。
对于自己的随笔创作,钟鸣曾经明确地指出其创作意图:即使做不成“由英雄们的不同心性和冥想构成的、既是英雄的向往所在,也是英雄挞伐旧秩序和宿弊所在的……英雄城堡”,也要“给那鹄立在陡峭山岩上的城堡,送去自己的一丝呼吸,几块惨痛、但却灼人的石头”。——这也就是说,从文体的角度看,钟鸣认为自己写作的是与抒情、叙事散文有所不同的随笔;从思想内容的角度看,其随笔创作又担负有某种不无艰难的社会责任,或者说具有某种启蒙性或文化批判倾向。
钟鸣散文——随笔的创作就是在如此清醒的文体意识指导下进行的。
二、文化批判
钟鸣20世纪70年代服过兵役,并曾到越南参加过战争,改革高考制度后又进入大学读书。丰富的人生经历使钟鸣较早获得了个体和文化意识的觉醒。在他的随笔创作,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不无深刻的文化批判。《关于曼德尔斯塔姆的黑太阳》一文,大致记叙了作者对俄国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及其诗作的理解与评价。
曼德尔斯塔姆是表达“对世界文化的眷念”的阿克梅诗派的重要成员,他“透过历史文化的比较和联想,对各个文化历史时代、对现代及其前景进行思索”。“曼德尔斯塔姆虽然理智上理解革命到来的必然性,却不能接受其破坏性的方面。”因而“不为新的现实所需要,为新的现实所抛弃。”在《关于曼德尔斯塔姆的黑太阳》中,钟鸣对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和其诗作历史价值的理解是深刻而令人回味的:“当一个时代,借助社会的本能和权利的惯性,放肆营造文化平面气氛时,诗人便会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他的死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了诗的有效性。”
在《侏儒野史》中,钟鸣用真真假假的叙述表达了对中国数千年以来的封建集权制度及其衍生物的反讽:“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是矮子。确实,当你周围尽是和自己一样高的人时,你又怎么能知道自己就是那闻名的侏儒呢。所以哲学家尼采说,有种侏儒就踩在我们的肩上,它是一个精灵,但却像一个侦察兵,随时都可能跳下来。当他跳下来,蹲伏在你面前时,它会告诉你,所有的真理都是弯曲的。当然,也并非全部是。”
需要指出的是,钟鸣的文化批判并不是用传统的方式、从正面直接进行的,而是夹杂在大量类似寓言加想象的“奇文”之中,人们常常会在貌似荒诞不经的行文中突然感觉到思想的光芒,明亮耀眼,但随即又尘埃落定,仿佛什么也不曾有过。或者说这种批判带有比较明显的诗性特征,它曲折含蓄,同时又尖刻犀利,隐含着的锋芒既令人捉摸不定,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两者所形成的巨大张力,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而且给人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启示。
应该说,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继承并发展了鲁迅杂文的某些特点,在思想上也与五四时期的反封建主题和“国民性批判”有着承续关系。由于市场经济及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新潮散文作家片面追求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削平深度”,有意无意地放弃了作家应该勇敢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启蒙意识,使散文的整体思想品质有所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钟鸣的写作表现了对人类现实生存状况和精神生活的深刻批判。钟鸣的视野是广阔的,立足于此的思考也是严肃而认真的。他用艺术形式上的种种尝试,成功地打破了某种话语空间的密闭性,使自己的随笔创作向着更为广阔的意义空间敞开、向着更自由的精神境界冲刺。
三、想象力的驰骋和语言狂欢色彩
钟鸣的随笔最突出的特点是想象力的驰骋和语言狂欢色彩。林贤治认为:“钟鸣的随笔也有着自己的叙述语言,典雅、跳宕,不乏想象力和幽默感,其中最突出的,也最为人看重的是‘引书以助文。”
所谓“引书助文”,就是频率很高地引用古今中外的各种文献资料,或讲述事件,或印证自己的观点,并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文风,颇有点当年周作人“文抄公”式的文体特征。但是,与周作人引用大量古书有所不同的是,钟鸣的引用常常以想象为桥梁,语意由此及彼,跳跃而曲折多变,就此形成一种使人真假难辨的艺术效果。他似乎是充分地沉浸于古旧的书本和自己的想象中,由此构筑起令人耳目一新确有将信将疑的文本。《鼠王》是钟鸣散文中的“名篇”,其中引经据典地记叙了唐鼠、香鼠、隐鼠、红飞鼠,土拨鼠等,简直就是一个老鼠的文字世界。然而,他并未涉及任何一种老鼠的生物特性,而是仅仅是梳理它们在文字世界里作为符号的意义,其中有许多种老鼠也许只是在文字记载里才存在过的。如他写鼠王:“大地有乌合之众,土里有乌合老鼠,统称‘鼠王。这是加斯卡尔对‘鼠王性质形而上学的限定”。这样,“鼠
王”似乎就成了和人类社会有着某种对应意义的符号,但是人们又无法像对号入座那样丝丝入扣地将两者联系起来。——因为,这个文本世界说到底是作者钟鸣驰骋个人想象力的即兴之作,就在这种若有若无、若即若离之间,读者所得到的根本不是关于老鼠的认知,而是一种极为新奇的艺术感受。或者可以说,《鼠王》是钟鸣以各种支离破碎、或者干脆就是杜撰的所谓“经典”为材料,以自己的想象为蓝本搭建起的一座文学迷宫,其中某个局部可能具有某种象征和隐喻意义,但说到底,象征和隐喻并非文本的主要目的,而建筑(对于作者而言)或走过(对于读者而言)迷宫本身才是其基本意义和价值所在。
应该说,这样的随笔作品和上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一样,都是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具有某种实验意义的文学作品。相对于80年代盛行的带有“伤痕”色彩和乡土色彩的两类主流散文,90年代的新潮散文特别是钟鸣的随笔具有明显的超越意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价值首先并不在于建构了什么,而在于继巴金和贾平凹之后,再度解构了某些早已成为束缚的陈规戒律,为散文随笔的创作清理出一片曾经人所不知的空间。
语言狂欢色彩。巴赫金在谈到狂欢理论时曾说:“如果文学直接地或通过一些中介环节间接地接受这种或那种狂欢节民间文学(古希腊罗马时期或中世纪的民间文学)的影响,那么这种文学我们拟成为狂欢化文学。”“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转化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散文相对于小说而言,“没有较多的技巧可以凭借,因此在艺术表现的形式上,主要就得依靠语言本身的光泽了。”
诗人出身的钟鸣具有良好的语言天赋,在随笔创作中,他有意营造巴赫金所说的那种狂欢效果。一般来说,语言的狂欢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言材料的选择,以绮词丽句争奇斗艳,声光色味交错杂陈,形成美不胜收的审美愉悦;二是语气语势的营造,或以排句形成势不可挡的气势,或以不断变化的句式形成摇曳多姿的语气。钟鸣比较看重后者。他对语言材料的选择大体上是以质朴传神为目标的,很少用所谓华美的词藻造成延宕的艺术效果,但他总是竭力追求一种节奏较快而且语音铿锵的通达与流畅。语言在表达事物属性时总是有局限性,具体属性有时常常不可穷尽或难以精确表达,这就难免使人意犹未尽。对此,钟鸣常常以排句的形式加以弥补。如《变色龙》的结尾提到老子及其哲学:“老子是道家的祖宗,皇帝们的宠儿,百姓的救星,悲观主义的说客,享乐主义的律师,末日的预言者。”又如《鼠王》:“人们担心猫的失灵,甚至在指头上、耳根上缀满了沉甸甸的,象征性的猫眼石。还把已移植到脖颈、胸脯、手臂、腹部甚至鼻端的珠宝,看做是猫眼固定的硬化效果。另一方面,食人眼鼠王的出现,完善了人类的厚葬,东方的两大裹尸技术,便是埃及的木乃伊和中国的厚棺。人们越害怕老鼠,憎恨薄土,便越是想通过巨木或其他材料,来加强自己死后的宽厚度和坚韧性。在中国棺椁的厚度,标志着地位的高低。厚厚的楸木棺材,加上周围无边的泥土,这样,人们便以为老鼠要吃死人的眼珠几乎是不可能了。但这仅仅只是形式上增加了一点难度而已。因为这种厚葬,反过来又唤起了鼠类世界性的强烈的穿凿欲。”这些都是在思想接踵而至应接不暇之时,一路放纵笔墨而形成的狂欢效果。从外在形式上看,这种狂欢增强了语气和表达效果,从其思想内核看,无疑是作者生命在自由自在的状态下,元气淋漓任意挥发的自然表现。
当然,钟鸣随笔也存在有较为明显的不足。从整体上看,早期的随笔更具有历史担当意识和批判精神,思想性较强;而后来的散文,批判色彩越来越淡,语言游戏色彩越来越浓,因而被林贤治批评为“挤满各种文化信息”,“不但炫耀知识,而且炫耀身份”。这样的批评虽然太过于尖刻,但也确实不无道理。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所必需的历史责任的担当,后现代的游戏色彩当然要轻松得多,但也就是在这种轻松之中,作家有可能渐渐地丢失了自己,也偏离了当初认同知识分子写作的初衷。关于这一点,沈从文当年在《风雅与俗气》一文中就已经批评过,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