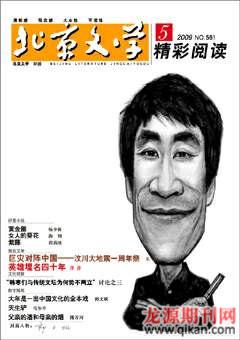父亲的酒和母亲的烟
傅万河
一
父亲早年是不饮酒的。
这除了家庭生计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本人不太得意(喜欢)。用老人自己的话说,没有这个口福。晚年儿孙满堂,逢年过节,大家都急着往家里赶,山珍海味谈不上,老爷子的酒自然是少不了的。到了他孙子们这一辈,出手更是了得,什么“茅台”、“五粮液”,甚而“白兰地”、“法国干红”,都想让老爷子补上大半辈子的缺。父亲有时高兴了,也会烫上一壶,不多饮,只三盅。三钱左右的小酒盅,约一两。这时父亲的面颊便会慢慢红润起来,一脸的皱纹都舒展开。我的侄儿们便争着抢着抱过他们的孩子,一个一个让太爷爷亲。父亲便在每个孩子的嫩脸蛋上嘬一下,嘴里还不停地夸着,“俊,真俊。”灯光下看老人,长长的眉毛抖动着,两只眼睛流闪着一种异样的光,往日的威严全不见了,一脸的迷醉,一脸的慈爱。往往这时大嫂就开腔了:“行了,行了,别都来献宝了。看给老爷子累着。”父亲总是笑着说:“嘿,过日子过的是啥?过的就是人嘛!”这仿佛成了我家春节的保留节目,一直延续了十几年。好多年以后,当我的小孙女偎在我的膝弯,仰着颏注视着墙上父亲的照片,天真地说,“爸爸的爸爸是爷爷,爷爷的爸爸就是太爷爷了。”我的心中就会自然地重播出那无比温馨的一幕。
二
母亲吸烟,比父亲沾酒要早得多。
在良玉古镇西头,也就是蜈蚣岭和西庙之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沟。小河沟两岸是簇簇拥拥的绿柳,柳阴间便散落着十几户郭姓人家。母亲的姥姥家就姓郭。母亲十六岁那一年,(父亲比母亲大九岁,那当是1925年),灾荒加兵患,姥姥和姥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和村里人搭帮举家逃荒去了黑龙江省。也正是这一走,铸就了姥姥和姥爷悔叹了一辈子的事,狠着心把她们的大女儿嫁给了穷山沟的老屯,为的是那一点点逃荒的盘缠钱。当然,这户人家也是根本人家,虽说是山旮旯,倒也能吃口饭。姑爷岁数大了点儿,可老实巴交,想来闺女嫁过去也不能受气。这就是姥姥、姥爷对我母亲———兰儿婚事的全部判断。父亲广墨在良玉集,从驴驮子上卸下了几百斤谷子,换了钱,便由三爷领着(三爷是父亲的三叔,庙里的香火,跟郭家关系极好的),又用驴驮子驮回了自己的新娘。十七八里的山路,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一句话也没有说,倒是三爷哼哼呀呀地喊了一路梆子腔。他当然很开心,能给二十大几的侄儿说上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又仅是几百斤谷子的价,三爷的心里该有多敞亮。可怜了我的母亲哟,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儿,幼小的心灵怎能装得下这么多的离愁和悲苦,那稚嫩的双肩又如何去承载日后生活的重负。
这是母亲开始吸烟的日子。
如今的女孩儿结婚,要多排场有多排场,要多气派有多气派。有人特意坐飞机去北京举行婚礼,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新婚照。说不定再过几年,人类的青年男女到月球上度蜜月,怕也是极为普通的事了。这是多么温馨和谐的时代,又是多么让人异想天开的时代。然而,八十多年前,在战争和苦难折磨得人类奄奄一息的岁月里,母亲的新婚之夜只是一盏豆油灯和一笸箩老旱烟。老姑见母亲不吃不喝,便给母亲找来了一个小烟袋。聪明伶俐又能说会道的老姑,是爷爷的老闺女。在我的记忆中,老姑是我们家几代人里最受尊敬的老姑奶子。尽管她比母亲还小上好几岁,却成了我母亲抽烟的师傅。那时光,在北方,特别是在东北,女人抽烟,是极普遍的。“关东山,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大姑娘小媳妇叼烟袋。”这就是关于母亲抽烟的时代和由来。
三
父亲是20世纪的同龄人,生于1901辛丑年。父亲母亲共生育了我们弟兄姊妹八个孩子,当我这个老疙瘩出生时,父亲已经是知天命之年了。翻身、解放,共和国成立,好日子就像春天的柳树芽,一天发一茬,一天一变样。那时大哥参军在外,父亲母亲带着二哥、三哥、大姐一帮孩子侍弄地,当年就是个秾收。秋下来,别人家的庄稼用车往回拉,我家人多,十多亩地的高粱、苞米都是肩膀扛回来的。看着刚刚上学的四哥五哥也去扛秫秸,村里人都说,老傅家还能不发起来,连小猫小狗都往家叼柴火。那一年就盖起了三间土坯房。那一年大哥也就结了婚,娶了嫂子。那一年我也就急急地来到了这新中国的土地上。我的乳名叫连喜,这大概就是父亲给我起这个名字的缘故吧。
多年的艰辛岁月,四十多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奶水哺育我,我从生下来就是大姐嚼子喂。再后来便是在一家人熬高粱米粥的大锅里,用纱布缝个口袋,放入少许的粳米,这是父亲特批给他老儿子的“高消费”。及至上学时,就是高粱米饭。父亲总是用筷子剜一点猪油给我拌饭。我嘴急,又怕迟到,常常像尾巴一样在父亲身后转。父亲便用他那粗糙得像榆树皮一样的大手捧着碗,细细地而又急切地用筷子搅拌。嘴里一边吹着,一边还说,“凉凉热热,莫烫小狗屁股。凉凉热热,莫烫小狗屁股。”四岁那一年,我得了荨麻疹,俗称鬼风疙瘩,浑身奇痒难耐。父亲就用他那双像老钢锉一样的大手给我摩挲。边摩挲边哄我,“喜子听话喜子乖,爸给喜子买糖来。”“喜子听话喜子乖,爸给喜子搭戏台。”……我便在父亲的臂弯里睡去了。
母亲说父亲后来能饮一点酒,和我两岁那年生日有关系。那天,父亲和互助组的李老井一起去石山站赶集,为的是买黑龙江克山的土豆种。傍晌午一场大暴雨,回来走到望山铺,山洪便下来了。李老井说找个人家借个宿,水过去再走吧。父亲从怀里掏出给我买的虎头鼠皮帽,说,今儿个是小老疙瘩生日,说啥也得赶回去。傍天黑水也是小了不少,父亲便趟着水往回赶,不料正溜的水还是挺猛的,一下子便被卷走了。后来父亲回忆说,山水把他冲出去十几里地,被一个土崖子的老榆树根子挂住了。黑夜里,他艰难地爬上岸,见有一个小窝棚,里面亮着灯,父亲便挣扎着去拍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救了他。换了干衣服,喝的小米粥。父亲说吃大葱叶子都不知啥味,耳朵里感觉就像驴吃草,咔噌咔噌的。后来父亲专门提着礼物去谢过,但怎么也没有找到。那处河湾的西面就是驿马坊,打听谁也说不清哪家在河东有瓜窝棚,又是谁家的老太太。打那,劫后余生的老父亲便落下了胃寒的毛病,偶尔心口疼,就点燃一盅酒,和着红糖送下。那一场险些夺去父亲生命的山洪,让父亲沾染了酒。大姐说,第二天父亲回到家,进屋就趴着悠车看老儿子,手里还比量着那鼠皮的虎头帽儿。
四
母亲活了八十七岁,抽了七十一年烟。每逢年节,儿孙们回家看她,就有心思劝她老戒了,为了身体。老人总是抿嘴笑,说这一辈子就这点口福。有时还和大家开玩笑,说毛主席、邓小平抽了一辈子烟,不也都高寿吗。常常弄得人们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母亲抽烟是十分节俭的。就连点烟的火都不肯破费,冬天是火盆,夏天是火绳,早晚做饭就在灶膛口对着了。直到八十年代,日子好多了,也如此。母亲抽烟一辈子,从没挑剔,大抵都是自家种的。年轻时孩子多,日子艰难,没黑夜没白日地劳作,只有抽一口老旱烟,才提神、缓劲,也解忧愁。我在另一篇散文里曾写到母亲为孩子们做鞋的情形。一大帮孩子的鞋都要自家做,还要缝连补绽,光景稍好的时候,还要纺棉花,织土布。设若没有老旱烟,母亲那超负荷的劳作,又怎能撑得过来呢。那时还没有后来的黄烟,都是青烟,俗称蛤蟆癞。母亲说,她最艰难的时候连茄秧叶子都抽过。父亲得伤寒病那一年,连熬药的柴禾都没有,母亲捡来别人家丢掉的烟梗子,用米汤泡了,砸碎,再晾干来抽。天知道,母亲的身体竟出奇的好。晚年八十多岁,也不咳嗽不喘的。这也许是上苍(如果真的有上苍的话)对母亲额外的垂怜吧。
母亲一生抽的最好的烟,是吉林的蛟河烟。那是五十年代初,郭守信二舅(母亲的表弟,也是逃荒落在吉林的),回里城家给母亲带来的。据说蛟河县也只有几亩地才产这种烟。关于里城家,我们这一带凡逃荒到吉林、黑龙江的人,都管辽西的原籍叫里城家。这是否就是由柳条边来的,我不甚清楚,过去有东边外一说,我想辽西对于东去逃荒的人,就是边里的家,里城家了。尽管后来借出差的机会,我曾为母亲买来过湖南的“凤凰晒”,云南的上等云烟的“大金叶”,甚或河南的“黄金叶”,陕北的“油绦子”……母亲都说不如蛟河烟,不如她表弟捎给里城家的烟。早已经谢世多年的姥姥、姥爷,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出走,给里城家的女儿留下的创痛,是多么的悠久弥深。
五
父亲和酒,似乎还另有一些渊源,抑或一些故事。如今却是我无从知道,也无法弄清的了。记得是父亲六十六那一年,(在我家乡一带,老人到了六十六,好歹都要办一办的。老话说,交年六十六,不死也掉块肉。又按从古至今的干支纪年,人到六十六岁,是又一轮六十甲子的初始阶段,所谓六十花甲子,花甲重开。)正是“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到处都在破四旧立四新,父亲的六十六自然不能稍事声张,但哥哥姐姐们还都是远远地赶了来。住在老屯的四叔、老姑他们也都来了。四叔是逢酒必喝,又酒后话必多的人。席间,四叔不停地教训我们哥儿几个,你爸你妈拉扯你们八个不容易,到啥时候也不能忘了父母的恩德。父亲就说:“老四,你高了,歇着吧”。四叔却红涨着脸:“大哥,要不是那年你那三碗酒,咱这贫雇农的成分真就整瞎了。你看咱这帮孩儿,当干部的当干部,挣工资的挣工资,连老三还是贫农主席,一家子都是根红苗正。你再看那西院万贵,儿子孙子都是黑五类、狗崽子,当兵都不叫当……”四叔说的老三是我三哥,当时是生产队的贫协(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万贵是我们老家老屯的富农。这在讲成分比如今出国护照还重要的时代,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确是至关重大的事。父亲淡然一笑,简单地说了下始末。最后说:“纯粹是扯淡,哪有地主富农还选的?”
那是一九四八年,除国民党占据的锦宁线上几个大城市,辽西山区大部都解放了。我们的老家老屯,就是爷爷以及上几代赖以生息的地方,属义县和北镇县交互管辖,大山沟里的一个小沟岔子。全村二十来户,都是傅门子孙。村长是东院广明大爷,伪满时是村长,国民党时还是村长,共产党来了还是让他张罗着。这个人其实也不坏,只是过于精明了。土改工作队自然要分地,要划成分,就觉着山外十里八村都有地主、富农,老屯不管咋着也得有。于是就要选地主。那时人们别说政治觉悟,啥叫阶级也弄不明白。可地主就是财主,财主谁也不愿当,谁也不敢当。都知道当财主就得往外掏东西、掏大洋。老屯的人都是靠老辈开荒传下那点薄地,哪里有大洋可掏。全村十多户,七十多口人,就数西院万贵家日子冒点尖儿。他哥万春在外面做事,听说是做大学问的。万贵在家拴了一挂车,有一头骡子一匹马。再下来就是东院广明大爷和我爷爷家了。广明有两头牛,爷爷家有一头驴,几只羊。爷爷家劳力多,父亲是大头顶,哥儿五个姐三个,也是八个孩子。劳力多,种的开荒地也就多一点。于是爷爷就害了怕,叫四叔连夜把父亲喊回了老屯。那时我家就是父亲和母亲带着孩子们生活的家,在闾阳镇。因为母亲的姥姥家在这儿,所以父亲就落脚在这镇西蜈蚣岭屯了。那时闾阳驿叫良玉,现在老辈人还这么叫。我猜这与闾阳是个古驿站,闾阳驿的转音怕是成了良玉了。
于是,一九四八年那个冰封雪冻的腊月里,一个只有十八户的小山村,在历史车轮就要辗过天翻地覆的一霎,演出了这么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广明老大说:“不用费事选了,万贵就是咱村的地主了。这富农,就是老院老爷子(指我爷爷)。”我父亲说:“为啥?”广明就说:“你家有驴,还有羊……”
“那你那两头大犍牛不比驴硬实?”
广明语塞。就从条桌下捧出一坛酒,刷刷刷地倒了三海碗。广明说:“广墨(我父亲的名字),你要喝下这三碗酒,这富农就我当。”父亲瞅瞅这一屋子老傅家人,那一刻,他看见了缩着脖、蹲在灯影里的万贵,他也看见了一直咳嗽不止委在炕头的我爷爷,他更看见了精明的广明那捉摸不透的眼神……这就是历史大变迁前夜,在我的老家老屯发生的一件荒诞不经的事。父亲六十六之后,再也没谈起这件事。那天父亲说:“长了这么大,就那么一回。那酒也不知是咋下去的。”伟大的时代对老实人来说,也不免开一个小小的玩笑。特别是我父一辈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精明的广明大爷没能成为富农,窝囊的万贵也没能成为地主。战争年代的土改有好多事是说不清的。广明大爷的阶级觉悟受到工作队的口头表扬。委屈了万贵,一骡一马才当了个富农(其实以万贵的资财,按当时的政策,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中农)。一九五七年我七岁时,随父母回过一次老屯(那是为爷爷的丧事),曾见到过万贵的哥哥万春。村里人说,他是北京的大右派。这位本家哥哥那时已有七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很清瘦,戴副深度眼镜,须眉皆白。他很谦恭地称我母亲为“婶母大人”。我曾暗下里揣度,他大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西院万贵的儿孙们确如四叔所说,颇是享受了一些狗崽子的待遇。万贵四个儿子中,有两个终身没有女人肯嫁给他。我也曾想过,设若父亲当年不饮下那三碗酒,像四叔说的把成分搞瞎了,那我和我的哥哥姐姐,甚而我的子侄们,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父亲,也许您后半生喝的酒,加起来也没有这三海碗。但儿子说,这酒,您喝得值。这是好多年之后,给父母上坟,我在心中默默诉说的话。
六
在我们村,因为是母亲的姥姥家,母亲是本村的姑奶子,所以村中人多数都管母亲叫大姐,我的舅舅就特别的多。年轻但占着辈分的往往又在称呼前加上我们的姓氏,称老傅大姐。母亲心肠热,所谓刀子嘴豆腐心,最见不得别人的眼泪,凡村中人有为难遭窄,皆尽所有。计划经济年代,因外边有几个儿子挣工资,母亲自然比光靠工分的人家宽绰些。这自然也成了母亲接济别人,甚或队里集体的经济基础。我家的三间土坯房,一直拖到八十年代后期才翻建。在此期间三十多年的时光,几乎成了社里、队里的公家财产。土改、合作化、四清……什么时候的工作队、工作组,凡上边来人都派到我家。“文革”中的知青、五七大军更是常客。志愿军抗美援朝乍回来,没建营房前,团部就设在这三间土坯房里。这在时下的电视片中是应该叫“堡垒户”的。生产队的会都愿在我家开,即使有了队部,也一样。我说这些其实并不是想表白什么,我要说的还是母亲的烟,母亲那磨薄了底,磨破了边儿,补了又补,粘了又粘,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本是柳条编的烟笸箩。那时光,凡有人来,母亲除了糊米水(在我家乡,人们常常将高粱米炒糊了,再用滚水冲来当茶饮。至今老辈儿人仍如此),便是老旱烟。母亲的烟笸箩,好孬是从来不能空的。大哥说,回老家别的都差些,千万别忘了给老妈补充烟叶子。二舅和三姨谁从黑龙江来,都是整麻袋的烟把子。
几十载春秋过去,母亲的小烟笸箩,消耗了多少老旱烟哪!
关于母亲和烟,村里人有许多传说,有的甚至很玄。比如说母亲很有远见,用两把子烟救了文波书记。说实话,母亲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个农村老太太,她能有什么远见,她又怎么知道文波同志后来走上那样高的领导岗位。她只是按照她的生活信条,她的做人本性罢了。那是“文革”最晦暗的一页。当年曾在我家住过的工作组老刘———刘文波作为地区的“走资派”被造反兵团围追堵截,在大苇塘、高粱地窜了几天。走投无路之时,夜里摸到我们家,亏他还记得这三间土坯房。当时文波同志真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母亲差一点儿都认不出来。瞅着老刘吃得那样香,就像多少天没吃东西。母亲说:“老刘啊,你咋成了这样?”文波同志哽咽了:“大妈……一言难尽哪!大妈……”县里的造反派连夜搜到我家时,母亲已让老刘睡下了。噼哩拍啦的敲门声中,母亲灵机一动,找出几把烟,包扎好放在柜盖上,又拿出帆布旅行袋胡乱塞了些水果罐头、衣服之类的东西。造反司令是县里农具厂的工人,问母亲炕上躺的是谁。母亲说,是我儿。是我大儿回来了。司令说莫不是走资派刘文波。母亲立马指着司令说:“什么走资派不走资派,你胡说。走资派能给我买烟、能给我买这些东西?”把柜板拍得山响。司令是个胡传魁式的人物,又被我母亲掖上两把烟,(显然他也是个烟客,且不喜抽洋烟的)也就悻悻然走了。“文革”后,文波同志恢复了工作,到了省检察院。母亲告诫我们全家,谁也不要提起那档子事。只是文波同志曾专程看望过母亲,给母亲的礼物,竟也是两把老旱烟。还一再说明,这是纯正的蛟河烟。
七
父亲识字不多,十二三岁就给良玉一家叫德盛永的站栏柜,那时叫学徒,现在说就是打工,且是童工。我有时猜想,父亲能写毛笔字、会打算盘……恐怕就是德盛永那两年苦出来的吧。
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二十年了。作为上个世纪中国北方的一个普通农民,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也没有什么要言妙论,甚或关于酒的点滴趣闻。他没有文化,也就谈不出什么酒文化,哪怕时下那些餐桌上必有的酒段子。然而,父亲却用他的人生,酿给了我们永远品味无穷的老酒。那是一些多么富含哲理、充满智慧的思考啊。比如他说“见好就收”。那其实就是直白不过的凡事适可而止,似乎也就是先贤们所言的急流勇退。记得父亲八十寿诞时,老人和长孙有一番对话。爷爷说:“中南海呆了几年了。”孙子说:“十二年。”于是老人就说见好就收。于是孙子就转业了。
比如他说“拿人心比自己”。其实也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今天的换位思考。那个年代,队里青年点的伙食都不好,有些知青就常来我家“贴补贴补”。我那时在县里,有一次回来听说,上海那个小魏子,魏积雄,尝黏饽饽就尝了八个。父亲就说,都是熬克的。我那几个孙子不也一样吗?就是离着远。真的,我的侄儿侄女那个时代就有八个下过乡,老大当特种兵也是从青年点走的。无怪乎父亲八十大寿,那些回了城的年轻人,抚顺、鞍山、大连,甚或哈尔滨、上海都赶来了。
又比如他不只一次地对我和几个哥哥说,当干部莫错了一个念头。喝凉酒蹋官钱,早晚是病。如今大哥过年也八十了,我也快退休了。弟兄子侄中做干部、亦即公务员的,有公安、司法、金融、税务……少说也十几、二十多个,这些年也未闻有一个半个和腐败案子沾点边儿的。两年前“804”案爆出,网上炒得很厉害,大哥给我打电话质询,口气十分严厉。我则诙谐地说,那样的好事找不着你老弟。父亲临终时曾叮嘱我:“你太聪明,太要强,又太拿事儿,太不服软……”父亲哪,你其实最挂念的还是你的小老疙瘩啊。
少小的时候,听父亲说话,句句是真理,仿佛高远的蓝天,明净、澄澈;三四十岁时,又感觉父亲的话那样浅显明白,像平川旷野,一览无余,似乎也不绝对真理;如今再咀嚼父亲的话,竟又如云雾深处的密林古刹,幽远、深邃,久索而难穷其味。
父亲,您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具学识的人。父亲,您更是我一生永远也读不完的经典。
八
如果说母亲的吸烟是历史的误会,那么,在母亲吸烟的历史上,却也有些颇具风采的趣事。父亲的伤寒病总是不见好,爷爷便叫二叔把父亲接回老屯去养。大哥、二哥、三哥能干点活儿的也都回屯了。母亲便领着大姐和四哥,怀里抱着五哥,随着逃难的人流北上去了黑龙江。那是母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回娘家,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当年姥姥姥爷逃荒落脚就在这绥化北的海伦一带。大舅为人敦厚,有的只是力气,便在林子里拉木头。二舅较精明,在铁路上谋个差,只是个半拉木匠。姥姥、姥爷则带着孩子们开镐头荒。日子虽然不富裕,依然紧巴紧拽,但吃饭基本没大问题。大姐后来说,住的都是马架子窝棚,苫厚厚的草,院子用板皮夹着板障子。整天土豆、大子粥。家家都种毛嗑(向日葵),种黄烟。女人都抽烟,说话打唠都嗑毛嗑。这对我母亲和孩子们来说,已经不啻福窝,简直就是天堂了。姥姥家的王家窝棚离海伦县才十几里路,日本的关东军都开上前线,进关打仗去了。海伦的驻军并不多,但也时常下屯里来骚扰。年轻点的妇女,像二姨三姨这样的姑娘们整天提心吊胆。二姨说,那几个鬼子也都抽烟,一来就“打巴勾,打巴勾”地要黄烟。母亲便说,赶明儿个再来,我逗试逗试他们。这其实不过是一种恶作剧。在我家乡,新姑爷来老丈人家拜年,总是要遭到小姨子们围攻的,什么招儿都有,叫“耍姑爷”。有的笨姑爷也常被抹一脸锅底灰,叫“打画迷”,有的甚至被弄得鼻青脸肿。但“蛤蟆尿”一般是不能用的,闺阁中也都明白,怕给人坐下什么毛病。今日看来,对于手无寸铁又被欺侮的中国妇女,这也未尝不是惩罚敌人的一种机智。于是姐妹们便抓来许多公蛤蟆,专拣那个儿大的抓。把晒得通红的黄烟叶铺下,然后放上蛤蟆,扣上铁盆。蛤蟆们折腾够了,铁盆里安静下来,便用棍子在铁盆上猛然一敲,蛤蟆突受惊吓,就把尿蹿在烟叶上。如此反复几次,蛤蟆就没尿可蹿了。这样再晾干的烟叶,人抽了,万万受不得惊吓。有一点外界刺激,就大小便失禁。我长大后,老姨曾对我学说过:“那几个鬼子抽完‘蛤蟆尿之后,都贼眉鼠眼的,冷不丁一听我们放鞭炮,什么井上、松下、矢村的,都尿滚尿流蹽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借在哈尔滨参加一个会议的机会,我曾专程赶往海伦。彼时姥姥、姥爷早都不在了,二舅已退休在家,住在海伦城里北街。我曾绕着县城走了大半天,这是一个不大的县城(现在已经是海伦市了)。高大的建筑并不很多,但很干净,城市绿化得也很好。没有大都市的喧嚣,确像一个女性化的年轻城市,静静地偎在松嫩大平原上。是哪位先哲给她命名为海伦的?这年轻的小城和古希腊神话东方美女海伦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听了老姨讲的故事,我曾有些疑惑,我那吃苦耐劳、心地慈善、勤勉了一辈子的老母亲,苦难的生活教会了你抽烟,那是一种麻醉和解脱,可你却把烟草演绎出这样的极致。母亲,关于烟草,您还有哪些故事没有叫儿子知道呢,那不应该叫儿子知道吗?
九
在父亲走后的日子,老姑订正了父亲与酒和母亲与烟的史实。老姑说,嫂子不会抽烟,我见她一脸悲苦,又一整天水米不进,赶明儿这三朝可咋办?便教她装烟、点火。在那时代,装烟是有很多讲究的。新媳妇进了门,拜天拜地拜公婆,然后才是入洞房。第二天起一连三天都要给公婆请安,这叫拜三朝。最重要的便是给婆婆装烟。彼时,新媳妇要亲手给婆婆装上一袋烟,且毕恭毕敬地递到婆婆手里,然后用取灯(火柴)划火、点烟。婆婆在接过新媳妇装的烟之后,很庄重地抽着。再掏出红包,赏装烟钱。以我爷爷当时的家境,媳妇过门就是劳力,就干活,没有什么可讲究的。但母亲给奶奶装烟,还是不可减免的,那意味着从今而后,媳妇就要听婆婆的,叫“随手”。(当然,这些老古董,在我母亲当了婆婆之后,都被她老人家取消了。从大嫂到我的妻,都没有拜过三朝,也都没给母亲装过烟。倒是在平常日子,她们都很有眼力见儿地给母亲装烟、划火。)那天,老姑教母亲装烟、点火,老姑也婆婆似的承受着抽起来。老姑便说:“嫂子,你也抽一口。这烟,香。”母亲只是摇摇头,并没言语。站在一旁的父亲便说:“抽吧。抽一口,能解闷。”母亲这才抬起头,正眼看了看自己的男人。母亲怯怯地说:“那……你咋不抽呢?”父亲便红着脸说:“我……我喝酒……”
于是,父亲便喝了头一口酒。
于是,母亲便吸了头一口烟。
其实,父亲沾了酒和母亲吸了烟,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只是问到母亲时,老人家总是摇头,笑而不答。再问,便说全都不记得了。
十
父亲一生最大的奢华是死后的事。一口红松木的棺材,足四六的尺寸。那时火葬刚刚提起,乡亲们还没有普遍接受,我家依旧理,土葬。盛殓时,我将一坛子“闾山白”(本地烧锅的酒,用秋子梨做辅料,是父亲生前喜欢的酒)放入棺内,又配了九瓶“大凌川”(锦州产的酒,父亲认为上品)。亲戚、朋友和乡邻们似有不解,我却执意放了进去。哥哥和姐姐们都没反对。
母亲一生所用的,要论价钱,当属那枚老翠嘴。那是一九八五年我到西安,在骊山古董店,巧遇一老妇人欲出售给店家,经店主说合买下的。母亲吸烟日久,所用烟袋嘴,有金属的,如白铜、铝,有石料的,但极普通,没有名贵的。母亲是从不讲究的。然每见母亲好端端的两排牙齿,含噙烟袋之故,上下左右对应处已深深凹陷,磨成了两个圆圆的孔洞,我心中就酸酸的。据店主介绍,玉石中的烟嘴当属翡翠,细腻、温润、冬暖夏凉,不但有益牙齿,且于身心也有补益多多。那是一枚白脂绿云的老翠嘴,且雕工精细,用手抚来,温温的,放在面颊上,感觉腻腻的。母亲极是喜欢。吸烟时总端详,停火时就把不住撩起衣大襟擦拭,像小孩子第一次拿到电子玩具一般,把玩不止。母亲走时,殡葬制度已经改革,但依然用了棺木,这是母亲唯一的遗愿。我把母亲的骨灰轻轻地放入棺内,然后将那翡翠嘴的烟袋慢慢地送到近前。给父亲送葬时,全家人仅仅是胸戴绢花,臂缠黑纱,仿佛领导人的告别仪式。及至母亲走时,就大不一样了,凡族中人皆白衣,系麻丝,鼓乐、纸活一应俱全。民俗文化又有了应有的尊重。
母亲去世十周年忌日,也就是母亲和父亲合葬的十周年,我们全家都来上坟了。从七十九岁的大哥、嫂嫂,依次而来到我这五十九岁的小老疙瘩,身后便是两位老人的孙子、重孙子……八月的秋阳依然沉静地泼洒着那亿万年不变的光芒,母亲和父亲的坟茔静静地卧在闾山角下,坡下那一湾细水闪着粼粼的光,那是要流向绿柳簇拥的小河沟的,最后也终归是要流向大海的。
默默地摆放上果点,默默地点燃三炷香,然后是焚烧那些毫无知觉的纸钱……静默中,大哥给母亲点燃了一支烟,我给父亲斟上了三盅酒,是三钱的小盅。
秋阳无私地照耀着大地、田野、山川,照耀着这世上的每一个人。
[郑重提示:本文关于烟和酒的文字,实乃叙述之所必须。又因为是父亲母亲生活的碎片,故不能舍弃真实,而造虚假。敬请读者见谅。吸烟有害健康,酒过量则伤身,愿天下人远离烟酒。
—————作者]
责任编辑 白连春